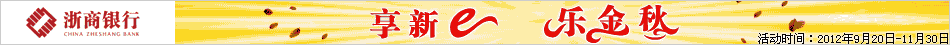华生:发展矛盾与改革路径
对话经济学家华生
今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更新了一条评论:“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让华生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短短数语,让国内思想界爆发出一场大讨论。一时间洛阳纸贵,《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知识分子传阅的读物。
华生的个人介绍是:著名经济学家,师从被誉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董辅礽先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现任东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生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奖项。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适逢改革开放大变局的时代,手执各个学派的学术武器,试图在知识界嘈杂的争议中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以及相关政策争议的宏大图景。
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入世”的情怀,晚清重臣曾国藩有云:“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对经济学家而言,进入决策中枢,作为高层智囊发挥建策作用,无疑是一条“知行合一”的最优路径。而最终,能够将策论推行于世,产生波及深远的历史性效果,就更为值得赞赏。
华生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中提出著名的价格双轨制,为中国经济转型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双轨改革的一种宏观红利。用华生的语言来说,就是某一阶段的改革路径选择,会对后期的政策调整产生不可避免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以致想走回头路很难。从这个角度而言,双轨制可以说是迈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近期出版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是华生“中国改革系列”的开篇之作,主要包括华生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对现状的理性判断以及改革下一步,如何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路径设计。
翻阅华生的博客,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层面包括城市化、资本市场等等献计献策。但华生对于改革的考虑,早已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社会和政治领域。这种开阔视野使得他更能站在全局的角度去解读诸多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提出契合中国现状的可以被高层认可、推动和执行的解决方案。这些观点的表达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改革的忧思。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整体形势?
华生:中国现在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这几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各种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化,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但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过去这些年可能过度强调了维稳,即维持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稳定。一些地方甚至以牺牲法制为代价,这实际上在全局上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这就需要在政治体制方面尽快进行变革。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呢?
华生:从中短期来看,应该说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因为中国处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阶段,城市化处于前中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几年虽然上升比较快,但在全球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短期保持现在7%-8%的增长速度,还是具有现实的可能。真正需要担忧的不是短期波动,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逐步企稳,明年新政府上任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企稳回升,这都是可能的。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中长期的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十八大之后,或者说更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有怎样的推进次序?切入点在哪里?
华生:新一阶段改革的切入点,新一届政府某种意义上已经有所表示。因为推进改革必须是长远的共识,否则很难推进,或者推进的效果也不好。
从新一届政府的动向来看,城市化是重头戏。这也是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上的一个主线。国际评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化的道路怎么选择,这是各项改革切入的关键点。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是农民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他们离开了家乡到沿海城市打工,但是没有真正离开土地。因此一方面他们给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作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巨大的牺牲;另外一方面是农业的经营规模还处在狭小的水平上,这样的城市化道路很难推进。
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自然要求产业升级,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力资本升级。但目前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后代难以升级,因为没有在城市定居,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待在老家乡下,没有接受好的教育。这直接影响到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从城市来说,现在城市化道路导致城市房价高昂,大量的外地人口、更不用说农民工包括外来人口都不能安居,引起城市本身的不稳定。此外,目前城市扩张造成的征地矛盾带来了各种冲突和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步的改革切入点是在城市化的主线下面,首先是土地制度,以及土地相关联的户籍制度的变革。这也是现在经济、社会也可以说是政治的焦点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您怎么看新的改革阶段国企的合理定位,以及“国进民退”等相关争议?
华生:国企的合理定位肯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拿不到最前面来,现在国企问题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国企的核心问题还是要回到过去确定的政企和政资分开的道路上来。这些年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跟国企的关系不但没有分开,而且变得更紧密了,一些地方国企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和平台。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民企目前的处境以及出路在哪里?
华生:我觉得现在民营企业也有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现在不光是民企在中国发展会遇到困难,全球的民营企业都遇到困难,美国的企业困难很大,欧洲的企业困难更大。所以不要把在全球经济动荡当中,企业普遍遇到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遇到的困难都推到制度上去。就像美欧没有什么国企,但不是没有国企民企就能欣欣向荣,不是这么简单。浙江的民营企业过去发展得很好,现在遇到很大困难,制度环境并没有变化。
目前还是要进一步要创造民营企业发展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纯粹在于民企怎么发展,而是在于怎样让各类企业都主要回归到实业上来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大家都说既得利益群体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你如何看待这一群体?
华生:这里的最大问题是现在所有人都讲别人是既得利益者,但都不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比如一般会说国企是既得利益者,那国企里谁是既得利益者?如果说国企的领导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可能说,待遇和市场经济里面比较并没有更高,到年龄就要退休,并没有多大好处落到身上。所以现在最大的难题、困难就在于各个阶层都普遍有怨言。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需要决策者有行动。
《财经国家周刊》:但事实上确实存在很多政策向部分利益群体偏离的现象。如何去优化政策制定过程,阻止它和部分利益群体的结合?
华生:这一方面要靠受到利益损害的人的抗争,形成一种压力。另一方面是要靠当政者和决策者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加以回应。其三是需要好的制度设计,许多时候光是出发点好,未必能达到好的结果。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的GDP还在高速增长,民众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却有激化的趋势?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华生:目前中国处于向中等收入转化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个必然的过程。现在矛盾的激化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制度本身的问题以外,恐怕还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法治的缺失。中国社会本来就缺失法治,几千年来中国是人治社会。中国人的法治观念应该说是在世界上算是比较差的。在目前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以后,在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如果缺了法治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比如民众骂医生得了红包,但医生觉得很不公平,他们很辛苦,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我认为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法治。
其次是缺乏民主参与的渠道,有很多问题民众参与进去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更加理性。如果民众没有参与进去,你把什么权利垄断在手上,大家就会把所有问题都归在你头上。
《财经国家周刊》: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哪些是次要作用?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里面,有些人认为高层可能起的作用更关键,有些可能会觉得智囊起的作用更大,还有一些认为中产阶级崛起可能会有推动作用。
华生:我觉得改革从来都是上下合力推动的。如果民间都很满意,这个时候高层就不会有变革的压力,因为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高层对社会矛盾和变化的判断、认识和反映,改革决定是很难做出来的。除非是混乱和革命,改革离不开上层。
智囊和精英作用都很重要,这不在于他们能否做政治决定,他们也做不了政治决定,领袖人物才做政治决定,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么尖锐复杂的局面,真正能够做出政治决定的当然还是高层。某些时候,某些人物会起很关键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这样。但领袖人物能做出相应的关键的政治决定需要有对应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形势,否则无事生非,少数人想变革也通不过。真正的变革就难以发生。
智囊包括经济学家的很重要的作用是做制度设计,去影响具体的经济、社会等政策往相应的路上走。历史有很多叉路口,选择和走上一条路之后,就有路径的依赖性,将来想返回来就很困难。所以每一条小路都要走好走对,这对于中国能不能成功地改革作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