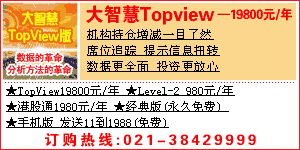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张献民的无限交流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1日 14:20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南京人,1964年出生,毕业于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7年至今一直在电影学院任教。 他当过演员。比较早的是在《巫山云雨》里饰演男主角,那是一个陷入交流障碍的人。他在《颐和园》里也有演出。在独立电影《举自尘土》中,他又扮演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矽肺病人,主要的戏,就是躺在床上大口呼吸。在交谈中,他说自己一直希望演那样一个陷入呼吸困难的人。看来他对于呼吸空间的感受比一般的人要敏感许多。他还导演过两部纪录片,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监制、独立制片人。 在业界内有一个说法,称他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教父”。他是最早关注和参与独立电影制作,并为拓展其生存空间而与各方积极交流的人之一。 禁片史的书写 他交流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是书写。1990年代后的“禁片”,其实现在大多都已经不再是禁片,虽然几乎都还没有获准在影院里放映,但是却有了各种传播方式,比如有了DVD发行。这样一个局面,是时代的进步,是交流的结果。张献民曾为1990年代的独立电影,写过一篇长文——《90后禁片史》。 书写历史,需要一定的特权,首先要能够占有知识。但占有同样知识的人并不少,有的人并不会为这些当时充满失败的地下电影操心,他们可以搞主旋律电影,搞时事性不强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因此这仍然算是张献民的主动选择。书写历史还需要好的文笔,这点张具备。而书写后若没有发表与传播的空间,也不会在当时形成社会效益,恰好当时媒介形式和限制尺度已经得到拓宽,他的文章都是在纸媒上发表的。 张在他的“禁片史”中指出,各种现象的发生,有时候其实只是沟通的不完善。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在内容上并没有违反任何的禁忌,电影局不通过,其实不是针对这部电影,而是因为他以前的过失。由于没有可见的明晰的条文规定,所以处理相关事项时会把过多的个人意志带进来,这些处理方式带有着一定的惩罚性质。张献民说:“直到目前,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常渠道了解谁将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当电影局的修改或其他意见下达之后,也往往仍然无法知道到底谁看了,意见是谁写出来的。如果一个创作者或投资人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是个非常有办法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非体制、地下的色彩。” 他呼吁分级制度,因为分级制度不仅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受到保护,还有其他可见的效应。“电影分级制度是将电影审查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分级必须制定明确的、对社会公开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会因为个别部门的意见、个别领导的好恶、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临时的政策而改变。” 张献民曾在《书城》杂志上开了个专栏,名为“看不见的影像”,最后又以同名结集出版。那些影像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和大家见面,张的做法使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被大家看到。在这些文章中,张以知情人的身份把这些电影背后的故事讲述了出来。吕乐的作品《赵先生》是一部优秀的片子,没有任何反动内容,但是却得不到公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拍摄之前剧本没交上去,等拍摄完毕后想再把这些程序补上去,却遭到拒绝,于是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被领导看过、但被规矩禁止,却从根本上绝对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危害的东西”。 张献民说:“有人说了,你张献民天天瞎说什么,有本事就去拍吧,别说了,整个一假把式。但有这么多人不说就拍了,然后就地下了,然后谁也看不到,怎么办?所以光说不做的假把式我还要当下去。” 娄烨说:“我跟张献民是完全两类人,我不喜欢说,我喜欢做,并对说的人不屑一顾。而跟张献民在一起的日子让我觉得说也是重要的,让我觉得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做。” 从某个意义上讲,那些作品若不能被看到,又不能形成公共话题,那么它们就真的不存在。这些当年有着类似命运的人,虽然他们共享着一个时代背景,但每件事和每个当事人都是孤独的。张献民及其他学者的书写使他们被整合在一个名义下,获得与社会和其他力量交流的音量。他们促使“禁片”成为一个现象。 无限交流的概念 若你不发声,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若有疼痛而不呐喊,则没有人会在意你的疼痛,你将逐渐被忽略掉,当公共政策出台却又没能照顾到你的时候,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你必须习惯于发言。我们发言的每一句话,都不会白说,它们会形成微妙的力量,即使不能在当时马上改善局面,也会在细微之处调整着人们的心理秩序,最终将改变历史进程。 这不仅仅是一个信念,还是一个很容易被证实的观念。当然也许我们不能准确地说,这些独立电影人的呐喊与后来生存格局的改善有多大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声音的确有人在听。2004年贾樟柯解禁前后,电影局召集了张献民、贾樟柯、王小帅等人开会,谈的正是关于禁片的事情。此后,电影局打破了此前设定的很多禁忌。在2003年11月谈话时,有一些人仍然持消解态度,既有对对方的不信任也有为自己创作空间的担忧,张献民是持积极态度的,此后交流的效果,也是很积极的。 2004年1月贾樟柯全面解禁。此后创作《世界》,贾樟柯声称他的创作倾向并没有因此而被改变,“我不会因为通不过就极端,通过就不极端。”后来他的双片审查的结果是:4月13号拿去电影局受审,4天后就拿到了通过的通知。交流使双方放弃了某种抵触和防备心态,从而走向和谐的局面。 从与张献民的谈话中,我发现他不相信二元对立的思维,他似乎不认为世界只有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而是处于时刻变化着的互动中。他说,由于媒介手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从有限交流走到了一个无限交流的状态,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交流却仍然欠缺,那就是公共政策方面的官民交流,态度似乎都不积极。既然现在媒介手段增加,要想有所作为还是不难。这些年张献民曾进行过一些签名呼吁,而签的必须是实名,“我们只能用个人的实名作为保证,这也就是我在网络上坚持的,必须实名,你是一个公民,是有身份的,你必须对你的言论负责。”他说。 无限交流的概念也许还意味着,再也没有一种让人彻底绝望、因为完全没有解决之道而走向彻底对抗的局面,一切都还有着余地,但看你是否有着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而这些力量需要积极地去培养。 张献民一直积极鼓励DV创作,他将DV称为“低微”,DV带来了平民化的影像,成本低,也往往不追求大的利润回收,因此不受各种限制,能够做到平易地观察身边的事情,并可能拿来纪录自己觉得重要的社会资料和用以举证的各类证据。 张曾专门为DV青年写过一本书,叫《一个人的影像》。 这些年,张献民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在南京组织中国独立电影节,目前已经组织四届,他是组委会主席。 传播、交流与经验的开创 现在,张献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黄亭子建立了影弟工作室,定期组织“影弟放映”。影弟的名字,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独立)的前两个音节。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和崔卫平。后两位也一直在为中国独立电影进行呼吁。张献民称,“影弟放映”类似于好莱坞的“试片会”,专门放一些低成本小制作的刚刚完成的影片,多是专业摄像机摄制而成。郝建戏称,“这里放映的电影大多数是穷馊馊地拍出来的,如果一部片子花了20万元人民币,就会被称为大制作。” 这个为电影青年提供看片交流的活动类似于艺术沙龙。由于来的人并不多,所以活动还提供茶水和红酒。郝建则戏称这些观众是一帮伪小资,“在11层高楼喝着红酒看地下电影”,“对底层的关注、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很奇怪地与小资格调和时尚品位融合在一起”。 张献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独立制片人。在此之前,他为很多独立制做的电影提供了许多无偿帮助,现在他试图进行一种产业化的尝试,希望在这些片子里面有自己的股份。具体做法是,他为一些片子提供机器,有时候会帮助寻求拍摄资金,对于后期的发行也有着一定的介入。 最近几年,中国电影持续活跃,但与中国的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电影的多元化程度不足,个人创作才华也展示得不够,这也正代表着尚有着无数的增长点和足够的发展空间。独立制片人这一职业,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就有,但并没有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独立制片人的位置。如今,这个职业又逐渐显现了。 所以张献民的许多经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许是开创性的。在目前,对独立制片人的限制依然很多,但只有试探着走下去,才能体验到哪里有闭塞且需要开放之处,也才有对话、交流以及空间的拓宽。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