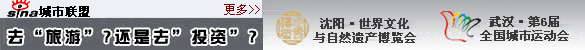不支持Flash
|
|
|
|
被再造的记忆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0日 17:58 经济观察报
叶滢/文 写字台上放着12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旁是几乎家家都有的小台灯,桌面上铺着一整块的玻璃台面,台面下压着家里人的照片,爸爸妈妈带着少年儿童,在某一个名胜古迹前惘然地笑着。电视还没有开演,老式挂钟的时间指向7点差5分。 这是什么时候的情景?至少过了二十年了吧,房间里的时间凝固了。7点差5分,或许一家人的晚饭已经结束,孩子想看电视,母亲还在催问当天的作业。这些人物消失了,那些物件似乎有缓慢的呼吸。这是一个被记忆制造的房间,或者说,是被记忆创造的房间,它存在于某一个时点,与现在的生活遥遥相望。 这是仇晓飞的世界——— 《快七点了》。这些电视机、写字台、台灯……灰扑扑的,好像已经用了好多年,它们是仇晓飞造出来画出来的,用传统的艺术品分类似乎难以归纳,雕塑、油画、装置……都说不明白,但至少这些仿制工业制品的作品,都和记忆有关。 那时候,黑白电视机的牌子至多也只有两三个,家里买回了“飞跃”牌的,被父亲用自行车小心翼翼载回家,但我家里的电视没有放在写字台上,它受到了隆重的保护,被锁进家里仅有的穿衣柜里,除了周末,只能在星期四的晚上抱出来,其余的时间小孩不许看电视,因为总是锁在柜子里,时间久了,电视屏幕上总是出现好多雪花点,爸爸说,可能是受潮了。我的家在南方城市,什么东西都容易受潮,这一点可能和仇晓飞童年生活的哈尔滨不同,他绘声绘色地说起小时候在哈尔滨的冬天,松花江上了冻,可以跑卡车,记忆为什么可以如此生动清晰呢?这是他在生活中惟一可以依赖和把握的吗? 这些灰扑扑的照相簿、用旧了的桌子、电视、主人离开了的房间……出自这么一个看上去颇时髦的青年之手。 两年前,因为索家村要被强行拆迁,曾经去过这个被废品回收站、小汽车维修点和菜市场拥围的“国际艺术村”,庄辉带我们去各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的对库房似的空间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刷成了时髦的全白,仇晓飞和她的女朋友共用一个工作室,室内没有什么修饰,作品零散地堆着,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他画的小玩具、旧照片,一时也不知从何理解,外面是为了保护艺术村激情昂扬的艺术家们和媒体,气氛是热烈而兴奋的,而他的工作室门口,聚着他的一群朋友,他一一介绍,我也不记得名字,这些小青年看上去表情都很淡漠,有的染着红色的头发,有的穿的像个朋克,他的那些旧玩意儿,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有些格格不入。 索家村终究是要拆迁了,去年秋天,仇晓飞要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这个城乡结合部的艺术村。“村子”里没什么人,有些房子已经被拆掉了。仇晓飞的工作室已经很久没收拾了,房子里有些凌乱,一边是他准备去参加利物浦双年展的作品ArtClass(美术课),一边是他做的大积木,黄的、红的、绿的大方块,磨旧了的颜色。一年多前来看过的很多画儿、做的电视机、玩具已经不在了。 我们在空荡凌乱的工作室里说话、抽烟,气氛也有些沉闷。这天上午,我才去顺义见过一个雕塑家,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村子里造了很大的工作室,在雕塑家整洁的院落里,他和我说了80年代时他们那一代人的激动和郁闷,经历听上去都是大起大落的,和时代变化命运攸关。几小时后,我们在索家村边上的小饭馆里囫囵地吃着十元一份的盖浇饭,听仇晓飞说他和女朋友搬到环铁那边了,和几个朋友一起,那边盖了一些可以做工作室的大空房。 索家村的骚动很快归于平静,这个临时性的库房建筑群由于违章建房,被政府命令拆除,而对于曾经短暂居于此的艺术家,这里也会很快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他们仅为寻找工作用地暂居一处,这个地方于他们的经历和情感也没有太大关系。 环铁周围零星地盖起了各式大库房,四五栋一组。这里离798还有好几里地,载人进城的多半都是当地人开的黑车。仇晓飞和他在美院的朋友王光乐租住在一个院子里。王光乐和仇晓飞在美院都是学的油画,一个沉迷在记忆里,一个对水磨石着迷,这里并不是什么艺术村落,仅仅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租的工作空间,他们偶尔在一起聊天喝酒,说说最近看到的人和作品,然后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像几年前他们一起发起的展览N12,12个美院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联展,各自的风格却不同,他们只是12个想被看到的个体,却不是85新潮前后在此起彼伏出现的画派群体,N12的展览持续了三届,作品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到了三十岁的仇晓飞,脸上还挂着些孩子气,或者在生活某处,存在着某个秘密通道,能让他刺溜一下就滑回了小时候的哈尔滨。 四月,仇晓飞刚从伦敦回来,他说起自然博物馆,那些大恐龙的巨大骨架,想当然地认为达敏·赫斯特小时候肯定流连在自然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不然怎么会那么喜欢拿动物的骨架做文章?他漏了很多美术馆,自己钻进伦敦、巴黎的旧货市场。他在旧的东西里翻出自己的新来,在别的城市印证自己的记忆,香榭丽舍大街感觉就像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都是小石子铺的地面,东方版的欧洲风情就这么确凿成了某种最亲切真实的存在,巴黎有些地方很像哈尔滨,这是不是他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寻找到踏实感的理由? “把经历过的情景描画下来或者是凭空画画过去的某一种莫名奇妙的想法,里面也有些东西是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显然,他知道,过去是回不去的。 这些在他的手底下再造出来的某种记忆载体,并不是以过去的旧来抵挡现实的新,这些东西在此时的时间里沉默着,更像是缓慢的褪色的梦境,它独立存在着,不惊扰你,也并不抗拒你的进入,这个梦境与其说是建立在过去的记忆里,不如说它正缓缓流淌进了我们正处在的现实里,它不是封闭的,所以谈不上抵抗和保护。 尽管仇晓飞说,“我希望靠每天画画儿能一点点的建立一个我所熟悉的世界,一些真正影响到我生活的历史”,这些画儿又有那么一些不真实,他画的很多并不是记忆本身,是家庭照相簿上的黑白照片或者旧明信片,这些对于旧时的记录之物再描摹,有些是惆怅的,有些是潦草的,有些是调侃的,他并没有重温真实记忆的决心,他愿意和它们隔着一层玻璃纸,彼此张望着游戏。 他生活的城市是眼下的北京,从西边的父母家到大东边的工作室,要经过塞车的四环、三环,不耐烦的司机大声按喇叭,环路上全起了高楼,房地产广告触目惊心地高悬在道路边,“上东”、“奢适”、“至尊”,大词儿层出不穷,成为商品房或者时髦思想的广告,仿佛人人都进入了华丽的21世纪。这是他此刻正在的城市,被训练出了直接刺激的表达方式,有媒体直接问他作品的价钱,他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问题但也被这样的问题搞得郁闷,他要谋生,也干过美术辅导老师的兼差,但如果谈到钱,他还是没法和更年轻的孩子一样自然。所有受过艰苦朴素的思想品德教育的过来人,都很难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表现得坦然吧。但到底从前的教育教给了我们什么呢?好像又说不上来,留下印象的很多营养都是杂食而来。他和很多90年代的城市少年一样,最初的自我启蒙是被摇滚音乐唤醒,豁出一年的生活费买乐器,最后好梦还是告吹,天生的五音不全;从来都认为进美院附中是侥幸,进了美院也不能按下性子老实上课,逃课、交女朋友、看杂书;匆忙地毕业,将就着以代课为生,前途渺茫时缩在小平房里画那些小画儿,描摹家里的黑白照片……在他这儿,听到的往往令人唏嘘,这个少年,长大得这样辛苦迷惘,即使做了个人展览,去了国外参加各种双年展博览会,他的心里头,还是有个留在童年时的哈尔滨的小人儿。 他的老师刘小东,眼下中国当代艺术最高拍卖纪录的创造者,曾和他说过自己的90年代吗?那对在冬天的铁路边在呼啸而过的火车旁争吵的年轻夫妇,在黑白胶片里留下的是怎样郁闷不安的时光,《冬春的日子》,刘小东和喻红演的电影,也是他们当时的记录,他们三十岁时可能比仇晓飞生活中承受的重量还要重吧,到了仇晓飞这一代,已经不那么明显地感受到政治压力了。他的老师选择直视现实,犀利强硬的,而他,滑进了可能存在过或许也被他篡改过的个人记忆里,那个温和的、毛边的、生动的凝固着的个人世界,对他人没有召唤和冲击,自顾自地存在着,他进到这世界,常常给它重新上色,让它更旧,他坐在这些自造的大积木、旧画架和重新做的阿里斯托芬头像中,抽根烟,常常的,一整天。 这些对于旧时的记录之物再描摹,有些是惆怅的,有些是潦草的,有些是调侃的,他并没有重温真实记忆的决心,他愿意和它们隔着一层玻璃纸,彼此张望着游戏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