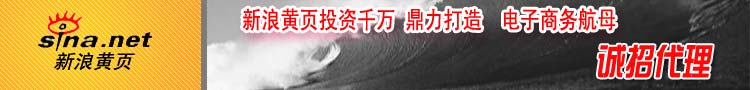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我试图勾勒的是某种集体人格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1日 22:32 经济观察报
唐晓渡/文 1985年2月号《诗刊》头条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题为《为诗一呼》的文章。这是他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促进新诗走向繁荣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这篇文章中,老诗人们同时向“各级文艺领导同志”、评论界、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发出了吁请,吁请他们注意“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所致的贺词中”对“包括新诗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的肯定,吁请他们(“重要的是各级文艺领导同志”)“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吁请的背后是不满,不满的背后是担忧,担忧的背后是正在悄悄兴起的商业化大潮,是各种势必导致诗歌的社会文化地位急剧下降的无意识力量的合流。老诗人们关爱新诗事业的拳拳之心确实令人动容,问题在于,这种“为民请命”式的呼吁将如何落到实处?它所诉诸的良知或悲怀是否能反过来成为其有效性的保证? 饶有兴味的是,于此前后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也在纷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吁请,吁请诗歌社会更多关注他们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回应,回应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率先采取这一行动的是一批四川的校园诗人。他们以写所谓“莽汉”诗相号召,并自印诗集《怒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群落,其主要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等。1985年1月,由柏桦、周忠陵主持的民间诗刊《日日新》在成都创刊,同时创刊的民间诗刊还有署名四川省东方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会主办的《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3月,由《他们》文学社主办的民间诗刊《他们》在南京创刊,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丁当等。4月,民间诗刊《海上》、《大陆》在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孟浪、默默、陈东东、郁郁、王寅、陆忆敏、刘漫流等。6月,由燕晓东,尚仲敏主编的《大学生诗报》开辟“大学生诗会”栏,并撰文倡导“大学生诗派”。7月,署名四川省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研究室主办的民间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创刊;同时北京的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 这种组社团、办民刊的热情在其后的两、三年内有增无减,形成了一定影响的包括:1986年3月,由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推出所谓继“朦胧诗”之后的“第二次浪潮”;5月,署名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室主办的民间诗刊《非非》创刊,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等;稍后,《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在四川创刊,主要成员为石光华、宋渠、宋炜等;又稍后,黄翔等在贵州发起“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并印行同名诗报;1987年3月,由廖亦武执编的民间诗歌出版物《巴蜀现代诗群》印行;5月,由孙文波等主持的民间诗刊《红旗》在四川成都创刊,由严力主持的《一行》诗刊同时在美国创刊;1988年7月,由芒克、杨炼、唐晓渡发起,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并自印民间诗刊《幸存者》;9月,首倡“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诗刊《倾向》创刊,主要成员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11月,民间诗刊《北回归线》在杭州创刊,主要成员有梁晓明、耿占春、刘翔等。 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众声喧哗。这既是在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当代诗歌的自身活力和能量的一次大开放,一场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说的“语言狂欢”。如果说其规模、声势、话语和行为方式都很像是对“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滑稽摹仿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其无可争议的自发和多样性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根本区别。或许,说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达达主义运动更加合适。它在历史的上下文中恰好与前不久那场“清污”运动形成了反讽,并使“指导者”们控制局面、收复“失地”的愿望完全落空。形势变得越来越像W·叶芝在《基督重临》一诗中曾写到的那样: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 猎鹰同再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运动的高潮是1986年10月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据统计,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人数最少的只有一个——诗歌中真正的极大值)参加了先后分两期刊载的展出。当然数量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就像尝试借用商业方式运作(包括运动中提出来的那些针对“朦胧诗”的策略性口号)以推广诗歌尽管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但并没有给这场运动额外增添什么光彩一样。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在于使“朦胧诗”之后一直酝酿着的二次变构表面化了。新一代诗人自我确认式的介入表明,多元化已不可逆转地成为当代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寻求自律的诗正越来越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同时意味着其可能性在生命/语言界面上更广阔、更深入的探索和拓展。由于运动,“第三代诗人”或“第三代诗”成了风行一时、臧否激烈的谈资,进而成为批评家和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很少有人想到,这一集体命名或批评术语的最初版权,竟应归属于毛泽东和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我所目睹的有关这场运动最令人感动,也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诗刊》办公室。当时我正在看稿。一劲男一靓女满面风尘,合拎着一个大旅行袋,像冒出来似地突然出现在身后。未等我开口询问,他们已从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着的旗帜,“呼”地一下展开。旗帜大约有近两米长,半米宽,紫平绒作底,镶着金黄的流苏,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劲沉雄的大字也是金黄的,写的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我一时惊诧,口中讷讷, 却又见他们收起旗帜,复从旅行袋中取出沉沉的一卷纸,在地上“啪”地打开。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叠铅印的诗报,刊头处亦题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旗帜上的显是出于一人之手。此时但听那劲男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来啦!”这话听来像是在背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我不觉“哈”地一下笑出了声。我说写诗就写诗吧,怎么还要咬人啊。这两人却不笑,仍是一脸庄重,也许是紧张。交谈之下,劲男说他姓王,本来身患重病,在医院躺着,差不多已被医生判了死刑。但一听说要来北京,陡地浑身是劲,瞒着医生爬窗户,从医院直接上了火车。“我太热爱诗了”,他攥了攥拳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我无法不相信他的故事,无法不为之叹息。最后他指着地下的诗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筹款印的,想送给诗刊社的老师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给一块钱的工本费,不给也不要紧。”我还能说什么?赶紧掏钱买了五份。我记得那是1986年初冬。 隔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滤网,当然不能指望《诗刊》会对那些正在民间的广阔原野上驰骋嘶鸣的诗歌黑马作出直接回应;但既是生活在同一片时代的天空下,它自也会有自己的机遇和峥嵘。在这里工作的,毕竟大多是第一流且经验丰富的编辑。他们的敏感,他们为诗歌服务的热情,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使《诗刊》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过重心。 吴家瑾,头脑无比清醒、心思极为缜密、永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编辑部主任。任何时候你去她的办公室,都会看到她在埋头伏案。教会学校出身,拉过小提琴,少时即投身革命。在一次话题广泛的交谈中她突然从唯物论的角度说到信仰。她说早年在教会学校时曾请教过一位牧师,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牧师回答:想想电。电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能使灯炮发光。由此我知道勤勉地工作之于她意味着什么,而她的历练又为何毫不影响她心态的年轻。她总是谦称她不懂诗,但正是由于她的慧眼和坚持,金丝燕的《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一文才得以在《诗刊》1986年12月号发表。在我看来,该文或许是整个80年代见载于《诗刊》的最精采、最有冲击力的诗学文章。 王燕生,诗歌界公认的“大朋友”,一只地地道道的诗歌骆驼。他的古道热肠使他们的家门敞向四面八方,使他的桃李遍及江南塞北,也使他曾经英俊的容颜早衰,使他年不及五十便两鬓飞雪。他一年的发稿量,往往比三个人加起来还要多。但他对《诗刊》的最大贡献,恐怕还得算从1981年起,连续组织、主持了十余期原则上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后者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无异当代的“诗歌黄埔”。把他和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是诗,还有酒;而推杯换盏中和酒香一起弥漫的,不但是友情,是逸兴,还有难得一抒的忧思和不平之气。我不会忘记1987年冬某日,为了王若水、吴祖光、刘宾雁等被开除出党,他下班后将我这个群众拽至家中饮谈。那次我们差不多喝掉了整整三瓶白酒,其结果是第二天起床后不得不花十分钟找他的鞋。 雷霆,自称“快乐的大头兵”。我从未问过他这么说时心中是否想着帅克,但假如我真这么问,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确实,在经受了太多的欺瞒和挫败之后,还有什么能比保有帅克式的自嘲、帅克式的机警、帅克式的幽默更值得成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快乐之源?问题在于真要修炼到帅克式的境界决非易事,因此我宁愿认为他的快乐更多地来自他的淡泊和自我安妥。他坚持按自己的时间表和节奏安排工作,毫不在意这样的我行我素对管理体制意味着什么。如果凑巧听到了批评,他会伴以无辜的表情一笑了之。“你不能照着某种固定的程序写诗,因此也没有必要当一个小公务员式的诗歌编辑”,私下里他曾对我传授道:“他们总是盯着我上班迟到,却看不到我差不多天天都最晚回家,更甭说业余投入的大量时间了。我不会和谁计较,关键在于”,他按了按胸口:“咱对得起良心。” 热烈而自持,放达而勤恳,胸有丘壑而又恪尽职守——如此的评价并非适用于其时《诗刊》的每一个编辑,我试图勾勒的是某种集体人格(当然是它的“正面”)。正是依靠这样的集体人格,《诗刊》同仁们群策群力。于1984年下半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办起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及院刊《未名诗人》,以一方面吸引更多的青年读者,应对相继创建的众多兄弟诗歌报刊的竞争局面,一方面适应逐渐增强的商业大潮的冲击,改善日见窘迫的财政收支状况(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诗刊〉通讯》,那是我到《诗刊》后独当一面负责的第一个项目);也正是依靠这样的集体人格,在随后邹荻帆先生因病住院、邵燕祥先生坚决请辞,事实上无人主持视事的一段时间里,《诗刊》的日常工作照旧有条不紊地进行,基本未受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分享这种集体人格,犹如朋友们的诗所带来的震撼,总是被我视为不断摆脱诗歌蒙昧状态的自身努力的一部分。写到这里我能感到一股微温从心头直传到指尖,但我知道这和时间的魔术或中年的感伤无关。确实,80年代《诗刊》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之于我远较90年代值得忆念;它还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变得像后来那样冷漠,那样势利,那样雇佣化,那样在两眼向上的政客和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的窒息下麻木不仁,散发着某种令人感到屈辱的腐败和慢性中毒的气味。 随着“大气候”经历了周期性的震荡后又一次摆向宽松,《诗刊》也开始再度舒展它的腰肢。“诗歌政协”式的“拼盘”风格仍然是免不了的,但变化也甚为明显,这就是以前瞻的目光进一步敞向青年。1984年第8期《诗刊》非同寻常地以头条发表了邵燕祥的长诗《中国,怎样面对挑战》。在这首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危险,/不在天外的乌云,/而在萧墙之内”)为背景的诗中,“五十年代的青春”和“八十年代的青春”形成了一种错综的对话,从而共同凸现出“新鲜的岁月快来吧”这一未来向度上的呼唤。应该说,邵燕祥的呼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诗刊》大多同仁的心声(就像他传达“重庆诗会精神”时阴云密布的表情汇聚着同一的“痛彻肝肠的战栗”一样)。随后《诗刊》的一系列举措显然都和更多地面向青年读者,致力于拓展自己的“新鲜岁月”有关,包括第10期的“无名诗人作品专号”,1985年第4、7两期的“八十年代外国诗特辑”、第5期的“青年诗页”、第8期的“朗诵诗特辑”、第9期的“外国爱情诗特辑”等。尤其是新辟的“无名诗人专号”,作为每年第10期的特色栏目,在此后数年内备受欢迎和关注,事实上和年度的“青春诗会”及刊授学院改稿会一起,构成《诗刊》不同梯次作者的“战略后备”。 同样,密切与诗歌现实关系的举措也体现于批评方面。1985年6月号发表了谢冕评《诗刊》历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新作,兼论现阶段青年诗的长文《中国的青春》,可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信号。紧接着,7月2-4日,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的诗歌学者、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就当代新诗发展的现状和可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会议尖锐触及了新诗批评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叶公好龙”的态度对待“双百”方针,不能形成正常的批评风气;部分论者知识老化,方法陈旧,对新的创作现象缺乏基本的敏感和了解;对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缺乏重视;青年一代从事诗歌批评和研究的不多,有后继乏人之虞等等。随之,11、12月号《诗刊》又连续推出“诗歌研究方法笔谈”特辑,以期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1986年1月号更前所未有——此后迄今也再没有过——地推出了“青春诗论”特辑,使一段时间以来业已初具规模的不同诗歌观念的交响,突然奏出了一个E弦上的华彩乐段。 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一时期称为《诗刊》的自我变革期。这种自我变革同时涉及其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而又有极大弹性和张力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作协机关刊物,它更坚定、更热烈地维护其与党内外坚持改革开放的进步力量相一致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作为为诗歌服务的刊物,它试图更多地立足诗歌自身的要求而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一部分。和同一时期某些风格上较为激进的兄弟刊物,例如《中国》相比,它的美学趣味仍未能摆脱“庙堂”的局限(《中国》因相继刊发一系列“新生代”的先锋诗歌作品,尤其是1986年10月号推出“巴蜀现代诗群”而被勒令改刊。同年12月号《中国》印行“终刊号”以示抗议);然而,和它历来的面貌和心志相比,它却从未显得如此年轻,如此放松,如此主动,如此焕发着内在的生机。这里,“更多地敞向青年”决不仅仅是一个姿态调整的问题,它同时意味着更多地敞向诗的活力源头,敞向诗的自由和多元本质,敞向其不是受制于某些人的偏狭意志,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无限广阔性的、不可预设的前景。 这种势头并未因为1986年春社领导班子的变更而稍有阻滞,而是为其接续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关于这一点,在听了新任主编张志民先生至为简朴的“就任演说”后大家心里就有了谱。正如后来为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他的方略是“无为而治”,换作当时流行的管理术语就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他把自己的就职会定名为“谈心会”,是在以一种最没有个性的方式来表达个性,最见不出智慧的方式来呈现智慧。他说:“《诗刊》是大家的刊物。大家的刊物大家来办。‘大家’不是抽象的,具体讲,可叫作两个‘大家’。一是全国诗歌界及广大读者的‘大家’,一是《诗刊》编辑部的‘大家’。”另一位新任主编杨子敏先生接茬儿发挥:“两个‘大家’的提法很亲切。两个‘大家’融洽、和谐,息息相通,就会为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实行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我们的刊物也就会更加生机勃勃,多彩多姿。”有关会议的侧记热情洋溢地写道:“谈心会开得十分活跃!人人争相发言,争相插话,有回顾,有展望,有对刊物工作的具体设计,有对未来的畅想,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充满了民主、开放、生动、活泼的气氛。”作为与会者之一我认为这并没有夸张。那时我们——包括两位主编在内——全然没有想到,数年后宽慈仁厚的张志民先生会一方面被指为“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软弱无力”,另一方面被指为与副主编刘湛秋一起,合力“架空”了杨子敏。 由刘湛秋接任副主编据说颇费了一番考量功夫,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这位黝黑精瘦的小个子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尽管遇事喜欢一惊一乍,但确实干劲十足。接手主持《诗刊》日常工作后,他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策划才能:从版式到人事,从卷首语到新栏目。作为诗人,他倡行并耽溺于所谓“软诗歌”(从前苏联的“悄声细语派”化出);然而作为刊物主管,他的工作作风并不软,充其量有点心不在焉。他最大的长处是使权力欲和工作热情混而不分。他上任后的“亮相”文字题为《诗歌界要进一步创造宽松气氛》,而他也确实真心诚意地喜欢宽松;只有在感到难以应对的情况下,他才把挑战视为一种威胁,这时他会表现得神经质,在感伤和激愤之间跳来跳去。不管怎么说,他主事后没有多长时间,《诗刊》就呈现出某种新的气象,其最大胆也最出色的举措包括在1986年7、9月号分别刊出了两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诗,在9月号选发了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以及通过当年“青春诗会”人选的遴定,在相当程度上引进了先锋诗界的活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发表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