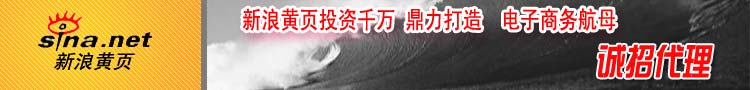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之三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1日 22:11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 全球化正使我们的文化身份变得暧昧起来。 如果有人问: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除去一些外在表征,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答的出。 是时候来考虑我们文化认同的危机了,虽然这一话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被提出。 当传统的家庭、社会伦理随着农耕文明远去,西方文化又汹涌而至之时,知识分子该承担怎样的职责?又应该由谁来重建信仰? 接续上期,本报继续刊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思考与探讨。 是为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系列之三。 金耀基 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任社会学讲座教授,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著有《中国的现代转向》、《现代人的梦魇》、《从传统到现代》、《海德堡语丝》、《剑桥与海德堡》、《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儒家论理与经济发展》、《大学之理念》等。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传统的误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等,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下) ——与金耀基教授对话 文/刘梦溪 1. 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分子 刘梦溪:关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不知金先生怎么看。 金耀基:二十世纪,很多国家都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中国是很突出的一个。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M.I.T.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只有权威的危机,没有认同的危机。其实,认同危机是存在的。承认晚清以来文化危机存在,就不能说没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已把民族与文化拆为二橛。曾国藩为了保中国文化,宁可站在满清王朝一边,而“五四”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为了救中国民族,就不能不打倒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思维结构下,民族文化的认同就不能不有危机了。 刘梦溪:这个危机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真正获得解决。我同意余英时先生的意见,不仅没解决,在某些方面还加深了。个体的文化认同是一个问题,精神的定在性,已有所涉及。群体的文化认同也不无问题。 金耀基:群体认同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群体认同涉及文化、宗教、种族等等。中国是个复杂的大群体,中国的认同与中国文化最攸关,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的认同也就必然成问题。 刘梦溪: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知爱惜,动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自毁根基。近年虽有所重视,却又理路未清,便走向了商业化和俗世化。在这种背景之下,群体认同不但没有得到整合,耗散、失落的反趋严重。 金耀基:在商业化与俗世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最失落、无奈。 刘梦溪: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因为中国缺少学术独立的传统,所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很少能够得到表现。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找不到用武之地。结果知识分子变成了普世化的概念,有文化的人、掌握一定知识的人、大学生,都算做知识分子了。 金耀基:大学生怎么可能都是知识分子?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成千成万个行业,每个行业都需要有知识。这么说,什么人都是知识分子了。我想,不是受过大学教育、有知识的就是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应该是关心身处社会的时代批判者,关心群体社会、时代问题。现代化社会,高度分工,专业性强。能够从本身专业中跳出来讲时代问题、世界问题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超越性,言论才能保持客观。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美国越战时大批知识分子从学术专业中走出来,表达社会理性,反映社会良知。有这种功能才是知识分子。中国过去有士这个阶层,但士之所以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乃是士能够超越士的阶层来发言。中国现代新文明秩序的建构,就需要现代的“士”。 2. 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 刘梦溪: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特别重要。如果说文明秩序政治是中心,家庭则是社会的中心。观察传统社会的政治形制、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需要解剖家庭这个细胞。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立,也需要利用、消化家庭伦理的思想资源。“五四”反传统、反家庭反得最厉害。连熊十力都说过,家庭是万恶之源。今天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家庭实际上也在重建。我知道金先生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愿闻其详。 金耀基: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中国儒家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家。儒家伦理的核心可说就在家庭伦理。五伦中有三伦都是关于家的。至于国,在儒家的文化设计中,也是家的延伸,家的扩大。家的价值中最重“孝”字,胡适说,孔门哲学变成“孝”的哲学。所以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儒家,便以“非家”、“非孝”为攻击的重点对象。 中国的家庭伦理是和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联系在一起的。君臣比拟为父子,朋友比拟为兄弟。我可称你为梦溪兄,从陌生人到熟悉,提到了伦理的层次。所以中国人的社会,是家族式的组织形式,即使在今天最先进的商业系统里,都还有这种现象。当然社会越现代化,家族式的组织形式便会逐步转化为非家族式的组织形态。香港、台湾就出现这种现象。有一点应指出,儒家文化虽重“己”,重个体之尊严与价值,但一落到家的里面,梁漱溟认为,就连个人都看不到了。胡适说,中国人不是自己,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就不是自己。儒家讲的修、齐、治、平,是儒家的一个文化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从家跳到治国平天下,便出现困境,这不是“以孝作忠”可以解决得了的。这在二十世纪就更不可能了。今天,君主已没有了,谈不上忠君问题。而国与家则是二个不同的领域,家是私领域,国是公领域,因此政治伦理、家族伦理应分属两个独立领域。此外,家与国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社会也是一个独立领域。建立现代文明秩序就须往这个方向思考。我有一篇《论中国人的“公”、“私”观念》的文章,谈这个问题比较具体。 刘梦溪:传统家庭的弊端、负面影响,自然是明显的。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对社会的整合、文化的整合,有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特异性的形成根源,即主要来自家庭结构。传统文明秩序向现代文明秩序转变,家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只是如果人为地改变家庭秩序,势必造成对社会与文化的破坏。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习惯搞运动,家庭秩序被破坏了。特别是提倡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制造道德上的难堪,陷于不伦。正常的人格也因此被扭曲了。实际上,这是对社会文明秩序的极大破坏。 金耀基:不过,中国传统家庭秩序在工业化、现代化中也必然会产生变化。只要进入工业化,必然出现小家庭,出现核心式家庭结构。过去,《尔雅》里面,家族关系彼此称呼之多,世界少有,说明中国家庭的繁复性。今后的家庭结构一定会简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虽迭遭破坏,但有些基本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仍得到保持,比如有的母亲节衣缩食,但可以花大钱供儿子念大学,这只有中国,家庭价值观念有力地保持的情况下,才可能这样。 我总觉得,中国传统家庭中有些伦理仍值得有选择的保留,作为建构现代家庭的文化资源。我在二十几年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愚妄的‘孝的宗教’固嫌野蛮,温柔敦厚的孝的精神则十分文明;妇女的三从四德虽不公平,但夫妇相敬如宾则岂不十分艺术?父为子纲固然有害子之独立性,但父慈子孝,相濡相润,则岂不可以减少代沟之冲突?”说到底,有文明的家,才会有文明的国。 3. 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 刘梦溪:请您具体谈谈文化与社会的问题。 耀基:现在用的“社会”二字,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过去没有“社会”一词,有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家、国、天下,但没有社会。当然,自从有人类存在以来,就有社会了。中国为甚么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大概“家”、“国”太突出,社会就看不到了。 刘梦溪:中国有“社稷”的概念。 金耀基:社稷不是社会,社稷指土神、谷神,为天子诸侯所祭,有国者必立社稷,故社稷是国家的意思。从今天社会学看,中国过去确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 刘梦溪:中国虽然没有社会的概念,但以家庭、家族为网络的民间社会是存在的。传统社会的民间力量不小。许多文化活动,特别是宗教活动,以及明末的结社活动,都是在民间。如果说现在文化与社会都面临重建的问题,我想民间这一环不可或缺。 金耀基:是的。中国虽无“社会”这个概念,但不表示中国无社会,只要有人类聚居,就有社会。中国过去有“民间”的概念,民间似是国家之余,政治之余的意思,亦即国家政治力不及之处。传统中国,民间可以有活动空间,但并无一种自主性的意思。这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不同。要建立中国新的政治秩序,如果社会没有力量,便不易发展民主。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意义是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一个市场的逻辑,市场的理性化。通过经济发展,最后导致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出现,这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是有帮助的。台湾的“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刘梦溪: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学术界现在开始重视小传统的研究了。 金耀基:大传统和小传统相互渗透。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一文化下有不同的“俗”。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下边有很多小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的渗透性相当厉害。小传统有其地方性,但不可能与大传统基调不一致,小传统可以成为大传统。在此应指出,中国是多种族的国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体多元”。 讲中国文化,不要太迷信一体化,中国文化其实有许多文化传统。传统是社会历史智慧的累积,也是社会安定秩序的支柱。 刘梦溪:我很怀疑一个说法,按这种说法,中国社会直至辛亥革命一直没有一个大变动,所以当务之急是中国社会应有一个大变动,于是就发动民众变动起来了。后来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社会的大变动最容易使社会的机体受伤。日本的改革比较温和。所以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成功,革新的结果,既能容下传统的又能容下现代的。 4. 关于“挑战—回应”模式 金耀基:从挑战与回应的角度看,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回应。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秩序里,已变成超级国家,哈佛的傅高义(Ezra Vogel,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教授甚至说日本是No.1,的确,日本在寻求新文明秩序时,是一个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例子。中国对传统的批判太过分。破得太多,立得太少。今天有人结婚,用什么方式?西方的?传统的?但什么是传统的,现今的中国人根本连传统的婚礼也不清楚了。 刘梦溪:所以今天文化重建的任务很重。婚礼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西方婚礼在教堂举行,气氛肃穆隆重。中国人结婚,常常大闹一场。喜兴倒是喜兴,庄重就谈不上了。我有时痴想,今天新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在有些方面可能得仿效古代制礼作乐的方法,要有人折中采择,制定出新的礼仪、仪式规范。 金耀基:这一类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日本也有自己的问题。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出席世界法律社会学会议,一位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教授)说,日本有“现代化”但是没有“现代”。现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如“工业化”、“民主化”等,日本完成了。但日本有市场经济,国家却管理得很严格;有民主制度,却为权威主义所渗透;个人的价值,也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性格。这就显出了一个问题,即现代化是不是都应该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若把日本和中国比,可以写很多书。日本的文化,原来是向中国取经的。一直到十九世纪,日本走了脱亚入欧的路。今天它又要重返亚洲。从文化观念讲,日本是受到儒家影响的。后来,才把西方作为乐土。日本维新改革,模仿的是欧洲。二次大战后,台湾学的是美国。 刘梦溪: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唐宋文化,日本人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明以后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就比较小了。相反,现在的日本人很多看不起中国人,甚至不是少数,这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原因了。 金耀基:现代日本在某一意义上讲,是东西文明的结合体。日本的现代化值得我们参照,但并不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要变成,或会变成日本的文明秩序。日本的民主,是讲究共识的民主,不是西方抗辩式的民主。是日本不够民主?还是日本有另一种民主?有人认为,日本现在看起来与美国不一样,但将来还是会一样。这个说法是极有问题的。日本的民主,还在发展。的确,如您所说,日本人中很多看不起中国人。事实上,日本人百年来都想变成欧洲人,即由亚入欧。其实日本人也看不起其他亚洲人,不过,现在亚洲已升起,日本人要想如何由欧洲重返亚洲了。最近,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由日本参与制造的舆论气候。日本人第一次感觉到中国真正开始富强,而有所疑惧。对日本,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挑战—回应”模式怎么评价,是一个问题。十九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统治层与知识界有强烈的反应,即存在“挑战—回应”的历史事实。余先生讲的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动力,是中国传统内部起变生变的力量。这个历史观可以补“挑战—回应”模式之不足。我认为“挑战—回应”模式是一种历史视域,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现代历史演变的线索,当然这不能穷尽中国现代化故事的全貌。一个美国历史学者保罗柯亨就主张要建立“中国本位”的现代史观。 5.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 刘梦溪:我听到一种颇为有趣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式实现的;而近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即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首先从农村开始;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工业结构、工业体制的改革,主要还是要靠农村的工业化。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金耀基:你讲得很好。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城市革命家,他进行的是政治革命,把中国基于普遍王权的政治秩序革命了。毛泽东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不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因此他重视农村。工人革命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中国的改造,中国的现代化,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农村问题。农村人口这么多,百分之十的农村人口一流动,就可以把城市淹盖住。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发展。费孝通先生竭力鼓吹,很有远见。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环保上的大问题。至于中国全面的工业化,当然不能全靠乡镇企业。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问题,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大问题。中国的人口、中国的环保,是下一个世纪不能回避的两大问题。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估计将达十五亿。十五亿个嘴巴一张开,多少东西吃进去。控制人口的政策有必要。 刘梦溪:拥挤不可能产生文明。 金耀基:文明,是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距离是一种秩序。泥鳅一大堆,挤在一起,看不到秩序。农村的重要问题不只是粮食问题。经济不是一切。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但没有科技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村,怎么样才能走向现代化?这是一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道路。环保问题,我也有十分深切的感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日本东京到京都,哎呀,铁路两边都是工厂。最近这几年,在南中国,马路两旁工厂一个接一个。南中国出现了六十年代日本的情景。农村在急遽走向工业化。这令人兴奋。但绿色在哪里?中国生态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能不注意人与自然的秩序。 6. “亚洲价值” 刘梦溪:已经在品尝苦果了。清风明月已经很少看到。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文化界、企业界开始在讲“亚洲价值”,您觉得“亚洲价值”这个概念可以成立吗? 金耀基:当然可以讲亚洲价值。不幸,这个问题被炒得太热,变成非常政治化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因为讲亚洲价值,便成为西方学者媒体抨击与刺讽的对象。其实这是个很严肃的文化问题、现代性问题。西方的现代性,个人主义是根源,表现在西方家庭、西方企业、西方民主中;但亚洲价值则不同(当然,应注意亚洲也是多元文化价值的区域),至少东亚的儒家价值是“非个人主义”的。儒学重个体性,重“己”,但“己”与“人”(即群体)却非对立,这非必是集体主义,但决不是个人主义。西方企业和东亚的不一样。过去讲管理,就是西方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日本经济成功了,才承认有日本式管理。讲管理,要看是否有效率、有效能,没效果不行。日本管理的效果不差于美国,才被承认。过去讲民主,也就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但现在也必须承认,民主非必只有美国式的。衡量民主,主要看是否尊重个人之尊严,是否对权力之更替有合理机制等,但不必一定是美国的二党制、三权制衡制,也不必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有一种争论,即亚洲的现代性,是不是一定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前面我们说过了,欧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性的“个案”,那么今后会不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第二个“个案”?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关心思考的大问题。 刘梦溪: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吗? 金耀基:假使你一定要我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我的答案是“是”。现代化理论中有一种看法,即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走上现代化之后,最终所出现的现代性(或现代的文明秩序)必然趋于汇流,亦即会出现同一的现代性。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这种持“同一的”现代性观点,不啻视西欧的现代性不止是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也是一切现代性的“范典”了。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相信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别类的现代性之可能,亦即现代性是“多元的”。上面所讲的现代化理论完全没有考虑历史文化的因素,当代哲学家泰勒(C. Taylor)对此有深刻的批判,我很引为同调。不止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或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所建立的现代性也可以有其特别面貌。当然,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会有“共相”,但也会有其特殊相。 刘梦溪:您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深刻阐发,使您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一直站在前沿位置。请问,您今后的研究方向会有什么变化吗?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是我长期研究的兴趣,它不仅是学术兴趣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走向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建构的问题。近几年,我的关注点由“现代化”转到“现代性”问题,二者有关,但却有根本性的不同。讲“现代性”,就要进入到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也即对西方现代文明秩序的批判。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性的批判,盛极一时,更有“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种种说法。我认为对中国,对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现代化还是主要议题,至于西方是不是已进入“后现代”,还是个争论不已的题目。简单地说,对我而言,讲“现代化”,重点是中国发展的问题,讲“现代性”,重点就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今日,应思考的是地球村的现代性问题了。
【发表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