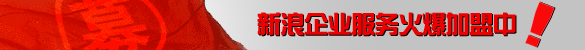知青九年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5日 17:23 经济观察报 | |||||||||
|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被捕,持续10年之久的“文革”宣告结束。以后三年中,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并有700万以上的知青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途径回到城市。三年后,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但在人们的记忆中,1976年应该是上山下乡运动实际终结的一年,迄今已三十年。 在上一期,我们刊登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小萌的文章,力图告诉大家,一项旨在缓 另外,上期我们还选编了刘小萌的两篇知青口述实录。感谢以刘小萌先生为代表的知青史学者,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富有责任感的记录者。他们把一个个知青从悲痛与怀旧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使其坦然而富有批判性地正视过去,也使得我们对那场人类迁徙运动有了一种深切的体验。 本期,我们刊登另一位历史学家秦晖的知青回忆录,继续我们提取和保存记忆的工作。同时我们想告诉大家,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正在从事口述历史的工作,但是进入这个领域并不都需要历史学的学位,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失忆、错忆,甚至佯装失忆。那段历史结束不过三十年,你忘得了吗? 访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以下简称A 口述:秦晖,以下简称Q A:您家是世代居住在广西吗? Q:我父亲是广西的土著,我母亲来自东南沿海:浙江,她是“8·13”抗战沿海沦陷后流亡到广西来的爱国学生。那时候广西是中国的大后方,桂林则是当时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我父亲则是本地学生,抗战期间在那里(桂林)进大学,1948年毕业,在校时我父母都积极参加反蒋的学生运动,是第一代民盟成员,但不是共产党员。 A:民盟应该是在西部由一个姓张的人创立的吧? Q:您说的是张澜?他是当时的领导人之一。 A:与您的父亲在同一个时期吗? Q:对,但张是老先生,是名人。我父母只是个大学生,民盟的基层活动者。父亲当时曾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是共产党把他推上台前的。由于有这段经历,解放军进城后他们便进入桂林市军管会参加学校接管工作,后来到广西省教育厅任职。 实际上40年代广西的民盟组织与许多地方的民盟组织一样,是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我父母两人的入盟介绍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我父母本人不是。虽然他们一直信仰马克思主义,但1949年后并不被信任,尤其在文革中他们被放逐到广西最穷的县之一,为时达8年多。直到1978年与我进入大学当研究生同时他们才“落实政策”回城,回来后他们已不愿回原机关,而要求去教书,结果到大学里过了几年学术生涯就退休了。 但总的说来我父母还是幸运的。1957年他们也参加了“鸣放”,当时正好我父母工作的省教育厅有两位刚从北京教育部下放来广西不久的民盟成员不幸抵充了“右派”名额,我父母得以幸免。但他们从此不敢参加民盟活动了,虽然当时他们还分别是民盟广西区委、南宁市委委员。此前早在50年代初,我父母就申请入(共产)党,但直到80年代改革初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才在晚年被批准入党。而他们的儿子我反而在他们之前,70年代在农村插队时就入党了。 A:他们当初加入民盟是在哪儿? Q: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当时叫广西师范学院,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解放以后,省会才从桂林迁到南宁。 A: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占领的桂林? Q:大约是1944年8月,“湘桂大撤退”的时候,(占领)直到1945年初。当时学校就疏散了,我父亲被疏散到了贵州,母亲则被疏散到了广西的山区,罗城县。 A:那您的祖父是广西人吗? Q:是,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县的土著。 A:他是学者吗? Q:不是,他是龙胜县的一个农民,但有时也做些小买卖。 A:那您是在桂林长大的吗? Q:我是在南宁长大的,因为1949年以后,我父母成了干部,随着省府迁到了南宁。我是在南宁出生的。 A:那你的中学也是在南宁上的吗? Q: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然后进了中学,从1966年到1969年,你可能也知道广西的武斗很厉害,整个儿都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就在这三年中,我度过了初中,但实际上没有上过一天正式的课。到1969年,我就下乡插队了,当时我15岁。而且,您可能知道,广西在文革时是一个特殊的省份。在其他省份,大大小小的造反派或多或少都掌过权,但在广西,他们从来没有得势,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前的一把手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是一把手,这在全国是惟一的。因此,广西对造反派的镇压非常残酷,而我们这一派就是被镇压的。这样,我们当时下乡,除了毛泽东的号召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对我们这一派的惩罚。 A:是在广西下乡吗? Q:是,是在广西最边远的地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叫田林县,属于百色地区。然后,我在那儿一呆就到了1978年,即9年多的时光。 A:您呆的地方,是纯粹的农村,还是类似于建设兵团那样的地方? Q:是农村,纯粹的壮族农村。我们田林县是广西人口密度最小,而面积却是最大的一个县,从我们公社到县城足有200里(100公里)。 A:您是一个人呆在一个村子,还是和别人一道呆在村子里? Q:当时那里的村子都很小,比如说我呆的那个村子,一共只有11户人家,容纳不下那么多知青。因此,当时的知青都比较分散,一个村子有时只有1-2个。我们3人在一起就算是多的。但在中途,大概是在197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知青家长,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青的一些问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集群定点”。我们则被集中到了一个大的村子,形成了有10来人的知青小组。因此算来,我在前一个村子呆了5年,在后一个村子呆了4年多。 A:后来的那个村子大吗? Q:也不是很大,只是比前一个村子大一点,那个村子大约有70户人家。重要的是这个寨子临近公路。而我们原来那个寨子离公路就有60里。那时如果要进城,你必须走整整一夜山路,次日早上到公路旁等汽车。如果白天走,到公路边已经下午,就要住宿。而我们那时穷得住不起旅店。 A:您可以随时回南宁吗? Q:因为我父母也被放逐到了另外一个县,叫凤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回南宁。而且,我刚刚说过,我们村离县城有100公里。因此,很多农民连县城都没有去过。 A:您对那里的农村的印象是什么? Q:首先是贫穷。但是,我们南方的贫穷和西北的贫穷不是一回事。西北是不毛之地,而我们是与越南类似的丛林地区,热带雨林地区。而且,因为人口少,生存空间很大。所以,生存是没问题的,即使粮食颗粒无收,靠采集也能生存下去。我们刚去时那里的山民甚至没有种菜的习惯,“自留地”种的也是玉米。要吃菜了锅在火塘上烧着,人到寨子旁的丛林里转转,弄点什么竹笋、野菜就下锅。但是,那个地方的农民没有什么货币收入,从货币收入来说,那他们可真是穷得一塌糊涂。 A:另外的印象呢? Q:就是当时的那种制度。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在正常情况下,那里是不会发生饥荒的,因为靠采集也能生存。但是就在那样一个地方,1959年前后,几乎村村都饿死了很多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按理说那地方是不应该饿死人的。到后来知道,1958年的时候,我们县搞“钢铁野战军”,把全县一半的劳动力集中到几个山沟去“炼钢”,用武装民兵把他们困在那个地方不准跑出来。结果一断粮,又把人给困在里头,大饥荒就发生了。 A:你和那里的农民的关系怎样? Q:应该说很不错,我最近一次回去是在1997年,20多年后,在同去的一批知青中我几乎是惟一仍能与村民用壮语交谈的人。不过这主要是由于我在那里呆的时间长,插了9年队的在这些知青中就我一个。而当年大家在农村时,我并不是与老乡们处得最热乎的。原因并不是我有什么城里人的身份感或者知识分子的清高而看不起农民,相反,我当时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把“贫下中农”看作理想主义教师,一门心思想从他们那里感受“大公无私”的圣人气质,以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私心杂念”的。然而,现实中的农民不是圣人而是俗人,把他们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与把他们当“土佬”来鄙视的人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的“知心人”。而且前者甚至可能比后者与他们更隔膜。 那时的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而我们这号怀着“朝圣心态”与“贫下中农”接触的人倒很难真正与他们“打成一片”,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把他们当成俗人的知青可以接过话头插科打诨,我则只能面红耳赤默不作声。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把他们当成俗人的知青很会凑热闹,我则往往兴味索然不知如何搭腔。当然这不会使我“看不起”农民,因为意识形态教育使那时的我相信这些都是“支流”、是“表面”,当老乡和我谈起生产或者队里的公事时我会找到对“贫下中农”“本质”的感觉,更不用说假如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些什么为革命种田的大道理(可惜这类“本质”话语我从未听到过,当然除了开会以外)。遗憾的是老乡们(其实我也一样)总是生活在“表面”上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中,现在想来,这种把生活“本质”化得不食人间烟火的看法不就是所谓“异化”吗? 应当说老乡们和我的关系是不错的,我干活卖力,生活上惟恐不“农民化”,那时频繁征调劳工(号称“民兵”)修建各种工程,农民恋家不愿远出,我则很愿意出来顶这份义务。我那时以爱看书而小有名气——不是看“学术”书而是各种农村应用百科知识,如水电、农机、医药、农技等等,还是解决了村里不少问题的。老乡有事我很乐于帮忙,那时我决心自食其力,从不让家里寄钱物,这在当时我们这批知青中极少见。但老乡生病要药什么的我可没少麻烦家里。我父母把我当时的农村来信一直保留着,90年代一次回广西我妻子看到这些动辄向家里伸手要这要那的信件好一顿挖苦,说你可真能慷爹妈之慨去巴结老乡。反过来讲,老乡们在生活生产上对我关照当然也不少。平心而论我还是怀念他们的。但现在回想,我和老乡们并不真正贴心,往好了说是君子之交,往不好说还是一种隔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那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识形态氛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某种政治表演色彩。我想老乡们对我这个过于“假正经”的人不会觉得很亲切,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我是我们那批知青中最后离开的一个,来时我才15岁,是知青中最小的,走时却已是全公社知青中年龄最大的老大哥了。当插队9年多之后我终于离开时,全村多数人家都来了人送我,但那主要是一种尊重,并没有挥泪惜别依依不舍的场面。其实,在插队的最后三年我已经随和多了。那时我几次被借调到县文化局去搞乡土文艺创作,与文化馆的专业创作人员合作为本县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编写壮剧、彩调、民歌等演出脚本。由此我对乡土文化、主要是当地壮族土著文艺形式如壮剧、师公戏、腰脚韵壮诗与山歌发生浓厚兴趣。而众所周知,真正的乡土文化总是具有浓厚的感官色彩,所谓“郑声淫”是也。过去我这个“正人君子”对这些“黄色山歌”什么的如同对乡间的“下流玩笑”一样从来敬(对“贫下中农”不能不敬)而远之,但现在我有了“采风”的浓厚兴趣,这无疑明显拉近了我与乡村世俗生活的距离。这几年我学会了不少“酸曲黄调”,对壮族民俗与乡土文化的知识大有进步,(用当时的套话讲)也“密切了群众关系”。但是正如再执着于“参与式观察”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土著”一样,我的“采风”兴趣实际上还是一种认知兴趣而非真正的文化认同。应该坦率承认,插队9年之后我没能真正成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虽然我一直这样追求。 因此我曾说:“如今回忆知青生活的文字总不离两个调子:一是诉苦怨旧型的,以上等人落难的腔调把农民说的很不堪;二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间,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这两种说法让人分别想起当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城里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形相反而实相通的两种调子。”我对这两种调子已经不感兴趣。对那片我确实为之“贡献了青春”的土地我不可能没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对我而言已经是个人化的。那些年里我既有难忘的温馨回忆也受到过伤害,但这些都不足以使我有理由在整体上把农村与农民看得高于或矮于“城里人”,认为二者中谁有资格“教育”谁。当年与如今我都有不少农村朋友,但他们是以某甲或某乙、而不是以“农民的代表”身份成为我的朋友的,正如我本人也从不自称代表了农民(我认为这种代表资格是需要农民授权的)一样。 这些年来有人说我研究农民问题是“情系黄土地”。当然当年的生活感受对我后来的治学经历影响很大,但我认为我治学还是从理性出发而不是从情感出发的。我对现实中农民问题的言论得到不少农村群众的好评,对此我当然高兴。但是有人说我是维护农民利益的斗士,对此我只能说任何人的利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我作为一个学者既不可能竞选农会主席也不可能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谈不上代表他们去争取利益,我只是希望给予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公民权利(例如组织农会的权利)。有了这种权利,他们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别人被剥夺权利而旁人视若无睹,那么任何人的权利也难保了。 作为利益群体,农民的利益未必就是我的利益,但作为公民,他们的权利与我的权利是统一的。我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我自己的权利。不仅农民,工人等等的权利也是如此。作为学者我主要研究农民问题而对工人问题了解较少,但作为社会评论者,我对工农和其他公民群体的权利都是关注的,并不只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A:壮族人和越南人之间,由于离得很近,是不是在风俗上很接近?另外,在起源上,壮族和越南有什么关系? Q:壮族作为族群与文化共同体是跨越国界的,她在越南是仅次于京族(越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但壮、越两族不仅并非一族而且差异较大,虽然远古她们大概都是“百越”的组成部分。不过我觉得当时华夏所谓的百越大概也如后来西方人所谓的印第安,只是称谓者对其不太了解的许多族群之总称,并非单一的民族。如今按中国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壮越两族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但壮族属该语系的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老挝、泰国语都属此支),越语则语族未定,亦即壮、越关系较壮族与老挝、泰国人为远;而越南官方学者更否认越语属汉藏语系,声称应属南亚语系,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 越南北部有大片壮族聚居区,居民和广西没什么两样,相互之间也有来往。但是,您可能也知道,在当时体制下,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民族问题都被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看待。所以,“民族识别”问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学”问题。 A:壮族说的语言是一种别的语言,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方言? Q:在语言分类上,它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傣语支,和老挝、泰国的语言比较相似,跟汉语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壮族之间有方言的差异,比如说,南部壮族和北部壮族的语言就几乎不能相通,然而北部壮族与布依族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在民族分类上,语言相通的布依族和北部壮族分成两块,而把语言差异很大的南壮和北壮却划分到了一起。 A:在下乡的时候,你可以读书吗? Q:可以,因为偏僻,管的人很少。而我当时的藏书,主要是从家里带来的;另外,在我们那个很小的县城里,由于当时的文革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当时读书的人很少;另一方面当时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图书馆的书有熟人就可以拿到。我跟县文化馆的人很熟,于是就可以入库任意挑书,既无数量之限,也没有按期归还之说。实际上就是要按期还也很难。因为我们寨子离县城很远,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去一趟。您可能知道,中国比较活跃的思想,最早就产生在60年代,当时为了反苏而翻译了一批书,从这批反对苏联制度的书中,一些中国人得到了启蒙。这些书一般都叫灰皮书,因为是内部发行,封面没有任何装潢。它们的发行范围分好几级,有的如托洛茨基骂斯大林的书只有省军级干部才可以读,县里是没有的,但县级发行的多一些,每县只配一本供县长、书记阅读。比如我这里就有一些,像这本The Socialized Agriculture of the USSR。文革之前按规定,这种书我们是读不到的,文革中一切都乱了套,在那样一个偏僻小县这些书根本无人问津,我于是就得到了“县长待遇”,不但看了,还拿了一些。 A:我感到很惊奇,因为这本书是美国人Jasny写的。 Q:当时翻译这些书的目的是反苏。但后来,当人们看到它的时候,不由地对现实产生了某些联想。 A:您说到过您在初中几乎没怎么上过课,那您的大学是在哪儿上呢?又为什么选择了农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 Q:很有意思,其实,我既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本科。我说过,我下乡插队9年直到1978年。1978年从农村里我直接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而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实际上就是搞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研究的。 A:硕士毕业之后呢? Q: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在那里先后通过讲师、副教授又“破格”升为教授,可以说在“纯学术”生涯中我算是一帆风顺的。直到1994年我离开西安。 A:您是什么时候来的清华? Q:1995年。其实我1994年就来了北京。但是,先是在中农信(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他们当时打算成立一个农民学研究所,希望我来主持。 A:那为什么您后来又离开了呢? Q:不多久这个公司就出现危机。它本是80年代改革中出现的一种亦官亦商的寡头公司,1989年学潮时它与中信、康华、光大被并称为名噪一时的四大“官倒公司”之一,这类公司往往卷入政治纠纷而兴衰不常。我于是去了清华。我离开后不久,这个公司还真是垮了。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6—) 当代英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思想史家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评论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帮你赚钱 |
| 21世纪狂赚钱--绝招 |
| 韩国亲子装,新生财富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39健康网=健康金矿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