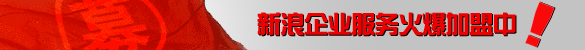崔卫平访谈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5日 17:20 经济观察报 | |||||||||
|
王:前两天报纸报道了所谓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互相“炮轰”,我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发现似乎交流出了问题,因为他们报道的你的观点,跟你平时表达的观点完全相反,是报纸的报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崔:当我看到媒体上的标题“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时,大吃一惊,心想做新闻就是这样写文章的?那是一个关于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小说讨论会,如果说会上真有什么“炮轰”
王:最近你在纸媒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涉及的面也广。陈家琪也说读你文章后,无法判断你的专业。你如何给自己定位? 崔:陈先生是过誉之辞,我的写作状态,主要是受问题的引导,问题将我带到哪里,我就想法尽力阅读、解决问题。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我原来的专业是文学,在这个领域中所花的时间、精力最长。算起来前后有二十年来学文学,研习文学的修辞学,写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文学的文章,我说过自己是“新批评”出身。只是因为有了这个积累,这个专业底气,我才敢于去做别的。因为在专业领域中,在经受训练有素的同行严厉目光质询的同时,逐渐养成了一种比较练达的眼光,或者说是比较理性的眼光,自我批评的眼光。这样的经验会带到其他领域中去。就好像一个木匠,他虽然不会打铁,但是他一眼就能够看出一个铜匠的活干得地道不地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专业上的底气,那种坐冷板凳的经验、忍耐性,那种长时间的积累,我们怎么相信他是可靠的呢? 王:你说的这种训练,有技术的部分,也有一种心境和气质的养成。另外,哈贝马斯说,修辞学与解释学乃是指导和训练交往能力的。 崔:哈贝马斯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不通过哈贝马斯,这个问题也能够说得清楚。拥有一门专业,意味着你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而不当寄生虫,你说这本身不是合乎道德的吗?并且,专业上的精练,同时赋予你一种自由人的身份,你凭本事自己吃饭,还要看人的脸色吗?若不高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应该说,有自己扎实专业的人是最好打交道的那种人,最容易与别人相处的那种人。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有一门自己过得去的专业,所有的事情肯定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当然,人和人的专业不一样,有些专业本身就是与专业范围之外的东西密切相关的。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他写下的句子在剧场被大声念出来,剧场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场所。他得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要太过个人化、私密化,否则多么难为情。而作为剧作家需要敏感,需要谛听整个社会的脉动、气息,将它们放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再者,一个人关心自己专业之外的事情,与他忍受的程度也有关系。同样的东西,对某些人来说几乎是不能忍受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安然无恙。 王:你翻译了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还引进了东欧其他思想资源,那天与学者赵诚同车,他认为你有两个贡献,一是把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的观念引进来,把他后现代风格的写作转化成一种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力量。另一个是把米奇尼克“共存”的理念介绍了过来。 崔:趁此机会,我要说一下对于哈维尔,人们一直有许多误读。哈维尔是个现代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后现代。同样,哈维尔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国治天下”的“谋士”、“策士”也很不一样,至少他对于经济问题几乎一窍不通,最早他发出抗议时,对于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也所知无多。他是一个文化人,他最为充分表达的是一个身为文化人的立场。你看他最早的那篇给胡萨克的信,基本上是从当时捷克社会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情况提出问题的。他指出目前这种处处谎言的道德现实,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是十分可怕的。他还指出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来说,不一定是明摆的问题,那些目前尚未感觉到的东西,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闪光的东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的杂志,不过区区几百个读者,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不起眼的杂志的某个地方,也许潜伏着某些目前不为人所知的某个灵感,而社会的前进就靠着这些走在前面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因此,干扰一本戏剧杂志,所造成的影响不是目前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成本看不见但却是巨大的。 米奇尼克学历史出身,他的视野与哈维尔很不一样。他始终在考虑社会应该如何建设。这个立场与波兰民间社会比捷克更加成熟也有关系。“共存”本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维度,只是在一个“你死我活”的文化背景中,才显出其了不起的意义。照人的天性来说,都有排斥他人的倾向,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黑暗,而有权力的人处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更加容易将这种黑暗加以放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明”就是对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加以限制和改动。文明人是知道如何与别人和平相处的人;“文明社会”就是共存的、共处的、共享的社会,米奇尼克强调说“只有一个波兰”,所以要能够使得所有的波兰人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剥夺其中一部分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流浪。 王: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人,尤其是哈维尔的写作与一个搞文化批评或者文化研究的人很类似。他们分析了文化氛围、私人化日常行为与政治权力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从一个制度或者政治的角度进入,但这个角度的进入对于当代同样有效。而在我们的语言环境里,强调文化、道德对于制度建设的价值的人,常常被人认为是在说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 崔:“文化批评”是一个特定的词,并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都是“文化批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尔、米奇尼克他们并没有用过“制度建设”这样的词汇。其原因我的理解是,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空间不允许,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实干家,他们所谈论的,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谈论别人的真理,但最好让别人去行动,或者仅仅说给大人物们听。米奇尼克谈建设公民社会,前提正是自己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而我们这里有些谈论“制度建设”的人们,自己属于“制度建设”的一分子吗?同样,那些把“文化”挂在嘴边的人,其谈论的方式也不是文化的方式,而是“谏士”的方式。谈论属于自己的真理,这也是追寻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并不是说,这些捷克、波兰的知识分子缺少对于全局的考虑,恰恰相反,他们有着对于本民族未来和现状的自觉考虑,有着身为知识界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的清晰想法,有着作为知识分子如何担当民族前途的有意识的使命。不同的是,他们怎么想就怎么去做,去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包括文化上的事情,包括从文化、道德、公共平台、公民社会等维度提出问题,而不是替代别人进行考虑,把自己换位到有权者的身份上去,替对方进行设想。 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不应该是别人的身躯、自己的影子;而应该是自己的血肉身躯和脚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评论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帮你赚钱 |
| 21世纪狂赚钱--绝招 |
| 韩国亲子装,新生财富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39健康网=健康金矿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