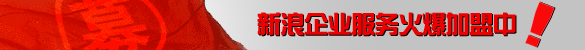崔卫平:我意图理解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5日 17:06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特约记者 王小鲁/文 公共发言的能力和道德 采访崔卫平教授,并没有太大难度,因为平时与她也多有交流。但是她前段时间身体不适,到密云青山绿水间的家里休养了。近年来她似乎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关注学者学
上半年,中国文化界发生了思想界与文学界互相“炮轰”,崔也置身其中。但报纸报道的关于崔的观点,与她平时素来坚持的相反,而有的作家也据此批评崔,于是又展开了一次缺乏建设性的争吵。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言训练,为什么精英们的交流仍然如此劣质? 交流与公共空间的良性建设,一直是崔努力的目标。在当下,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交流的障碍。在采访她的过程中,笔者的表达出了问题,她说:“我发现你的表达不如写作流畅,不过,我有时候也这样。”她说在北京电影学院上课时,学生都不喜欢发言。“我对他们说,你们发言不是对我负责,而是对整个空间负责。” 不愿发言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小时候老师鼓励你发言,其实只是鼓励某种特定发言,因为普遍舆论与公众精神的真正激发,常让部分老师难以控制。到后来,即使学生们有发言的热情,也没了发言能力。学生带着缺陷走入社会,给予社会以先天的不足。在国家压力下的社会空间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加强公共空间的建设是此时代的重要命题,也因此,社会需要一种发言的训练,需要有表率力量的个体出现。 崔卫平正在努力起着表率的作用。她近年来在公共媒体频繁发表文章,以至有朋友说“崔卫平简直是在母仪天下”。我问她最近这些年的发言,是不是受到了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公共空间理论的激励?她说,肯定有这个因素在,但我面对的是具体情境中的具体问题。 公共交流和公共空间是近来使用率颇高的词。在二战与纳粹之后,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等学者更加注意探讨公共交流的重要性。他们倡导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包括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比如说艺术意志需要与社会意志相沟通,这一现象的出现乃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世界性的或者国家内的灾难是由于交流不充分,公共空间缺乏建设。他们甚至认为,不会交流的孤独个体乃是极权的基础性力量。这个观点,也是崔在不同的场合不停地强调的。崔卫平喜欢阿伦特,她这几年的学术工作也受益于阿伦特,比如她引进的东欧的一些资源,正是顺着阿伦特这个藤蔓摸过去,寻找到的。 “私人生活的起点,就是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当人仅仅屈服于身体的需要、当他的生活仅仅是围绕物质必需品、围绕某种‘必然性’开展时,这个人是不自由的。阿伦特指出,在古代希腊,‘private life’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它被剥夺了参与世界事务权利。而如果把与他人共同的世界看做意义的来源,那么,沉陷于私人性中的存在则是荒芜空洞的。” 尤其是1980年代后,我们曾有称颂孤独的潮流,而崔的这个说法,却将人置于一种需要社会合作的压力下,仅此一点,她就区别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作家。崔渴望优质的交流,她的榜样是山姆佐德,《一千零一夜》里那个以讲故事阻止国王暴力的小女孩: “我觉得世界需要表述,表述就是理解,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什么关系。整个世界不能理解,那就是完全荒芜的。山姆佐德在讲故事,叙事就是意味着意义,她的故事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哪些说得长一点,要叙述哪些场景,放弃哪些场景,这些就是她的立场。所以意义就是通过讲述来实现的,这里是寻求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 经验主义的,女性的,贴身的 崔卫平以前是搞美学的,但她超越了专家身份,几乎针对社会整体进行发言。这就有难度,我认为她克服这个难度的主要办法,就是从经验出发,不停地回到生命原点,以此为据点考察一切。有生命细节做支撑,发言就不空洞。“学术的非学术的起点”、“政治的非政治学的起点”,这都是她大力提倡的。 崔卫平在北京电影学院讲课,许多学生似懂非懂,但还是不停地被吸引,许多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前来蹭课。她的课有特殊的力量,她往往从某件发生于我们身边的小事讲起,一步步向上引领,最后到达一个理论平台,日常的生活细节经过一番分析,忽然得到升华,获得了意义,这是奇妙的体验。“风起于青苹之末”,这样的讲课方式是经验主义的、反概念先行的。她的写作风格也是平易的,文章里没有意识形态或各种主义的对抗,所以这样的学者无法以“左”或“右”来定性命名。 “顾准有一本书叫《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走到经验主义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都是从概念出发,我现在尽量要求自己每说一句话,都有经验的成分。其实概念是容易的,我每次上课都帮学生分析作业,发现他们喜欢用大概念,后来我就说,这样吧,你们写理论文章都带秆小秤,每个概念看看你能不能拎动,拎不动就别拎,这些概念要和你的身高体重有个合适的比例。” 这就是她的说话风格,她经常在课堂上做一些生活化的比喻。比如她很喜欢讲“现代性”、“现代主义”,她说,现代以后,一切都不再是根深蒂固的了,“就好像一种小白菜,你种在地里长不大,必须在它生长到一定阶段后给它挪个地方,它才能长大。”现代之后,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坚固的、无须怀疑的东西,一切都必须接受再检验。 生活化、经验、感性直观,这些词似乎与女性更有亲和力。西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于日常要求,更关注个人生活的感性品质,而这也许恰好可以解释崔卫平为什么会禀有那样独特的思考方式,比如她提倡“政治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如此说来,女性身份在崔的写作中是有意义的,但她承认这一点吗?女性主义运动如今已经发展出了繁复的层次,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要过分强调女性性别身份,而有的则认为必须强调。崔卫平早期的文章中也曾经涉及类似问题,但她认为这个时代不仅仅女性权利有缺失,男性权利也有缺失,虽然她似乎也承认女性有自己独特的权利状况。从这里来看,也许可以冒昧说一句,崔卫平是有母性光辉的。也许崔不喜欢这样的话,因为把“母亲作为女性惟一有价值的身份”是很有男权色彩的。 崔向我坦言自己的写作与女性身份的关系,“比如我对于历史上的大人物不感兴趣,那是少数族类,他们把大部分人包括普通人和妇女都排除在外,大人物的经验不是我们的经验。我最近写文章批评张艺谋拍《秦始皇》,里面说秦始皇为开创伟业丧失了一些人性的东西。我认为,你不能在杀我头的时候,我还在替他着想。政治的话题,在中国很可能是变成一个大人物们的话题,谈到政治,就是治理国家了,就民族前途了,然后自己一下子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样的政治根本没把普通人放进去,当然政治是需要设计制度的,但是作为一个几千年被排除在历史外的女性的立场,我就会想到政治的起点,不管怎么设计,都起码不能与人类生活为敌。我们生活中有的东西,政治中才能有,经验中有的东西,制度中才能有。假如脱离生活经验来设计一套东西,就不太靠谱。” 崔卫平虽然反对精英嘴脸,但她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私生活中,而是做了更多承担。只是她不说大话,在兢兢业业地为时代裁缝一件贴身的理论衣服。她说:“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考虑的是思维活动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匹配。”“要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姓的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与道德 崔一直致力于引进东欧思想资源,从最早翻译《布拉格精神》,到后来翻译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其实崔在很久以前关注问题的向度,与哈维尔的写作是相像的。她本身是搞文学评论的,后来涉及到政治哲学,而进入问题的角度也多是道德的和文化的。哈维尔以前则是戏剧家,在成为政治家之后仍然有艺术家思维,而且他否认自己是政治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批评在中国受歧视,道德性呼吁更让制度学者反感,这当然有中国独特的语境。这个独特语境的特点是,许多词语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扭曲,不复是本意,而反对者其实也不一定反对那个词本身的所指,而是反对词义在特定氛围中的扭曲,这个反对也都是策略性的,因此目前的交流困难重重,因为发生了语言的混乱。文化与道德,就曾受到曲解,其实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词语的历史性污染,而忽略了那个词所指的问题本身。“文化太重要了!”崔卫平说。崔后来翻译哈维尔等人,我想一定是有所拣选,有良苦用心的。 崔卫平说知识分子要尽情享乐,这话听来刺耳,但我们该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她说,知识分子往往企望社会大事件,而不愿意过平常生活,这使他们无法理解过平常生活的普通人,也就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要求,而只顾自己的道德感和对豪壮场面的需要。“一个人如果不生活,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别人有生活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的生活。苦出身的人总爱将一些东西称之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再三看不惯,一有可能就要加以扼杀。这不能不说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不知道它们对于造成人的美好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作用。这就像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个性,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思想。他自己经验中没有的东西往往也不习惯别人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脚步要更快一些,尽量发展自己的生活,尽情享受一切美妙的东西。” 崔将日常生活的建立看得很重要,而文化批评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生活的。日常生活中,道德判断和文化品位无处不在,她打击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妄想,其实并不排斥每个个体精神性的建立。哈维尔为他所在的捷克社会所开的处方是道德性的:不讲假话,活在真实中。这不是宏大的制度建设,而是一个细微的道德要求,为什么要这样做?譬如一个工厂出了问题,我们知道问题何在,也知道解决此问题的科学方案,但把方案拿过去,却并不一定得到实行。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并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了其他东西,比如缺道德。而在这个方案未实行之前,人们往往变成犬儒主义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这个方案的不实行上去。而在哈维尔那里,他看到了这个僵化的空间中尚有可作为的地方,那地方就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但它需要个人的道德做配合,这样的热情使每个人都有了价值,每个日常行为都有了意义。 最后,读崔的文章后我有个疑问:“读你的文章惟一不满足的地方,在于对于超验的维度缺乏探讨”。在制度建设和社会层面上,也许需要经验主义,但对于文学或者个人精神生活,超验维度不能说是完全虚妄的。与那场“炮轰”中对崔的报道恰好相反,崔一直反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过分夸张,而其实她对于文学之个人精神性的抚慰和宗教性的价值也很少探讨,英美新批评把文学主要看作技术。而崔在《论道德》一文中则说:“道德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前提上——我们意愿呵护自己。”没有一个更可靠的绝对的根基,似乎道德很难走得更远,而哈维尔似乎是认可超验的存在的。崔卫平是这样回答我的上述疑问的:“我很理解哈维尔在最绝望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都会被记下来,什么东西都不会被遗忘。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信念,我其实能够领略那个东西的美,但是,我还是不使用这个维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很东方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评论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帮你赚钱 |
| 21世纪狂赚钱--绝招 |
| 韩国亲子装,新生财富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39健康网=健康金矿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