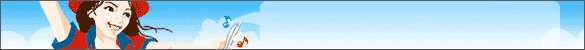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赵武平
一个间接有过交往的老者故去当夜,眼看就要十二点的时候,在广州编画报而久疏联络的朋友忽然来电,询问可否涂抹几笔以作纪念,——早先在光明日报大楼五层邻着图书馆的编辑部滥充编户之民那几年,对面而坐的同事与老先生常有往还,故而他慨然惠赐的散文篇什,以及自题签名的新书毛边本,我也有幸得以先睹,甚至收藏。出于世道嫌他文风散
漫的訾议虽偶有声闻,却不能稍减我平素所怀好感和好奇,况且还有熟识他的友人说过,老人不仅曾经受业“死于台湾的钱穆先生”,而且也与其旧北大师辈知堂先生私人交谊深厚;他寓中尽历劫难而仍庋藏多多的周氏杂著,“凡是刊印过的,由早年的《侠女奴》《玉虫缘》等,到最近的《知堂杂诗抄》和《知堂集外文》止,我差不多都有”,更是我辈周迷心动弥久的至宝。
有一年古吴轩藏书家王君自姑苏抵京,相约分头前趋往访老先生于其城外新居。待我从樱花西街出发,紧赶慢赶冲到说好碰头的地方,性急而先行的来客已从老人寓所辞别而出。彼时他已逾八五之寿,贸然登门再加叨扰总嫌不妥,索性过门不入。因缘不到对面不识,大约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以后,也在热闹场合望他袖手无言端坐,还曾托人求他为一部付印前的文稿题签,但始终无缘与他当面晤谈。
流年似水,一转眼人作古了,不到的因缘永远不会到了。但因其逝而起的诸般耳食之言,却难免牵人想起他缕述前尘影事,坦荡不避自己和革命女作家的情怨纠缠。他淡然谈往忆旧的姿态,远远超出旁人揣度:小说归属子部,情节大小皆可编可造,无须当真而言。浪漫主义的红色经典,在他眼中似乎若有若无;直面物是人非,他无怨无悔,更无憎。当然谁也无法证明,看客的强行附会,给他带有愁郁乃至烦扰究竟有多少,——晚年才与之结识的某公尝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一直有顾忌,因为他是余永泽,他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余永泽,我是瞧不起的,对他我也保持着距离,我怕跟他接触会被人说什么坏话,那时我还是《读书》的负责人。”更有著名话剧院主事者透露,同名电影中余永泽的饰演人选,投拍前非取身材相貌都似人物原型的于是之不可。如此而为目的何在,以及能否以之旁证小说家言是否属实,自然可以推而想之。
并非虚构的小说丑角,和他本人干系究竟多大,徒然空想并无所得;尽管两人当有重叠身影,实乃不争事实。前年偶然徘徊旧书店,意外检出小说家在“做老祖母的年龄”那年所公开的日记,方才看见她似乎还是心存恻隐的。她说:“当年我的爱人玄,本来他非常爱我。当我向往革命,当他不能和我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时,我终于毅然离开了他。当我们分开后,又一次我去看他,他变得骨瘦如柴,坐在一张佛像下,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默,回来吧!我们还在一起吧!……我不能——不能没有你呵!……’他那绝望的面容,他那悲伤的眼泪,使我心如刀割,使我几乎动摇了……他毕竟是我一生中初恋的爱人啊!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年,他在文学上有修养,我们完全可以在一起过着安逸、平静、充满爱情的生活;我们可以‘红袖添香夜读书’;可以毫无风险地共同翱翔在浩瀚的、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图书中……然而,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革命的信念,战胜了缠绵的个人情感。终于,我还是忍心离开了他。他后来对人说过,他几乎为我死去。但当时我又何尝不痛苦呢?当我看到他这样一个大学生,竟像老僧般趺坐在佛像下,‘这全是因为我呀!’我忍不住哭了。”然而先他而往泉下的她未必知道,看去心似止水的他,其实也有衷曲欲与人言:“本诸古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今训‘苦闷的象征’,我也想写小说。因为这种情怀,一是形体恍惚,二是分量太重,都宜于用小说的形式表达,而且要长篇。并已拟定标题,先是《中年》,写定命下的愁苦;后是《皈》,写终于寻得归宿。事实是没有写。不是没有能力写;我自信,有了主旨,正如其他所谓作家,我也会编造。而终于不写,是因为时移世异,这世有要求,表现手法可以殊途,所表现则必须同归,山呼万岁。我的《中年》的愁苦,《皈》的设想,都与万岁无关,行祖传明哲保身之道,只好不拿笔。”显然并非不欲抱怨,只是文网密时不能怨;而到了可以畅言的年岁,怨的念想已从心底消逝。诗自他手出,但已无怨。
“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仿佛于他却是例外;所谓以德报怨,更似可以其言行兼作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