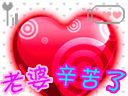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雷思温
今年1月27日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之日,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在绞尽脑汁玩新花样来纪念。要不是莫扎特的健康被他的天才过早耗尽,巴赫和贝多芬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崇高的地位。莫扎特的音乐是最容易被人铭记在心的。巴赫的音乐太过神圣虔敬,虔诚到使人敬而远之,而贝多芬作品的内在冲突太激烈,也没办法让人心旷神怡的慢慢消受。莫扎特
甜而不腻,老少咸宜,无论什么年龄带着什么心情去聆听,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不过究竟什么是莫扎特音乐的魅力所在,一千个人肯定会有一千个回答。莫扎特音乐的影响广泛而巨大,对于普通人而言,他让人心情舒畅,据说还能提高智商;对于音乐家来说,莫扎特高产而高质的创作成果始终无法逾越;而对喜欢莫扎特的思想家来说,莫扎特则拥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这尤其表现在莫扎特音乐的神学意义中。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对莫扎特保持了终身的热爱与激赏。他坦言自己多年以来每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聆听莫扎特,而且还略带调侃地讲到自己死后升入天堂,将首先去拜访莫扎特,其次才去见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和施莱尔马赫等神学大师。不啻如此,在撰写神学巨著《教会教义学》的同时,巴特还抽空写了本小册子《论莫扎特》来阐发莫扎特的神学意义。如今这本著作的中文新版面世,为莫扎特音乐的文化内涵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理解向度。
这本小书收录了卡尔·巴特论莫扎特的四篇文章。前两篇文章为巴特的报刊随笔,其中第二篇是巴特给莫扎特在天之灵的书信,读来饶有趣味。巴特对莫扎特神学意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最后一篇著名演讲《论莫扎特的自由》之中。
伟人对伟人的理解往往充满傲慢与偏见,波士顿大学教授罗森曾言,无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解,还是黑格尔对康德的理解,都远远谈不上公正和全面。然而巴特对莫扎特的理解却是罕见的例外。这位神学大师在莫扎特面前甘愿谦卑。在巴特眼里,莫扎特音乐包含和超越了一切为他所吸收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主题,并且将这些元素轻易地纳入自己的音乐之中,而成为其本己之物(Eigenton)。莫扎特并没有现代艺术的善变和后现代艺术的调侃与消解,他的音乐调性原理并不复杂,永远充满悦耳的和谐。莫扎特深深懂得,任何作品都必须在法则的约束之中方能成功,任何貌似自由而逾越规矩的创作免不了凌乱和浮躁,无法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品格。
有趣的是,巴特总是选择在清晨聆听莫扎特,这乃是因为莫扎特的音乐从未出现过悲剧气氛,听起来舒扬轻盈,充满嬉戏和喜悦。巴特将莫扎特精神概括为“凝重者轻盈地漂浮着,而轻盈者无限凝重地摇曳着”。他的音乐完全没有任何紧张与矛盾。尽管莫扎特终身生活相当简朴,他的天才也使他少有休息时间,而晚年的病痛更是雪上加霜,但这一切都从未在他的音乐之中显露出来。
也许我们会有一大套理论和赞美词语来描述这种精神,但巴特认为所有这种赞美与其说抬高了莫扎特,不如说降低了他的精神品质。因为莫扎特在音乐之中从来不像现代艺术家一般竭力解剖和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情感与处境。莫扎特的生活服务于艺术,艺术却从来不服务生活。尽管他的天才为他赢得了名誉和生活保障,但他在创作时却完全摆脱掉了所有琐屑的生活经验,而将完全自由的精神注入音乐之中。所谓“莫扎特的自由”,就是指他的音乐完全跟现实不沾边,也从来不曾试图为自己的音乐加入政治理念和人类梦想,他的音乐没有哲学。
我们无法指责莫扎特缺乏思想,缺乏对时代处境的必要理解,我们应该庆幸,正是因为他摒除了这些干扰,才使得他的音乐不会因为时代沧桑而有所改变。聆听他的音乐时,我们不需要费力揣摩作曲家的意图、生平和创作理念,只需要带着耳朵去感觉。莫扎特的内心所想只是上帝、世界与人,而没有具体的对象。他的音乐无比自由,摆脱了一切夸张和对立,真正做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道”,即中国古语所谓“中庸”。这一中庸之道是善与恶的巧妙平衡,而决非冷漠的不动声色。
也许这样连篇累牍地赞美莫扎特让人生厌,但又有什么能代替包括卡尔·巴特在内的无数人对他音乐的崇拜之情?令人惊讶的是,在巴特这样的布道大师看来,莫扎特的音乐远比巴赫更纯粹地道,是最伟大的教堂音乐。巴特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所散发出的不仅是充沛的人性,更是光芒四溢的神性。莫扎特使每个人都感到慰藉和惬意,领受到神的温暖与救赎,而没有一丝怨天尤人和无病呻吟。
你可以说这个时代充满喧嚣和浮躁,几乎无法形成定格的画面,但你不能否认在这些纷乱的表面之下还隐藏着春风化雨的传统。巴特在演讲结尾调侃地提到,莫扎特当年在进行欧洲巡演时,竟故意避开了瑞士的巴塞尔,而绕远道经过苏黎士并在那里举办音乐会。作为巴塞尔的居民,巴特由于自己的故乡没有莫扎特的光顾而黯然,而我们这里仿佛也在热闹地纪念着莫扎特,不管是真心诚意还是附庸风雅,却没有巴特一般源自虔敬的朝圣之心。对于一个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中国而言,聆听莫扎特是为了聆听西方的文明传统,而阅读卡尔·巴特的《论莫扎特》则是为了领教他们如何珍爱自己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