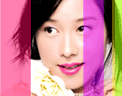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在四川、青海、甘肃交界处的阿坝地区拍摄的电影《王子传奇》,已进入后期剪辑。这是一部根据莎剧《哈姆雷特》改编的以西藏为背景的影片,演员全部起用藏族演员,全部采用藏语对白。导演胡雪桦将原作中的复仇主题作了转移和调整,更注重人的情感、对爱的追求和强烈的宿命感
本报特约记者王寅文/图
凌晨,透过慢慢散去的大雾,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展露在眼前。一队黑色的牦牛在雪地里走过,原野又恢复了寂静。
这是青海久治县境内海拔4207米的乱石子砑口,《王子传奇》开机的第一个镜头就选择在这里,这也是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年轻的甲波王子拉摩洛丹策马飞奔……
10年前,胡雪桦在云南丽江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兰陵王》;10年后,经历过好莱坞洗礼的胡雪桦回国再次执导新片《王子传奇》。和《兰陵王》一样,胡雪桦的这部新作依然钟情于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王子传奇》是一部以西藏为背景的影片,外景地放在四川、青海、甘肃交界处的阿坝地区,演员全部起用藏族演员,全部采用藏语对白。胡雪桦将原作中的复仇主题作了转移和调整,呈现在影片中,更注重的是人的情感、对爱的追求和强烈的宿命感。
雄心勃勃的胡雪桦希望这部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是一部有别于在此之前所有改编版的世界级的电影。
已经结束全部内外景拍摄的胡雪桦正在进行紧张的剪辑,《王子传奇》将于今年春天完成全片的后期制作。
《第一财经日报》:最初想到的就是做藏语原版的吗?就是背景放在西藏吗?
胡雪桦:就是做原版,就是在西藏,不在西藏我就不拍了。如果是搁在一个汉文化的背景里,我就不拍了。这个戏只有搁在西藏这种地方拍比较有意思,它是给你讲生存还是毁灭,在这种环境当中,意义就不太一样。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想法持续了有多久?
胡雪桦:两年。中国的文化分几大块。藏族这一块,我们一想到西藏就想到拉萨,其实是完全错的,它实际上有青海,有四川,有云南,有甘肃,这么几大块形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说过,你感触最深的就是阿坝特别苍凉、原始的地貌。
胡雪桦:我在去年4月份和7月份两次采景,当时感触最深的就是阿坝。阿坝这个地方等于是块处女地,实际上阿坝地区这些景是中国的一个“肾”,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有大量的沼泽地、草地,在这一块儿,草地就相当于人的“肾脏”,很多地方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但这块地方却保持得比较好。我和侯咏看了以后,把主要场景设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一种原始感,很强烈的一种荒凉、原始的状态,跟这个戏很合适。哈姆雷特在询问“生还是死”的时候,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是很棒的。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有层次,不是单一的——就是沙漠、就是荒凉。我觉得选一个戏的景,实际上跟选演员是一样重要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莎士比亚的这个戏被无数的人改编成戏剧、电影。
胡雪桦:莎士比亚是永远读不完的,而且《哈姆雷特》是改编最多的。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觉得你的胜算在哪里?
胡雪桦:在所有人的解释中,最新的解释我看到的是梅尔·吉布森1993年的一个版本,就是哈姆雷特有比较强烈的恋母情结,他是个母性欲望很强烈的人,他要解释为什么母亲在父亲死后还不到一个月就跟叔叔结婚。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每一次改编都把其中某一点放大。
胡雪桦:没错,我觉得我们这个改编也许是最有意思的。哈姆雷特询问这个问题,是个哲学问题。《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哈姆雷特》,因为它像《罗生门》一样,讲一个人的事情,而有各种各样的结果,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哈姆雷特》就是对仇恨与复仇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这后来成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某种心态。有了思考以后,你作决断会很困难,你会想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像哲学问题“生存还是毁灭”、“动作还是不动作”、“复仇还是不复仇”,形成一系列的思考。
我这个戏虽然也有这些,但同时把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调整——哈姆雷特不单单是一个哲人。这个戏里面哈姆雷特基本上是一个17岁的少年,而且他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复仇问题,而是一个情感、血缘的问题,他要杀的这个人恰恰是他的叔叔,这个戏情感的冲突就很强,同时这个戏因为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拍,我又加了一些临界的东西在里面。文化本身是有局限的,什么东西是没有局限的呢?你超越这个界限、国界,就是宗教的精神。我本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但是我对所有的宗教都很敬畏、很尊重,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人要宽容,人要有爱,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戏最终的点就在于权力对人是有异化的,爱是能够修复人的行为的,这应该是这个戏比较主要的一个精神。
《第一财经日报》:有些问题并没有必要在一出戏里给出一个答案,提出问题就已经足够了。
胡雪桦:对,因为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片子能解决的,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可能就在于提出问题。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也有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一些思考,他的一些挣扎,但最终要把这么大一个问题解决的话,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的,他毕竟太弱小,也不是我胡雪桦能做到和解决得了的。
作为一个电影人拍电影,作为一个导演把一部电影拍好,在电影当中说一些你想反映的思想、情感,就够了。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好莱坞工作过,这些经历对你现在拍片会有影响吗?
胡雪桦:好莱坞的经历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这是双刃剑,因为美国的片子比如说它在第10页有个什么情节,35页你翻开,35到40页肯定是床上戏,它有个formula(公式),它有一个配方,这就像麦当劳,你在世界各地吃味道都差不多的,它是一个流程。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你掌握这样一种配方和流程是为了做出你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哪里?
胡雪桦:就这个作品本身来讲,它一定也是具有个性的,为什么?我这个人做东西,它一定是个东、西文化交融的东西,比如说,国外的人看了《兰陵王》以后就说,题材是东方的,它的意念,它对人的、内容的解释实际上是西方的。这个戏实际上也是这样,题材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但是由我们东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演绎。莎士比亚这个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阴谋、权力对人的致命诱惑,它可以违背亲情,我把它调整了,更注重的是人的情感,对爱的追求,包括强烈的宿命感。
为什么我总会说人要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去处?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它还是一个宗教意识。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缺少这种对宗教的询问。
《第一财经日报》:我注意到你在开机饭上说过一句话:要把这个电影拍成一个世界级的电影,你心目中的世界级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硬指标?
胡雪桦:其实我没有硬指标,我就是要拍一部好的电影,能够让世界的观众都接受的电影,不仅仅是中国的观众,不仅仅是美国的观众,而是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接受的电影,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但这个东西有一个指标就是一定是一部好的电影,它不能是一部中流的电影,更不能是一部低档的电影,一定是一部好的电影。
《第一财经日报》:好的电影如何去定义它?比如说好看?有内涵?
胡雪桦:如果我们是从艺术的基本标准来讲,它一定是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它有非常吸引人的故事,非常好的演员,特别有意思的导演处理,特别好的摄影,这样基本上构成了一部好的电影;同时要独特。我觉得艺术就是个性,一定是个性,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造,如果没有创造的话,没有一个新的对世界的读解,没有一个新的对人的读解,就没有艺术。
《第一财经日报》:我觉得好莱坞对你的改变并不是很大,至少本质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胡雪桦:一个人本质的东西是一种宿命,它是改变不了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很多人会自己屈服或者妥协,面对商业、面对意识形态……
胡雪桦: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会知道如何去适应,但他不会改变自己。包括好莱坞一些好的导演。
《第一财经日报》:我记得10年前你拍完《兰陵王》,我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你说拍电影是折寿的一项工作。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这样看?
胡雪桦:对,我还这么看。我觉得只要你拍了一部你用了心的电影,大概少活三到五年。
《第一财经日报》: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么干值得呢?
胡雪桦:因为我爱这个东西,如果在各种艰难的情况下你这个信念一直有,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事业,喜欢拍电影,喜欢做艺术,你就愿意付出。人的生命的长短并不是靠你的年龄来衡量的,普希金(活了)37岁,我父亲(著名戏剧导演胡伟民)去世时56岁,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生命长就有什么意思。有时候你并不是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出来才有意义,你自己要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