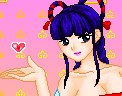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历来的冬天,往往都是英雄歇马、壮士还乡的时候。眼见着报业同仁们的来来去去,反而越来越觉得淡然,有的人彻底离开这个行当,更多人来年春天又加入进来,怀抱着“当代史官”憧憬的青年从来都像一茬茬的韭菜。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这样,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修当代史”的冲动和“道统”。当然,这也是因为现代政治的逐渐昌明,使青年们的憧
憬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三千年“道统”因之续如长河。
在中国,史分官史(正史)与私史。当同一段历史因“述其正朔”的需要而被“宣付史馆”的同时,它往往也会在别处以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有私史的存在——私史就是当代史。
以我们似乎已熟知的中国史为例,努力记录着它的变迁的,看来远不止煌煌一架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虽然当历史已经消散,承载它的只剩下这些纸页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置疑这些“官史”或曰“正史”的巨大价值。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它是否已足够了呢?朝代的更替,最终使“后朝修前朝之史”成为现实通例,本朝和本朝史官对此往往无能为力。无论他们多想“书祖宗之功业,垂后世以追范”,他们关于“当代史”的记述——譬如皇帝起居注、本朝实录等等——都只能为“覆我国者修我史”提供参考。历史之像,总得要假手于人,但它就此已然被“史”这个镜鉴折射了两次,光与色的散失偏移自是不待我言。悬案之多多、翻案之涌涌,谁能说可以撇清这个原由呢。
既然当代职业史官修不成当代史,那么就会有别的知识分子来作,作出来的就是——私史,私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往往直接记录着当代甚至当时。治私史,这个道统之发轫,起始于充满着最旺盛入世情怀的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孔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部已被普遍认定是孔子惟一亲著作品的史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其后这隐然成为一个传统,虽然历代政府对知识分子们的这一行为普遍不快,因为以“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记录些官史所不载的当代“阴暗面”等等,从孔子就开了头。比如,南宋政府颁布的政令就指出——“言私史害正道”,就此开了明令严禁私人作史的先河;到据后来的史书称“文字狱最酷烈”的清代,将私刻《明书辑略》的庄廷珑掘坟戮尸、诛其亲族;王缃绮作《湘军志》,而曾门将帅怒曰可杀,终迫其毁版……
虽然千百年下来,以私自记录、传播当代历史的罪名触讳取祸者不乏其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从来是不缺乏对自身的“公器”期许的,而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他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体现,往往其大莫过于“记史”。把真实的当代历史记录下来、传播开去,正是薪火相传的“道统”之一。而且,社会越是处在变革与动荡之际,这种欲望就越强烈。
正是这些非工具(史官)的知识分子出于春秋道统的自发记录,让我们的历史不再“从一而终”,使后世人对它有了多角度参详、观察的可能。
政治的逐渐昌明、讯息的发达,催生了新闻报馆和以专门记录当代史为职业的记者这一行当。私史与公器、知识分子道统与社会大众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有机统一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方法论而言,私史著者所柄持的“我之目见耳闻、大众之亲历身受”,仍是以真实和公心为基本出发点的记者所遵循的职业指归。而在实践论的范畴,报馆制度和记者行当,为有志于记录当代史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在官修与私修之间多少寻求到一种平衡的可能。
虽然这个行当的特性,使他们往往无法潜心一念、有条不紊地记录所有想记录的变迁,但就像历来私史限于条件无法都像《春秋》、《三国志》、《国榷》一样拥有完善的体例,这并不影响他们因力图准确地记录了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而带来的价值。那些价值,既是记者的职业要求,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所系,三千年未断,今后也会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