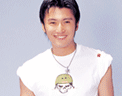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
赵松/文
早在111年前的那个12月里,一位长得与其说像作家,不如说更像美国西部片里冒险家的38岁的爱尔人,在《苏格兰音乐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成为一名音乐评论家》的文章,那些文字在当时不知道伤了多少人的心,它们看上去有点自负、有力、带刺同时也是异常的准确,偶尔还闪现出幽默的天赋。当然,那个时候他还远远不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
个人,甚至也不是到了旧中国与鲁迅他们合影的那个留着一把大胡子的瘦高个子讽刺文学名家,或者说,那时他还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萧伯纳,而是G.B.萧。而那篇充满力量感、洞察力和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似乎是写给同行的文章,如今成为三联版的新书《萧翁谈乐:萧伯纳音乐散文评论选》的前言。
他似乎天生就有着野蛮人的气质,但又非常善于对付那些天真得没脑子的文明人。“‘是什么使您灵机一动想起写音乐这个话题的呢?’于是我就说音乐碰巧是我最了解的一门艺术,故而写之。他们听明白后就走开了,对我这如实的答复大感失望和幻灭,仿佛它使我的成就掉价似的。甚至在我完全不懂音乐的假说逐渐不攻自破之后,仍有人不时呼吁我坦白承认我的音乐知识并不包括技法。我想这些人还漏掉了说我不懂美索布达米亚记谱法吧?该记谱法罗列愚蠢小气的乐句解析练习以唬住一般人,恰如在集贸市场上受过训练的猪的表演唬住了乡巴佬一样。”随后,他又慢条斯理却又毫不客气地敲打道:“一个不懂行的评论家有两大优势。其一,如果他是为日报而写,他就能避开分析,同时又使自己不失有用和有趣,仅凭搜集关于最近事件及名人最有丑闻性的时新消息就行了。其二,他的不称职只能通过把他一个月前写的东西同他今天写的东西相比较才能鉴别出来,而谁也不会为这去麻烦自己。”然后,萧伯纳先生开始嬉笑怒骂地上课了。
他不是为专家们而写的。这个集子里几乎都是标准的千字文章。他的眼光的确锋利如刀,像庖丁解牛,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些音乐外行们以及装出绅士派头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的家伙剥得体无完肤,而又不失幽默与智慧。他的笔锋指向演奏家、指挥家、评论家还有观众。实际上他并不刻薄,他所做的只是用刀背在那些已然赤裸的肌体上轻轻敲打几下也就算了,不过他的漫不经意的敲打,是会让骨头都发出响声的。他的确是个行家,例如,在那篇《地狱在圣詹姆斯大厅》里,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李斯特大师那部关于但丁《神曲》的作品,“我要在此马上宣布,我不喜欢这首交响曲……我还认为我的表达已算是够客气的了……我应该痛快淋漓地证明这首交响曲的曲式错了,其和声进行也是被禁止的,现代音乐的堕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它的影响……过多地几乎是不断地诉诸音色之美,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只有节省地使用,音色之美才能出效果。在别处使用产生过悦耳效果的乐器组合,若碰上这些被超过了限度的管弦乐合奏折磨得要死的耳朵,就只能是噪音一片。”另外,他对“要求加演”的观众也不客气,建议在他们要求加演的时候给大家传递一顶帽子,把加演的费用放在里面,以使他们明白“加演的要求并不是氮肥,歌唱家并不能靠它活着。从道德上讲,剧院内衣冠楚楚的乞丐也丝毫不比外面衣衫褴褛的乞丐更受人尊敬。”
早在1933年,已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G.B.萧游历中国的时候,就没给当时的国人们留下想象中应有的绅士印象,而一向对“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鲁迅,却因萧伯纳面对那些热衷于看西洋景的人们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而对他颇有好感,并且还跟瞿秋白自费编印了一部关于萧在中国的集子。这么些年过去了,伟大的萧伯纳在我们这个国度只是空留个名声而已,很多人都知道他,但他的作品翻译过来的又非常有限,原因或许是他不那么“现代”吧。在多年来惯于暴饮暴食的中国出版界与读者们那里,一向乐观的他实在是太容易被忽略不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