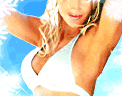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
杨 波
拜伦、皮尔与吉尔
南非摄影师罗杰·拜伦的照片非常有趣,以前只能从网络和图册上找到,却没想到他的作品近日来上海亦安画廊展出,于是得到机会去仔细地,看这一屋子的墙上满是嵌着污
垢的指甲、凌乱纷杂甚至可以发出静电噪声的电线,以及那一双双似乎暗示着“毋宁瞎掉更好些”的眼睛。
之所以说“没想到”,或是因仍旧被前些日子去看“皮尔与吉尔摄影展”时所思所想的影子罩着罢。其中那些人造革似的滑腻到可以发出光的脸孔、万花筒般繁华精巧的背景所呈现的美委实令人喘不过气来——但却着实造成了这个城市里一心要站在潮流前面的人的一大阵欢呼与共鸣。我想,他们或许在梦想得到某种资格,好去发泄那种干巴巴的奢侈与华丽背后隐藏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毁欲望。
于是,很奇怪,当这个城市已如一篇多过一千字的笑话般虚汗四溢时,它怎么还有兴趣用拜伦这样悲哀到话都说不出来的影像来虐待自己?
拜伦展出的这些照片,均取自他最近出版的两本摄影集:《尽头》(Outland,2001)与《暗室》(Shadow Chamber,2005)。这两本书的风格几乎一模一样,图片内容全部发生在一个逼迫人患上封闭恐惧症的狭小空间里,黑白,描述人与动物、人与静物的关系,也有干脆的静物图片。其中的动物都很干净,人与环境则极其肮脏。关键是其中这诸多事物之间的排列与相关是完全不合常规的,譬如在一幅名为《午餐时间》(Lunch time)的照片里,那个将上唇用力翻起、也不知是在剔牙还是做其他什么的青年男子,裸着上身,面前的盘子里有一条小到不成比例的死鱼;《藏在上衣里的头》(Head Mside Shirt)所呈现的是,一个男孩把头尽力俯下,深深地藏在身着长袍的下摆里,忽地看去,他就像没有头颅一般。
除了《藏在上衣里的头》之外,他的另两幅作品《歪面具》(Skew Mask)与《野孩子》(Wild Child)中也有男孩出现,然而他们的面孔全部被面具遮住——不禁要问,摄影师为何要几乎刻意地隐去这些孩子的脸呢?我想,那是因为孩子的五官与表情,很难具备他作品中那些成年人的神经质;一个再丑陋的小孩,其眉目间也会自然生出由无邪促就的美来,而这种美,与拜伦所强调的风格恰恰相悖。
构成拜伦作品里的一切东西都令人极不舒服:人物干瘦,面目怪异,皮肤上长着癣斑;他选择的动物也尽是老鼠、猪或死鱼这些叫人生厌之类。若将皮尔与吉尔作品里那些美丽的人与物件看作不食人间烟火之所的产物,那么拜伦的照相机则一定烙着“地狱出品”的标识。再向深里去,你却会发现前者是在用塑胶模特般的质感来刻意抹去人性的可能,后者则反过来——他对人投去的眼神尽管是蕴着痛恨甚至绝望的,但总归目光如炬。
无疑,拜伦比起皮尔与吉尔来更为人本位,虽然后者没有出品过一张没有人物的照片,而前者则拍过许多纯静物或动物的作品。你会发现,拜伦照片里的那些箱子、插座、电线、似已腐烂的毛皮玩偶或裂开并被涂鸦的墙壁,甚至人物本身,都呈现出被人使用过度后滞留的残像。无论他描述出来的人间如何怪异不实,却一定是地道的人间。他尽可能简约地构图,极少的物件却渗露出几近饱和的意象。这些,与皮尔与吉尔因饱和而单调、因绚烂而枯燥的风格形成对比。
拜伦或者皮尔与吉尔,他们皆是以霍克斯为代表的欧洲摄影摆拍派的后裔。但拜伦作品尽管摆拍,却也保证了对现实景况的忠实拷贝,这当然是他坚持住了摄影本质的一面——不像皮尔与吉尔在摆拍之后,还要在电脑上做复杂的后期处理。
不管怎样,摆拍即意味着制造假象——当人去为另外的人制造假象时,这个人就成为我们经常讲的“骗子”;但当一位摄影师去为另外的人制造假象时,那么他则可以被尊称为艺术家——那么,终于还是找到了这两个摄影展的相同之处。
意义、废话与艺术
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个观念艺术家,或干脆说任何艺术家,当他向观者解释其作品的“主题”时,最容易暴露了其作品的缺陷所在——这在我读两个月前一本欧洲艺术杂志对拜伦的访谈后想到。
这篇访谈中的提问者像极了小学语文课老师,他一直在要求拜伦为其作品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来,回答者却也很听话地说道:“过去20年里,在我作品中,毁损与溃败一直引人注目。我对人类生命过程的基本观念是,在控制我们的混沌的力量之后,人自身亦拥有一种永恒的反力。我所创造的隐喻并不是干脆的呈现,它更是一种反抗,暗示着人类与混沌之力量与现实秩序间默然却残酷的斗争。”
那么,他的回答一点也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令他的作品也猛然似乎枯燥呆板了许多。原先那种精妙的神秘主义、乱伦式的混乱逻辑、在暗中发笑的病态表情等等不明确的构成全部明确起来,而这种不明确,我想,却正是其美学的根本。在再没有人谈论艺术与酒神之间关系的时候,假如杜尚站出来向人们解释那台小便器的文化价值,这怎可令人忍受?我更愿意相信,那些令其作品意义明确起来的解释——就算是艺术家自己说的,亦全部是连他本人也拿不准的废话而已。
艺术首先是,或极端地说,惟一是美学。而意义既不是美学的灵魂,也不是美学的投影,它更像是美学不见也罢的远房亲戚。相信会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论调,特别是那些设计国旗或纸币的人民艺术家——但我确信,这是对待艺术最为深情的一种审美向度;同时也找到了你可以喜欢作品本身却完全可以对作者予其作品的形而上诠释投以轻蔑的原因。
果然,等到那篇访谈的最后,拜伦已几乎无措于对方对“中心思想”的一再追问,并不禁恼怒起来——当问题变成“究竟你作品里的那些病态和死亡气息所从何来”时,答案也就被硬邦邦地掷出来:“当你每天早上起床后走到街上或翻开报纸,你从中感到的‘病态和死亡气息’要比我照片里那些多得多!”
好吧。
但人们到底为什么偏要认为了解一位艺术家的世界观对欣赏他的作品有益呢?
现实、时间与美学
访谈中拜伦对其摄影操作模式的解释,人们可以看出当摄影成为艺术时其本质遭到了怎样的误读与暗算。拜伦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艺术家是毕加索、米罗和亨利·摩尔这些超现实领域里的画家与雕塑家,基于“他们作品中深刻而复杂的寓意”,他接着说;“最近几年,我看得更多的是油画和雕塑,远远多于摄影……”
无论用于实用或艺术,摄影的本质永远也只能是两点:现实与时间。简单些说,一张照片的所有功能不过是:将现实的一瞬定格并存留,摄影的一切价值皆建立在这个上面,包括它成为艺术后必须要创建的美学价值。
拜伦通过摆置制造的“假象”,当然是艺术的假象,同时更是现实的假象,是对现实的反刍,你说它比现实更现实也未尝不可。桑塔格曾说:摄影是惟一天生超现实的艺术,因为“植根于它所创造的那个被复制的、二手的、具备意外之美,更为狭窄于是更富戏剧性的现实世界之中”。
一个着意于美学或观念的摄影师也一定逃不过作为记录者的第一身份,其次才可能是艺术家。在照相机,哪怕是拜伦或皮尔与吉尔的照相机前,美学也永远站在记录之后,站在对时间与现实的复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