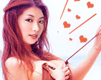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裴谕新
自从我做了性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关于年轻女性的恋爱、婚姻、职业发展等等的研究。只不过这一切,很遗憾的,我觉得从她们性生活方式去看更为有趣——我发觉我的朋友们对我总是暗含了一种期盼:就是希望我的私生活从此狂野起来。比如,他们会很幽默地问:听说你“亲身调查”啦?一旦我对他们的暗示加以反驳,他们就会不屑地加上一句:“
我X,还女权呢。”
那我就讲一个女权的例子吧。
前一段时间我的教授聘了一个研究助理芝芝,聘她的重要原因就是她长得漂亮。这个研究助理的任务是混进歌厅,和舞小姐交朋友,以便调查她们的“多性伴”现象。教授做这个课题其实有她的目的性所在:她想知道,近来在西方后现代女权中流行的“开放式多性伴关系”,在香港有没有现实可能呢?比如,这些舞小姐会不会告诉她们的性伴:其实你只是我裙下之臣中的某一位?
芝芝的课题还没有太多进展,自己的生活先出了乱子。原来芝芝是有一个男朋友的,男朋友忙的时候,芝芝就会有“备用男友”顶上。在芝芝的生活伦理里,“备用男友”不会伤害到男朋友。因为第一:她和“备用男友”只是搂搂抱抱的关系,甚至有一次他们开了房,最终仍然没有“真正的做”,那自然是因为芝芝坚持不做的缘故;第二:芝芝会把“备用男友”藏得好好,让男朋友永远不知道,所以永远不会对男朋友造成伤害。有了这两条生活伦理,芝芝在男朋友和“备用男友”之间过得好不逍遥自在。
可是女权主义一上来,芝芝的生活就乱套了。因为芝芝越是学习那些理论,越觉得其实“开放式多性伴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无隐无瞒,坦坦荡荡,多好!女人为什么就要生活在欺骗中?为什么不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就像她访问的那些舞小姐,她们就是谁的男朋友越多越引以为荣的。
理论给芝芝壮了胆,她首先破了“备用男友”第一禁忌:两个人又去开了房,上了床,而且“真正的做”了。接下来,第二条守则也突破:她选了一个自以为合适的时机,向男朋友“坦白”一切。
你可以想见那种结果——男朋友不断地追问:When? Where? How? Why? 芝芝发现,自己每一步的坦白,造成的都只是更进一步的伤害。
两个人纠缠着,最终还是要分手。芝芝不堪其烦,辞了职,离开香港去了另一个城市。临走前她问我:“你看过那本开放式性关系的书吗?”这是教授叮嘱我们的必读之物。芝芝的功课显然做得不好。直到这个时候,她还没有真正读过那本书。她不知道,书的作者是个美国人,同性恋。
有一个回答可以对付所有倡导我“亲身调查”的建议:如果我研究暴力犯罪,是不是自己先要杀个人?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太过强烈,不符合我一贯的作风。实际上我常常这样说:“你知道吗?女权有很多种。我是中国式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