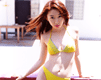|
童月
常去一家药店买煲汤料,久了,和店员及店猫都混得烂熟。俗话说: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说的是养娃娃需让他多见人,娃娃不认生,嘴巴甜,讨人喜欢;养那种看家护院的狗,最好别让它见生人,略略有个风吹草动,狗才叫得凶。养猫也一样道理,这只“大营子猫”,见惯人来人往,见谁都咪咪叫着贴上去,拿脑袋蹭。有资料说猫这是在往人身上“涂
香水”——它耳朵旁边分泌的一种独特的气味,借以向别的猫表明:此人甚好,归我了!
有段时间店猫失踪了足足一个礼拜,再回来时,有些黄瘦。店员意味深长地说:春天了呗。我说,恐怕已经怀孕了。要不要拿只验孕棒测一下?店员大笑,把猫翻过来,仔细检查它的小屁股,说,肯定有了,都不是小姑娘猫了。
我抓狂:难道猫也有处猫膜?
隔了将近一个月,再去那家店,不见猫,据说去分店出差了。我对店员千叮咛万嘱咐:给它吃点幼猫猫粮增加营养;猫怀孕两个多月就能生,要是看到它四处叫着找隐蔽处,八成是快了,提前准备好纸箱子……
我对一切可能孕育着生命的东西感兴趣:怀孕的母亲、种子、插土能活的柳枝……忘了哪本心理学书上说,小孩子拆开中国套盒、八音盒等一切“内有乾坤”的物品,源自一种成长的焦虑:他急切想知道自己体内蕴藏的是怎样的一个未知的“自我”。我的小时候,这种焦虑却表现为一种“种植”的渴望。
种过“太阳花”,老家俗称“死不了”——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好活的东西。拿花盆种似乎有点不搭调,最好找个残破的木箱子,铺好土,撒种。种子只有英文句号大小,每天浇水,有个三五天的样子,土上微微起了一层红雾,仔细看,是一棵棵细苗。不到一个月就能开花,每日一朵,日出开,日落败。开到入秋,颓了,烂烂的像一种叫马齿笕的野草。但种子还在长,熟了便炸开,一粒粒落到脚下的泥土中。此时种植是一件省心的事,一年工夫,换来数年花开,直到那箱子被丢掉。
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是花生。当年播下种子就遗忘,只因那块地临近水管,常年湿润,一不小心便长成一大棵。秋季,父亲替我收割,一铲下去,竟是沉甸甸一大串花生。只可惜掘早了,壳子里还是一泡嫩水。
最近,也许是源自想为人母的渴望,重新种植。在花店里千挑万选,花10元买了一袋“跳舞草”的种子。种植方法极其复杂:先用细砂土磨去表层蜡质,再放到50度温水中浸泡24小时,看到种子露白,才可播种。依法炮制了8粒种子。播种第二天,花盆正中央即冒出一棵小芽。欣喜,又有些疑惑:资料上不是说,播种3-5天发芽吗?第三天,又一棵小苗出土,和前一棵却全然不同。疑惑更大,不知孰真孰假。好在第五天又发芽两颗,均和第二棵相似。3:1,我判定最早出土的是野草。想想任何生命来到世间都不容易,任它生长。出土之后阴雨不断,跳舞草热爱阳光,阳光不在的日子,它们先后枯萎。而那棵野草沐浴春天的雨露,茁壮成长。至今,花盆里蓬蓬勃勃的一大棵,已抽出了花穗。不知道名字,但校园路边,满地都是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