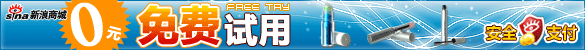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吴晓波:以企业的名义记录历史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1日 11:28 国际航空报
本报记者 陈晓颜 对话语录: 真正好的企业家是老乌龟,每年身上都要涨一层茧,壳很薄的时候,一踩就烂了,老乌龟就踩不坏,而且爬得慢,生命力有5、600年。 中国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有原罪感,因为他知道我是在突破现有的法律,同时又有高尚感,因为我是改革的先锋。 艾森豪威尔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条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这个职业还能活下来。 写企业史对企业家没有好恶感 本报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机缘下开始着手研究并撰写企业史的? 吴晓波: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哈佛商学院有个企业学史教研室,有很多知名教授,也有很多历史书,很多企业家传记。但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他们问我有没有一本书,能够讲中国企业历史的,或者有哪些好的企业家传记,我发现都没有。后来,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口述室,象洛克菲勒等一些企业家老了会把自己的历史讲一遍、留档,作为别人帮他写回忆录最基本的原始材料,这在中国没有。因此,2004年我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史,我发现二三十年下来,没人给这段历史断过代,你不知道这三十年历史该怎样分代,也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我又觉得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还要举办奥运会,那时候民族情绪会很高涨,大家会回顾。当时肯尼迪学院请我去做一个中国民间公司成长历史的研究,2004年离开的时候,跟他们签了协议,做这方面的东西,回来后就开始写,就写成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本报记者:一般情况下,企业不愿意把核心的内容向媒体或企业之外的人披露,你是怎么获得第一手资料呢? 吴晓波:第一,我是1990年开始当记者,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当记者14年,写过专栏、也写过书,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已经写了9本书,十多年接触很多企业。第二,写书一般不会受第一手资料所局限,你回过头来想,清朝写明史的时候,哪有第一手资料可参考。而且,现在其实是个档案社会,记得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王石当时讲中国入关后,房价跌15%,事实上涨3倍都不止。所以,当我写到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企业家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我就以王石为例来讲,这完全是反向的判断。整个社会,尤其是公众企业大量的东西是被档案化的,我可以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相关信息,最辛苦的是把老报纸、老的书拿回来重新翻检一遍。 本报记者:你曾经也说到过写作底线的问题,你怎么既保证阅读价值,又不把企业的商业机密泄露出去? 吴晓波: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没这个问题。在选材的时候,关于事实本身的东西我叙述比较多,我发现自己写了很多年后,现在对企业家没有好恶感,不会因喜欢他而写得特别好,也不会因不喜欢他而不好好写他,不会在价值观上来判断他,尽可能避免主观的东西。 本报记者:中国经济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通道,那么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机遇是中国处在一个高度成长的通道里,过去27年里GDP每年保持8%到9%的增长速度,这在过去100年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但中国企业家每天面对的都是从来没见到过的局面。创建公司就像爬楼梯,而在美国做企业,企业家本身受过良好的商学院教育,商业法规又完善,在2楼他就可能知道7楼是什么风光,而中国企业家在爬楼时,他在20楼时就不知道21楼是什么风景,所以中国企业家搞企业风险大些,成功或失败的偶然性大。 本报记者: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企业的总裁跟你沟通,认为你对他们企业的观察和分析比他们本人还要深刻? 吴晓波:当然,我肯定比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在那玩游戏,我在旁边看,比较客观。做企业跟做人一样,企业家个人张狂,这个企业也一定很张扬。有些人还能自我反省。我曾经跟潘石屹聊天,我问他:你有10个亿身价的时候,人家叫你小潘,现在你有140个亿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公司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上市以后,我有两个礼拜没搞清楚我叫什么名字,有点懵了。后来我去见了一个智者,智者跟我讲了两句话:第一,什么都没变,你还是潘石屹。第二,管理好你的时间。我在《大败局》里写的,很多企业是自然死亡,是行业的问题,但很多企业是崩塌式死亡,那就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潘石屹虽然看起来很张扬,但他很清醒,他本性也很谨慎。真正好的企业家是老乌龟,每年身上都要涨一层茧,壳很薄的时候,一踩就烂了,老乌龟就踩不坏,而且爬得慢,生命力有五六百年。 企业家不是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你的《大败局》,对很多明星企业家的案例做了分析,那么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带给你怎样的震撼? 吴晓波:我写书的时候,其实已经准备了二三年的材料了,所以在写的时候已经不太会有什么感情波动了。而且,企业看多了,我知道一个企业生死都有它的逻辑存在。另外,德鲁克讲过,一个好的企业家或好的公司其实是很寂寞的,公司管理是很无聊的事,当公司发生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事情时,公司就异常了,这是很多做企业的人没有想通的问题。很多人觉得企业就应该生龙活虎,风生水起,其实,如果一个企业做到风生水起的时候,离死已经差不多了,你看看这几年,喜欢讲大话、抛头露面、做重大决策的人,他的企业十有八九最后都衰落了。 本报记者:我们常说创业是需要激情的,但你曾经说过一些企业的死亡也源于激情,那么你认为企业如何把握“激情”的度? 吴晓波:这是最难做的问题,企业家一般都有工程师性格和赌徒性格,工程师性格只能按部就班地做,但你若按部就班,充其量只能当个副总,做企业还要有个冲动,就像男人的野心一样是不可遏制的。企业家有一大半是天生的,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很多人不适合做企业家。赌徒性格可以使他以小博大。打个比方,人和狼、狗的区别在哪儿,一块肉放在那,狗是不会思考的,看到猎物就会无顾忌地扑上去把猎物叼走,这就是动物性。而人是会思考的,这块肉是不是我的,这是不是诱饵,这是否道德,他会想很多问题,等他把问题想清楚了,肉已经被一群狼叼走了,这就是狼文化和人性的区别,但你要是狼,每次都这样扑肉的话,难免有一天会被肉毒死,这就是企业家做选择的难处。我认为,企业家首先是条狼,在不断赌的同时,要想到节制、要有道德底线、要考虑风险问题。 本报记者:你认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吴晓波:首先,我觉得企业家要有很强的冒险性,他敢于去尝试,他某些方面动物性比人性大;其次,企业家逻辑思辨能力很强,如果企业家是个很感性的人,他做企业是做不好的;第三,企业家体力要好,做企业很苦,企业家多数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在很多企业里,企业家一定是饭量最大、睡觉最少、朋友最少的人。 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往往把道德放在首位,判断是非,企业家则把得失放在首位,不是说企业家不讲道德,企业家也讲道德,但企业家为了利益会轻易穿越道德底线。我曾写过一本书———《被夸大的使命》,讲到企业家是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在中国不可能存在儒商,是儒就是儒,是商就是商,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知识分子,如果重叠的话,公众和舆论就会把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责任强加于企业家,我认为一定要把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剥离开。 本报记者:华旗的老总曾说过,在中国做企业家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怎么看? 吴晓波:他讲的没错,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突破现有的法规,中国的改革是企业家和民众从下往上突围,突破后,政策从上往下追认,追认其合法性,中国的法制就是这样被不断地完善。你在突围的过程中,中间有个过程就是原罪阶段,中国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有原罪感,因为他知道我是在突破现有的法律,同时又有高尚感,因为我是改革的先锋。 本报记者:您怎么看企业家的原罪? 吴晓波:从这样分析来看,所谓的原罪,都是制度的原罪,不是人的原罪,如果法律足够好的话,人是不愿意犯罪的,每个人都有恶的念头,但法律能遏制人恶的念头。 不愿当官、办企业,我只会写字 本报记者:作为财经作家,有没有考虑像梁凤仪那样写商战小说? 吴晓波:不会的,我写到现在为止,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不会虚构了,丧失了虚构的能力。 本报记者:前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一个图书方面的《福布斯财富榜》,郭敬明、余秋雨都名列其中,你关心这个排行榜吗? 吴晓波:我似乎跟这个排行榜没什么关系,我的书才卖10几万册,他们的卖100多万册。我07年出了3本书,加在一起卖了30万,版税一共90万,这个行业赚不了钱。 一个神父讲过一句话,人什么时候是幸福的,一辈子做你喜欢做的事,这件事顺便还让你有钱,第一点我们做到了,但第二点很可惜。我在财经写作里已经算是全国前几名了,但从财富角度来说,还不如我的房子每平米涨100块钱的收益大。这是可悲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 吴晓波:我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所有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就会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财务问题,第二个是职业有个天花板的问题,特别是媒体这个职业,很容易碰到天花板,你做了五六年后,就会发现自己没进步了,总在跑新闻。 上大学时,艾森豪威尔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条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这个职业还能活下来。当我财务问题解决以后,我的心态就变得平和了,我在研究企业的时候更加客观,能够保持我的立场。 所以我比较得意的是,我30岁的时候,就把财务问题怎么解决、职业问题怎么解决想清楚了。30岁后我就很少焦虑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看清楚一点,这个职业不会给我带来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我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职业,帮别人写软文,人家给你几万块钱,尽管也可以完成原始积累,但很丢脸,没底线了。我是搞财经的,长远的一些问题能看清楚,我认为,中国土地最值钱,房价会涨,所以从那个时候一年买一套房,坚持了10年,包括在千岛湖买了一个岛,财务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所以我现在写东西不怕人家跟我打官司,大不了我赔一套房子。 媒体人最后有三条路好走,第一是记者、编辑、主编、最后是管理者这样一条轨迹。第二条把媒体当作跳板,到企业去做分管文化的副总裁,或去开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把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套现,这也是一条很好的路。第三条就是还在写字,一辈子都在写字,当专栏作者或作家,我不愿意当官,我也不愿意办企业或为企业服务,我只会写字,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年蓝狮子发起人是6个,刘州伟、秦朔、胡泳、赵晓、刘韧,他们后来都当总编、做经济学家,只有我还在傻呼呼地写。 困难的阶段是我2004年写《激荡三十年》之前,有1年到2年比较困惑。我写完《大败局》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那时候就面临很多选择,很多人建议我开咨询公司、到大学教书,但我又觉得这些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懂管理学,只能讲案例,我又不是一个演讲型的人,我是一个写作型的人。2004年以后,我开始写《激荡三十年》,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不需要每天去完成任务,人的痛苦在于你要不断选择。因为诱惑、焦虑造成人一直处于无法满足的状态,那么怎么办呢,我给自己布置个任务,3年完成。虽然很辛苦,写60多万字,还开着几个专栏,再管理蓝狮子,但我没有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人在35岁到50岁之间最快乐的事情是给自己每隔3年到5年布置一个任务,就怕半年任务完成了,又要面临选择,很痛苦。 老了到岛上去当农民 本报记者:你对现在的生活是否很满意? 吴晓波:我很单纯,除了写字我什么都不会,第二个,我的专业很窄,没什么人竞争,《激荡三十年》写完之后,我会花两年在2010年之前写完1870到1970年这一百年的历史,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以后我还会每隔4年写一本《大败局》,我觉得4年会死10个企业,很有特点,55岁之前就基本上安排满了。 其实,50岁以后,这个社会就不需要你了,因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你写字的方式已经被淘汰了,就像我们看巴金的小说一样,那是前一代人的写作方式,我们已经不用这样的方式写了。到我们50多岁的时候,30多岁的小孩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我们写东西就是为了传播,人家不需要,我就不写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岛,老了就到岛上去当农民。 本报记者: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吴晓波:我女儿快14岁了,要移民加拿大。2011年之前我要把激荡一百年写完,我太太要做世博会,然后我们移民加拿大,陪我女儿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们必须回国,陪双方4位老人。他们都70多岁了,我们要陪着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把他们一个个送走,那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也就50岁了,我的职业生涯基本结束了。现在如果没有东方卫视那个《中国经营者》的栏目,我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退休状态,蓝狮子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把股份稀释给我的很多管理人员和作者,我是第一大股东,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就是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出版平台,让大家都能发财也做点有尊严有理想的事情。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的爱与怕》,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吴晓波:我们这代人受了很大的存在主义教育,我进大学是86年,那时候存在主义在中国刚刚兴起。复旦又是一个人文气息很浓厚的大学,那些哲学对我们影响很大,总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梦想活着,但我们跟老一辈人比较起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包袱。现在80后的孩子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我们那时候没有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压力,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夹在中间的,各有好坏。另外,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单位,然后能分得一套房子,在IT界,马云他们都是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就迎来了互联网兴起,新的行业诞生,媒体界也一样,各大媒体的老总也都是我这个年龄,因此我们赶上了很多好的机会。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新浪财经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