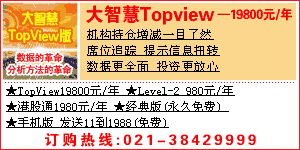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中国另类城市化图景:到县城去买房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3日 10:29 中国新闻周刊
说起中国的城市化,人们眼前通常会浮现这样两幅极端的图景:数亿农民困守土地,被城市拒之门外;抑或栖身特大城市,无固定居所和职业——其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随时提醒人们贫民窟形成的可能性。 还有另外的选择吗? 近一段时间,中西部县城房价出现上涨趋势。在所谓的推手中,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引发了如下关注点:这个人群的规模会持续扩大吗?会成为一种潮流吗?其所代表的趋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新可能。 接下来的问题是,尽管乡村人口在向市镇集中,但现行各种制度安排却并不与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镇被权力制约,无法建立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的治理架构,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建设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配套,小城镇发展会不会重蹈大城市发展的覆辙,尚难逆料。 去县城买房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开始涌入县城买房,是中西部县城房价上涨中最有意味的现象 ★ 文/杨龙 正当人们的目光紧盯着大城市的房价时,那些蛰伏在中国中西部的县城,房价正在悄然而快速地节节上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年前还徘徊在每平米几百元的县城房价,正在大面积突破2000元关口。 伴随房价上涨的,是县城的急速扩张。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场逐渐兴起的扩县运动? 走,搬进县城去 慈利,湘西一座10万人口的中型县城。 到处都是新建的工地。高耸的铁架、轰鸣的机器、忙碌的工人,是这座小城常见的风景。在10平方公里的城区内,仅10月份就有7个楼盘在同时对外销售,待售新房超过1500套。 这一天正是周末。县城刚下过雨,正在修建的火车站广场上满是泥泞。52岁的修鞋工陈金英带着板凳坐在潮湿的广场台阶边,眼睛来来回回紧盯着过往的脚步。她告诉记者,她女儿家新买的一套90平米楼房,就在广场边即将完工的一栋七层楼里的第三层。明年这个时候,她就会住在里面专心带外孙了。现在她每天一边擦鞋,一边看着自家的房屋一天天成形。 陈家的这套房,是以每平米1780元的价格买下来的。共花了15.3万元,首付6万元——三年前,这笔钱可以在当地繁华地段购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三年之后的今天,它只能付房子的三成首付了。现在县城房屋均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 房价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繁华地段的楼盘更是紧俏。县城中心申鸿华都售楼处工作人员周捷向记者介绍,该楼盘开盘不到两个月,170多套住房已卖出八成。 周捷告诉记者,他们的购房者中有四成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还有三到四成是附近乡镇的教师、公务员。他们分别构成了涌入县城的两个主要群体。 一个县城的扩容“三步曲” 慈利县的“买房运动”经历过三个阶段:先是本县居民买;接着是县城周围乡镇的公务员们进城买房;再后来,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开始涌入。 慈利第一栋公开对外发售的商品房出现在2001年,那是一栋六层楼高的橘红色建筑,一层是商铺,上面为住宅。当时住宅的价格为每平米600多元。据慈利县房地产管理局产权产籍股张文革股长介绍,那年买房的基本都是县城里的居民。 此前,慈利县本地的房地产商都认为这种开发挣不到钱,结果让邵东来的一个做皮包生意的商人接手了这个楼盘,从慈利掘走了他的第一桶金。这下,众多开发商看到了商机,周边石门县、常德市的开发商涌进,陆续抢占地盘。 慈利县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代侨玲告诉记者,2004年,政府开始鼓励旧城拆迁,改造商品房,县城出现房产开发热潮。这一年,县城内的商品房累计销售1500多套,县城开始逐步向东边扩展。此时,县城居民的抢购热潮过去,乡镇干部、教师开始大批进城购买住房。这时县城的房价已上涨到每平米1000元。 退休教师吴香庭就是那年买的房,那套房的价格为12万元。虽然花掉老两口所有的积蓄,但老吴两口子还是认为很值得。他们买房,首先为的是方便孙子以后在县城读书。现在,孙子已经开始上城里的幼儿园了。吴香庭的妹妹一家随后也在县城买房,搬进县城。吴香庭笑道:“都说老了落叶归根,我们一大家子,老了却都在往外面搬。” 从2006年开始,先后有7家江西的房地产商进驻县城。县城内,每条街都能看到工地围墙,有关楼盘的电视广告、路灯广告、大型户外广告牌开始铺天盖地席卷县城。据代侨玲介绍,从这一年开始,外出务工人员也加入了购房大军。 陈金英一家就属于这“第三次浪潮”的购房者。她的家乡在离县城15公里的零溪镇,她的丈夫、女儿、女婿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女儿向春生了孩子,他们便决定买下县城火车站广场边刚开盘的一套房子。 几年来,这两股进城的人群在县城内交汇,使这个小城慢慢扩大。与2000年相比,城区面积已由5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慈利县主管城建的副县长邢川告诉记者:五年之内,县城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城内居委会由6个增至9个。 县城开始快速向东部以及北部扩张。县城东面,已建起了一个容纳近千户居民的大型社区,三栋16层楼高的电梯公寓出现在县城的东边——此前,这里还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建筑。县城的触角也在悄然延伸到河北岸。那条宽约500米的澧水河,曾是县城和农村的分界线,背着背篓的农村人多年已习惯于乘坐木船往返于城乡之间。现在,一条四车道的大桥正在连通城乡,当地政府计划将城区北扩,新移民们将逐渐迁往澧水河北岸这个总面积达一万亩的新区。 天然的沟壑不再成为城乡的界线,各乡镇的方言也都在县城内汇集。湖南地方方言历来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说法,县城西街的菜市场上,操着不同口音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为什么是县城 慈利县副县长邢川说,湖南毗邻广东,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仅慈利县每年就约有10万农民工南下广东。多年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攒下了一些钱。 老一辈的外出打工者们会用在城市里面挣来的钱回农村盖房,村里的平房渐渐换成贴了白瓷砖的楼房。陈金英的丈夫在广东打工几年,在1996年,在村里盖了自己的两层小楼。陈金英记得,夫妇俩拿出了积攒的3万元钱,再向亲戚借了两万元。为了还债,农闲的时候陈金英便来到县城,在火车站旁擦皮鞋。但年轻一代却不愿再走父辈的老路,更倾向于进城。陈金英的女儿就说:“我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回农村。” 因此,县城买房的打工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种过田,他们大多读完初、高中,便汇入南下打工大潮之中,在城市里谋生。他们不会种田,更不愿种田。 但在大城市里,凭靠劳动力所换取的微薄收入,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那里。为了多挣钱,向春和丈夫每天都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1个小时,即使这样,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是不到4000元。“在深圳,就算不吃不喝打一辈子的工,我们也买不起我们现在县城里这样的房子。”向春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现状。所以他们选择了在房价相对低廉、生活也不陌生的家乡县城买房。他们愿意趁着年轻,在大城市里挣点钱,积累点资本,然后回到家乡的县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做点小生意,过踏实安稳的日子。“相比起回到农村老家,或者是在大城市没有房子的生活,县城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少这里有个安稳放心的住处安顿家里人。”向春抱着儿子,很满足地笑着对记者说。 另一个促使打工者回到县城扎根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土地和亲情的依赖。大部分农民都有一种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结。向春没想过在更大一点的市区安家:“在县城买房子,不太贵,离老家近,熟人多办事方便。”母亲陈金英对家乡的土地也是念念不忘,“我老了,还要时常回去住一阵子,搬得太远了不行,什么人都不认识,不习惯。”尽管将家搬到了县城,当地农民与乡村的关系也并没有脱离,他们与农村的亲属依然保持着密切往来,农忙的时候甚至回去帮忙干活。 向春夫妻决定在县城买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县城房价的节节上涨。“与其从现在起把钱存进银行,还不如买这里的房子。” 从2005年起,向春就有了回县城买房的打算,那时,城中心的楼盘不过每平方米1000元。但这个价格让她觉得有点太高了,同样的价格足够在农村修一栋气派的楼房,“那时总觉得房价贵,手头的钱也不够,想等便宜点再买。” 然而两年过去了,面对一路飞涨的楼市,和大多数持币待购的买房人一样,向春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了。如今县城中心的房子刚开盘,她就痛下决心,买了一套3室的房子,这不仅花光了他们夫妻俩多年来的积蓄,还让他们背上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银行贷款。令他们略感欣慰的是,县城的房价还在上涨,他们所买的房子依旧在不断升值。 涌向县城的迁移潮中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乡镇干部和农村教师。他们从农村走出,求学几年,选择了回乡镇就业,却并没有选择回到乡镇安居。 这些乡镇教师和公务员每月都有近1500元的稳定收入,乡镇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将来的事业发展、子女的教育以及医疗、交通等问题。显然,县城显然更符合发展理想,也更适应他们的消费能力。尽管工作地不在县城,很多人还是会倾其所有在县城内购房。 在距县城十几公里远的一所农村中学里,有二十几个农村教师都在县城里买了房。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平时住学校宿舍,周末回城里的家。一位男老师无奈地对记者笑道:“我和我媳妇在城里买了个‘卫生间’,每个周末就过去打扫一下卫生,睡一晚上,再用一下城里的卫生间来洗个澡。” 县城房价上涨的蔓延之势 慈利属于张家界市管辖。与县城的房产发展速度相比,张家界市的房价则显得平稳得多。据张家界市房地产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四年前,该市的房价每平米就已近2000元,但到现在每平米也不到3000元,涨幅只有县城一半。张家界一建筑商吴远征认为,现在是农村里面的人往县城走,县城里面的人往市里走,市里的人往省城走。但县城人并没有农村人的自由度,他们受工作、家庭的牵制太多。所以这种人口的迁移并没有像农村人口流动那么惹人注目,市里的房地产业也因此不及县城发展迅速。 记者从中部往西部走,沿途调查中发现,县城房价上涨的趋势正在向中西部蔓延。而购房者也多数为涌入县城的农村人。 紧邻慈利的石门县,其县城发展速度更甚于慈利。据石门县劳动就业管理处一工作人员介绍,到2004年,城内人口就已达到10万,全县18万人的外出打工队伍,每年有相当部分资金会转移到家乡。县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已达每平方米22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千元。城内居民住宅整齐林立,临街商铺门庭若市。在当地农村娶媳妇嫁女儿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订婚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有没有房子。如果在县城有房子,人长得丑点都没关系,没房子的话事情就说不成。在县城买房,成为该县众多农村青年的奋斗目标。 记者一路向西。 甘肃省,甘谷县城。 在这个西部小城,因为房贷政策的滞后,当地农民并不能按揭购房,这就意味着在拿到新房钥匙的同时,他们必须一次缴清购房的全部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很多农村人口往县城迁移的脚步。但尽管如此,甘谷的房价还是一路飙升至每平米2000元。很多人东凑西借,都想挤进城内。 地产开发大潮兴起,县城内第一、二毛纺织厂,甚至县委、政府的原办公地都变成了商品房住宅区。周边乡镇的公务员、教师、进城打工挣了钱的农民纷纷成为新建商品房的主人。 在这些涌进城的人流中,金山乡的农民是一个有名的群体。 金山乡距甘谷县城数十公里。和西北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人多地少,十年九旱,难以靠天为生的农民逐渐脱离土地另谋出路。当地人选择的是建筑业。金山乡的建筑企业多得让人惊讶,该乡登记注册的建筑企业82家,有7家企业资产过千万。金山乡实力较强的移家湾村,仅一村就有8个施工队,吸收3000名村民就业。经济实力渐强的建筑工头,成为迁往县城的第一批人,随后是跟着他们打工挣钱的村民。短短几年,原本有4万多人的金山乡,人口数量锐减到3万。上万人离开家乡,举家搬迁至县城。 与这一图景相对应的是,在甘谷县城最宽阔的康庄大道边,有一片区域聚集了100多户金山乡进城农民,被人们称为“金山村”。当地人都知道:甘谷有个“金山乡”,县城有个“金山村”。 随后,更多有条件的乡镇人口,开始纷纷像金山村的农民一样涌入县城,甘谷县城的边界在逐渐往四周扩大。 县城里76岁的祖林生老人回忆:从他记事起,县城就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县城四周是黄土垒成的城墙。2002年,县城遗留的最后一道北城门被拆除,旧城门处的十字路口发展成为县城的商贸集散中心。如今有关老城的记忆只剩一小段城墙,孤独地矗立在城中。而甘谷县城的大道仍在不断往东西两方延伸,道路延伸之处,依然是不断拔地而起的楼房。 生活在此处 目前慈利县县城人口数为11万,吃财政饭的为5千人,私营鞋厂、矿业公司、农产品加工厂等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1万,还有近9万人是在依靠第三产业以及打工者们在南方挣回的钱维持生活。 多年来,慈利县城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到城内两所医院公立医院去看病。然而近3年来,又有5家私立医院悄然兴起。三个不同层次的商业步行街已经形成,从高档品牌到廉价商品,生意人覆盖了消费的每一层次。城内餐饮酒楼一条街也在逐渐形成,每到夜晚,趴活的出租车停满街边。 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趋于完善,县城一所高中的新校区,占地300余亩,容纳近3000高中学生;两所小学、一所初中,也在准备扩容,城郊征地100亩,来适应逐渐增长的人口。 年初,向春在签购房合同的时候发现,一对在广东打工的小两口除了购买楼上的住宅用房,同时也花15万购买了楼下的门面房。买下房子,他们不再南下广东,而是打算把老人也接到城里来,在楼下做点生意。向春一刹那间也产生了留下的冲动。 “买完房子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再出去挣几年钱,等攒够本钱,我也打算回县城做个门面。”向春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她感觉,县城人对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只要有本钱,肯定会有商机存在。 旅行社、度假村这些名词不断跃进县城人的视野。 “咱们县就是个节日之城,有三个明显的对比:平日比较安静,生活节奏也不快。周末的时候在乡里上班的人回来了,公交车里都挤到没有座位;等过年打工的人回城,商场和超市里都没有可以站住脚的地方了。”一名退休干部这样感叹。 这里是人们的消费之城。搬进县城的农村人中,大部分都是在用县城以外挣来的钱购房,再把乡下的父母接到城里照顾小孩。而他们自己依然不得不在外地工作,用以维持他们在县城内拥有的一切。买房是他们扎根县城的主要途径,但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的脱离又使他们感到不安。 向春最终还是没有把户口也转到县城里,变成更彻底的城里人。提起以后的生活安排,向春仍然心烦意乱。向春说自己不会种地、也不会做生意,她看不到自己留在县里的好出路。目前她在深圳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加工显示器零件,每月能挣将近两千块钱。县城里目前并不能给她这样的工作机会。 大部分打工者们也都是同样的打算。县城里没有他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社会福利,有的只是房子和城市生活的便利。 不过,听说城边在大规模征地修建工业园区,她已经去工业园看了好多次。向春说希望能在即将建成的工业园里找到一份工作,让她可以不用远离家乡和孩子。★ 给市镇的自然发育松绑 究竟是由民众自发地进行城市化,还是由行政权力催生城市? ★ 文/秋风 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这一点无可置疑。那么中国究竟该如何实现城市化?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这一问题。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以充分利用聚集效应;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农业大国城市化的惟一选择。这样的争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在这些讨论背后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理性与权力的自负:专家或者政府有能力事先知道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才最好,且政府可以用权力强制所有地区走那条被人发现的正确道路。 不过,在现实中,权力的支配十分强大,上面的争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了。大城市和所谓的“小城镇”都在发展,但基本上都是权力造城运动的产物,两种城市化模式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了。 权力造城运动的畸形格局 一个城市看起来要像个城市的样子,需将必要的资源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品供应。按照目前的制度,只有建制市才能够享有相应财政资格。而建制市的设立,完全是行政当局的事情。省城、地级市自然地享有建制市的地位,驻于该城市的省政府、市政府对其下辖的市县又享有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力,包括在财政谈判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为它掌握着下辖市县官员的升降大权。而每级都要创造好看的政绩,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造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每一级政府都致力于利用权力把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投入到自己驻在的城市。地级市政府所在的城市除了自留资源外,市政府还可以利用其权力,集中全市资源用于发展该地级市。县政府也努力争取把本县变成建制市,即便不是建制市,县政府也会利用其权力汲取全县资源发展县城。 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权力主导之路。城市化当然有自然演进的因素,但也有太多权力主导的成分。由于权力本身是上下森严的,所以,城市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占据权力最高位置的城市占有最大优势,于是,国际大都市层出不穷,由此往下,大城市迅速膨胀,中等城市急剧扩张,曾经被视为小城镇的县城也差不多发展成中等城市了。 可以说,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是权力掀起的造城运动的产物,这样的城市化进路,看似捷径,但这些繁荣的城市很可能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诸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因此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损失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机会成本。没有市建制、而很可能具有城市之种种自然要素的县城的发展,普遍受到地级城市的限制,普通城镇又受到县城的剥夺。即使它们已经具有城市之实,也无法享受城市的财政待遇,不能筹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 这样的进程形成的城市格局必然是畸形的,那就是头重脚轻。本来,这些普通城镇如果具有起码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吸纳大量人口。但由于这些城镇的资源被居于权力上位的城市夺走而无法建设基础设施,移出乡村的人就沿着城市级次向上流动,纷纷涌入地级市、省城、大城市及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大城市为了保卫自己本来就紧张的基础设施,必然倾向于利用现有户籍制度,设置那些违反宪法的人口流动壁垒。这一壁垒固然阻止了乡村、外地人口流入本地,反过来又阻止本市人口分流。于是,在大多数人口还没有城市化之时,种种城市病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面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恐怕不能不思考关于城市化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由民众自发地进行城市化,还是由行政权力催生城市? 市镇化的前景有多大 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只可能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这种市需要具备很多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条件。政府尽可用其支配的资源建造起高楼大厦,但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一个市需要具备的文化、精神、社会等条件,而政府以权力支配城市扩张本身就意味着,该市不具备“市”的根本特征:自治。 当然,无数民众追求改善自身境遇的自发性努力过程,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一种创造出健全的“市”的趋势。近些年来,在很多地区已能看到一种趋势,即乡村大量人口向县城和镇集中。有的是在外工作赚钱之后在此购买房屋,有的是乡村人口为经商、子女就学、养老等直接迁入居住,还有一些则是追逐工业迁入,甚至包括外来人口。 看起来,这些城镇有点像费孝通先生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但对费老设想也有所超越。费老把小城镇定义为:“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从目前情况,随着城镇深度卷入现代经济网络,这些城镇未必与乡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另一种情形:大城市人口的郊区化,郊区可能出现某种新型市镇。 费老下述断言似乎也值得推敲:“小城镇是个新型的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许多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小城镇其实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城市,如果正确地理解“现代化”的含义的话。现代化意味着城镇居民享有“市”的自治治理,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假如制度安排合理,这一切在小城镇完全可以实现。 但无论如何,费老的基本构想已在现实中获得部分证明,费老的构想本身又具有历史依据。古代的“城”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城”是官府进行权力统治的节点,“市”却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以“市镇”来称呼费老所说的小城镇,可能更为恰当——这也可以与托克维尔所谈论的美国的township相对应。 历史上,中国各地市镇是十分繁荣的,尤其是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市镇数量与规模均持续扩大,到19世纪末,江南已有一千余市镇,其中颇多拥有数千户至万余户人口的巨镇。这些市镇乃是彼时江南社会、经济、宗教、教育等活动的节点,是经济繁荣与社会秩序的枢纽。5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权力控制经济,这个市镇网络被严重侵蚀。地区、县、乡所在城镇被赋予了特权地位,不少“市”被改造成“城”,丧失活力;大量的“城”也冒充“市”。即便如此,后来的社队工业和乡镇工业,也仍然是以市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费老在小城镇再次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生命力之时就预言,小城镇将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人口的“蓄水池”,而且将是商品的集散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以此为基础发育而成的“市镇”,也仅有此类市镇,有可能成为市民的自治实体。历史上市镇的自治确实是相当发达的,这是市镇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市”民的价值理念终究是不同于城民和乡民的。以自然发育之“市镇”为基础,不仅是城市化的正途,也有助于以自治原则重塑中国的治理体系。 问题在于,尽管乡村人口在向市镇集中,但现行各种制度安排却并不与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镇被权力制约,无法建立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的治理架构,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建设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品供应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配套,则小城镇发展也不过是重蹈大城市发展的覆辙而已。★ 城镇化:中国特色城市化的 曲折历史和探路难题 小县城房价上涨的背后,蕴含着中国城市化的曲折历史和现实难题 ★ 本刊记者/何忠洲 200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3.9%。 许多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城镇化现状:1978年~2000年,我国年均增加城市21.4座,年均增加建制镇824.5个;目前,城镇人口达到5.77亿人。 今年以来中国房价上涨日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和县城,似乎更为直接地显示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 其间意义,借用1999年来华参加城镇化高级论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由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城镇化,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农村——小城镇——城市——特大城市。 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区别于国际通行概念之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维新告诉本刊记者说:在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集中过程是“农村——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逆城市化)”,“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压力主要在城市解决,大城市不断扩张,然后再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周边卫星城纷纷建立。” 这是两种方向不同的城市化过程。 曾经有过种种争论: 大城市优先论者认为,世界各国城镇化初、中期发展的通例都是大城市优先。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非中小城镇所能比;大城市优先发展可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矛盾集中在城市解决,而且能节约土地和治污费用;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也有相当优势等。 小城镇优先论者则认为,作为城镇体系的基础部分,小城镇是大中城市的“母体”,世界各国现有的大中城市无不是从当初的小城镇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城镇的优势在于,建设成本、人口转移成本和体制成本低,适合中国国情;小城镇的体制包袱少,而大中城市短时期内根本无力吸收大规模的待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相较于大城市的光鲜与快速,小城镇联系城乡,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对城乡一体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等。 这是最为典型的两种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中等城市为主论”“大中小城市并举论”“县城为主论”“中心集镇为主论”“二元城镇化论”“城乡一体化论”“集中型(或聚集型)城镇化论”等,各侧重一面。 甚至不乏反城市化的声音。有乡村建设者认为,城市化未必是中国发展的惟一路径,中国的乡村完全可以挖掘传统,走出一条东方发展之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告诉记者:反对城市化的主要是一些生态学家。 种种争论更多的是囿于学界。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来不是照本宣科的产物。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政府推行的是“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方针。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一度还确立了“将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方针。这些举措,目的在于抑制消费,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 对城市化的这种抑制在1963年发展到完全的反城市化。当时,国民经济全面萎缩,粮食及商品供应出现短缺,因为“城市化发展的上限取决于商品量供应能力”,减少城镇人口成为解决难题的重要政策。 因此,在1949~1979年间,尽管这30年中国的工业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城市化率仅提高8.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8个百分点,比世界同类发展水平国家偏低20个百分点,30年只实现了1亿人口的初步现代化。 城市化的这种滞后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后粮食剩余局面的出现而逐渐松动。1984年,经过几年的农村改革,粮食第一次出现了全面过剩。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小城镇改革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当年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10月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标志着在农村的集镇和小城镇,放开了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两份文件提出的政策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经商办企业,但仅仅是允许流动,并非落户。 对农民进城限制的松动不经意间创造了80年代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1993年~1994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人数一度达到1.4亿人。1978年~2005年,中国的建制镇也由2880个发展到1.89万个。根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平均每年为0.82个百分点。 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很快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 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进一步具体化,有关方面并在户籍管理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而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则对十六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出“核心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化:加速与分化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本刊记者所讲:中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 一方面,城市化总体上在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的趋势却越来越严重。 从区域上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中心基本分布在内陆。到了90年代以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密集区。在东部地区集中分布了56.3%的特大城市、47.7%的大城市、49.5%的中等城市以及37.6%的建制镇。从经济综合实力上看,全国排位在前1000名之内的小城镇,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78.8%。 而且,北京、上海等40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36.24%,沿海三大城市群就接纳了约60%的城镇化人口。 大中小城市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北京和上海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北京的城市化率达到84.3%,上海的城市化率达到88.7%。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人们开始为污染、生活成本高等种种城市病叫苦不迭。而在中西部,一些小乡镇、小县城,虽名义为镇、为城,但和周边农村并无二致。而在贵州和西藏,城市化水平只有27.5%和28.2%。 这一差距,不过是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另一个表象。 其间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张正河教授说,和中国财政架构直接相关。 1994年的分税制,国家层面进一步将财力集中于中央,地方层面,则进一步集中于城市。由此出现如下说法:“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勉勉强强,地市财政紧紧张张,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 财力的分配,直接影响着中国城市的两极分化。而新一轮的城镇热,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维新说,主要还是个土地财政的问题。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下,中西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打起土地的主意来。 按照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在土地出让金管理上,30%归中央,70%归地方。原本规定70%用于耕地的开发,但实际上土地出让金成了政府各级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以地生财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快捷的财政来源。 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从1991年到1996年,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440万亩,1997年到2002年建设共计占用耕地1646万亩。 而由此形成的一个怪现状是:中国曾经长时期偏低的城市人均占地,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已经一跃为世界前列。调查显示,全国644个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远远高于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欧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进来,工作,住下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依据的。 2000年,中国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首次改变统计口径,把在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作为城镇人口。这一下,使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00~2005六年间增长了近7个百分点。 尽管相当多的人都向本刊记者指出:中国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携家眷的仅占20%~25%,而且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已经有着在城镇定居的可能。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事实上的联系。 但是,就是按照2000年当年户籍上的统计,中国的城镇人口也已达到3.9亿人,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中国城镇化率为30%左右。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即缓慢发展阶段或稳定发展阶段。 无论按照何种统计口径,中国都应该在加速期内,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即为明证。 在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3.9%之后,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事实已经有所改变——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3%,反而高于工业化率1个百分点。 但是,加速期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趋势却是让人担心的。 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明媚告诉记者,“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农民是否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收入能力是否支撑在城镇的定居和消费。” 但是,尽管城市人均占地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由于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这个高指标并没有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普遍明显改善。许多地却和城镇化了的人口几无牵连。 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修改城镇建设规划”的名目下,大面积土地被乱批乱占。根据小城镇发展中心提供的资料,即使在发达国家、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很少看到大马路、大广场、大花园,在国内的很多小城镇却遍地开花。 甚至完全没有产业支撑的一些地方,大规模的超前建设也屡见不鲜。结果城市里没有了人。郑明媚说,“天一黑,整个城市就一片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铁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包含多种指标的概念。它不光是土地的城镇化,也包括人口的城镇化。房价高涨有可能的一个后果是,非农就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面临着更高一层的门槛。 在土地财政冲动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其结果是与城镇化本身背道而驰的。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已经为此提供了教训。尽管他们的城市化率甚至远远高于70%,但是却被称为是假城市化。因为人虽然在城市了,但职业没有转化,产业没有转化。许多人没有工作,到处流浪,贫民窟成为城市里四处可见的伤口。 城镇化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国的非农业人口转移面临着多重的困难。 即使城镇化保持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即便2020年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即6.4亿人在农村生活。这意味着摆脱农村的贫困状态、建设新农村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两极分化。小城镇倘不能有效地在吸纳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那么常年上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就将始终在各大城市寻找机会。而其候鸟式的迁徙状态倘不能被改变,那么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感就始终无法消除。 这就注定,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多个出口应对人口转移压力:大城市、县城、乡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