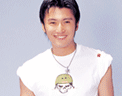中国医改将如何提速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13日 19:11 《时代信报》 | |||||||||
|
吴鹏/文 在今天的中国,看不起病的人太多了。 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在医疗覆盖情况一项,中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四。
然而却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医改,现在看来,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样的话,听起来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儿戏”的色彩。 看不起病的崔德洁们 12月10日,重庆沙坪坝区某大医院。 在那幢现代化大楼的底层,出入院登记处,我们看到了陈婉真,她来为她的公公宫剑南办理出院手续。在走之前,要再掏钱买些回家吃的药。 她解开她的红色的棉衣,从里面摸出用塑料布包着的一摞人民币,解开,数了一遍。有3500元左右。然后她面无表情的等待橱窗里的问话。 “要报销吗?”从里面甩出一句来。 “我是自费的,报销个鬼哦。”陈婉真嘟囔着说道。 交完了钱,陈在扭头的那一刹那,她对排在后面的我说了一句:这下子,家里的钱全部都洗白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17天,总共花费了17900多块,平均一天1500多块。”陈婉真说。 因为今天晚上就要走,陈婉真又提着药来到出入院登记处,她想把17天来明细清单打出来。 那张长达一米的清单的最下端,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数字:17239.22元。这是宫剑南从11月24日到12月10日住院的花费。 总花费的构成是:西药费11181.15元;化验费1126.5元;治疗费3034.26元;材料费399.81元;检查费498.5元;床位费788元;诊疗费107元,其他费104元;医院预收了14000元。 “不交预收费的话,医院就不会给你药了嘛”,当我问她为什么要预交这么多的费用时,陈婉真这样说。 陈婉真是四川泸州边上一个农村的村民,39岁,农业户口。和她患病的公公一样,没有医疗保险。 “农村人讲啥子医疗保险嘛。”她说。 她的公公宫剑南,今年61岁,2002年在这家医院做了换肾手术。陈婉真说,那是笔巨额的费用,包括这次来的1万多块钱,多数都是借的,家里已经被公公的这个病耗干了。 陈婉真是最近这两天才来陪护她的公公的,她替换走了她的另外一位亲戚,主要还是来的人多了,没有地方住。住在这里的空调病房,一个晚上的花费是40块,陪护的人如果是睡在床上,是10块钱。假如是在靠墙的一溜椅子上坐一夜,那么要收4块钱,而空调费,在一个三人病房内,每个人的付出是6块钱。 同病室的今年刚上初三的王志杰(化名)小朋友坐在床上替他的爸爸鸣不平:“我爸爸昨天晚上睡在外面的大厅里,那个姓崔的护士还向他收了10块钱,今天早上还是我去找他们说的。” 这一家人来自垫江,王志杰的父母月收入都是500块,他们是城镇户口,但是同样没有医疗保险,看病也是自费。王志杰患的是肾小球感染,这是一种慢性的轻微的肾病,他们在这里住了6天了,花费了五六千块钱。孩子的妈妈没有来,是因为从垫江到重庆,来回的路费要80多块钱。 从这家医院那幢高耸入云的大楼里走出来,回头可以看到这样的横幅挂着:建立节约型医院,推进全面可持续性发展。 王志杰很快就要出院了,现在他的脸还有些浮肿。但是下学期,不出意外的话,他可以回到学校的课堂读书了。 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崔德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2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报道。 “崔广顺的妻子杨德银从离北京500来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牧场乘长途汽车来到北京,照料他们唯一的儿子。为了节省住宿费,几个星期以来,她就在医院一处候诊室的塑料椅上过夜。 崔广顺回忆起得知孩子得了癌症的那一刻,他站在街上失声痛哭。 他本以为孩子要被判死刑了。但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直言不讳:“只要有钱,孩子就能救过来。”他回忆着大夫的话,“如果没钱就只能等死了。” 村长拒绝了他贷款的请求。说他的抵押物——房子根本一钱不值。当地政府也没帮上什么忙。“每天都有人死,”崔广顺说,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11月底的一天,崔广顺最终放弃了──他付不起孩子的所有医疗费。第二天,他长途跋涉回到北京的医院,和妻子一起站在医生面前,听她指责他们拖欠账单。“现在我们花光了钱,也失去了孩子。”崔广顺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孩子妈妈默默无语,但眼里充满泪水。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崔广顺和杨德银已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使他们儿子的白血病在医学上很有希望治好,他们也可能永远找不到足够的钱给他治疗。医院估计德洁的病要完成第一阶段六个半月的疗程大约需要18500美元(人民币15万元),这笔钱对这个年收入不到350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元)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和中国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一样,崔广顺没有医疗保险。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崔广顺靠在他家的红砖房门口说:“生了病什么也没了。”他随即叹了口气。他已经把今年种的土豆全部收下来卖掉了。玉米也全部收了,已经卖掉了大部分,只留下一些够全家过冬蒸馍吃的。他说:“我只能把德洁接回家了。” 仅仅谴责医院是不正确的 如果你去质问医院:为什么不交钱就不能先给药,先看病先动手术?为什么坐坐你的椅子也要加收4块钱?医院的领导们多半会耸耸肩,然后将两手摊开。 能怪他们狠心吗? 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的事件中,似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一方面是这样的谴责: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费近140万元,更让人惊奇的是,医药单上居然有患者严重过敏的药物,在患者去世后的两天,医院竟还开出了两张化验单。 另一方面是这家医院的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于铃范主任的申辩:这个患者我们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我们不但没有多收他还漏收了130多万元。 是于铃范在撒谎吗? 比如崔德洁小朋友的悲剧,正像《华尔街日报》中点明的那样:这是中国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医疗体制带来的严酷现实,如果不先交押金,医院就不给病人治疗。 德洁的主治医生谢静认为医院严格坚持现收现付的做法是必要的。她说,如果拖欠的账单太多,医院就要承担经济损失。而医生如果不去尽量敦促病人补齐费用,他们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她说:现在,医生不仅要给病人看病,还要催他们交钱。 根据医院的规定,如果病人拖欠的费用达到250美元(合人民币2000元),医生就必须向病人发催缴单,并负责催病人筹到现金。 她说,人们因此对医院和医生很不满。但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她说,最大的问题是医疗保险系统很不完善。 这家医院的医生并没有撒谎,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地区的医院都面临着这样尴尬和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遵从希波拉底誓言;一方面要面对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全面失灵所带来的恶果。这个恶果的承担者,往往是崔德洁父母这样的失去或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障的人。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医疗保障即使是对美国等世界最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如果生了病就有可能花掉全部积蓄。但不管怎样,需要紧急救治的人通常还是能得到救治,政府对享受税收减免的医院有这方面的规定。 今天,中国有许多大医院添置了很多最新医疗设备以吸引付费的病人。但在医疗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医院的收费也在急剧膨胀。据中国政府机构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多开药,或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项目。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医药费占中国医疗开支总额的50%以上,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在15%-45%之间。研究报告说,医疗开支中有12%-37%的开支是由不必要的药品处方浪费掉了。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病救治费用迅速膨胀,已经成了一项沉重的社会负担。崔广顺说,他们村在1996年才通电,大约30多户家庭中一半都背着自身难以承担的贷款,而那些没有贷款的人根本就没有余钱可用。 这家美国的媒体甚至指出:中国人的储蓄率之所以高达40%,存钱防病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什么是医改的当务之急? 医疗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覆盖到所有人。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免疫接种。在城市,在政府机关和国营单位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些单位往往还都有自己的诊所甚至医院。 但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也纷纷关闭或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从80年代初开始,政府要求医院开始自负盈亏。 对于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先是被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的葛延风副部长公开承认: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后来又有卫生部高官高强纠正说:从来没有人讲过医改是失败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国的医改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基本失败和总体成功我们可以看作是官员们口中的“文字游戏”,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们现在需要在乎的是:医改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兼顾效率和公平?是继续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还是回到起点?还是有可以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可以遵循?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 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这样一条在其他国家被证明为错误的道路我们不能再走。 据《经济观察报》近期的文章中称:卫生部制定的《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思路:由市场化向公益性侧重。 据报道,这份一直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意见》在其开篇就为“卫生事业”定性: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而在之前的“3月28日稿”中则没有对卫生事业性质的明确表述。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表述的变化,也凸现了7月版本较之3月版本更加确定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几个月间,《医改意见》由“市场化”愈来愈向“公益化”倾斜的转变,耐人寻味。也反映出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上的慎重和彷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即使像是7月版本中的《医改意见》,将来一旦实施,就真的能够撼动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吗?如果可以,怎么撼动?单纯依靠卫生部门的努力就真的能够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医改吗?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保证医改的公益性?如果我们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医疗体制改革,不能使得金融、财政、税收和卫生部门产生联动,那么怎么保证这样的一份意见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屠龙之技”?正像负责制定这一意见草案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讲,医疗机构掌握着专业权力,公民缺少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要想对这种强大的专业权力形成制衡,公民权力、国家权力、社区权力需要联合起来对抗专业权力。 在经济学界,经济学家郎咸平是在医改领域的“凯恩斯派”,他看不懂国内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应该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 郎咸平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在现实中,在“医疗体制要改革”的一片呼声中,我们却看到了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的事情。 看来,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时候由国家来负担并不是这位郎咸平先生说的这么简单。也许另一种声音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却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解决之途。 这便是经济学家汪丁丁早在今年10月份便著文指出的: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遭遇的挫折,恰好与普遍的权力寻租行为和转型期社会的道德沉沦密切相关。 汪丁丁说,经济学家们已经多次论证过:医疗服务领域和教育服务领域,是市场机制最容易失灵的两大领域。其次,为弥补“市场失灵”所引入的任何一种“政府机制”,其有效性的前提,必须是政府不失灵。在目前情形下,必须承认,而且需要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承认,我们面临着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 而政府失灵是远比市场失灵危害严重得多的一种制度失灵。 这位经济学者指出:当医护服务人员报酬的市场定价机制被政府管制严重扭曲的时候,医护服务人员的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严重扭曲。于是我们应该采纳一切成熟市场社会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能够被成功地借鉴到中国社会所必须的诸项条件,制定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并且顾及它们与中国社会一般道德状况之间的关系。 在医院总收入当中,从药和器械创造的收入各占约40%,财政拨款只占20%。中国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的形成在汪丁丁看来是体制的原因造成的。而这样的体制:是由财政部门、计划部门、卫生部门和人事部门、物价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组织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共同构成的庞大的医疗体制的总体混乱造成的。 据此,汪认为,并非是国家坚持市场化的改革的方向错了。 这位经济学家给出的“解决路径”是:1.让官僚机构退出医院管理领域,鼓励医护人员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诊断中心”、“手术中心”、“护理中心”等专业机构,保护一切参与竞争者的平等权益,引入与权益增加的幅度相匹配的惩罚强化机制。在这套机制内,医疗辅助团队的合理报酬将由医师合伙人组织根据护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务市场价格竞争决定;2.建立具有足够公信力的医疗成本审核委员会,定期发布指导价格,并开始寻求一套合适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方案。 这样的一条解决路径,想来也会不轻松。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12月大黑马免费送!!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国保佳教您赚百万! |
| 儿童EQ教育最新资讯! |
| 开男士品牌名店赚疯了 |
| 名品服饰 一折供货 |
| 肾病、尿毒症怎么办?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瑜珈美容俱乐部太赚钱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开个咖啡店赚了几百万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法国美容 浪漫赚钱! |
| 女人暴富好项目!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