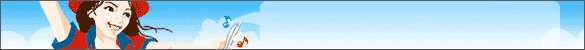经济扑克中的宗教牌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10日 18:4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作者:唐学鹏 经济发展游戏“扑克”中隐藏着一张“宗教牌”,这是马克斯·韦伯的结论。不过由于这张牌打法不明,大小难以界定。所以人们研究它的路径分散而怪异,不时发出哄笑和争吵。就像阿多诺说的,“我们做的是蝇眼分裂般的工作,我们找不到道路,道路拒绝了我们。”
的确,如果将经济发展的诸多变量剥离出来,只留下宗教因素,然后观测宗教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从牌理上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从牌局的玩法上看,是艰难的。因为宗教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是神秘和难以物化的。比较偷懒的做法是,可是专门采取文化符号学的方法大放厥词一番。但是文化符号学容易产生文人相轻,小范围的文化牌局冲突。 宗教差异的数字化分析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为此感到郁闷。巴罗一直相信,宗教的差异一定能从经济增长差异中反映出来。而且,他也固执地相信,文化差异一定能从数字侦探师的严谨侦察中体现出来。 巴罗这篇论文的名字就叫《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全文刊登在美国国家研究局的网站上。 在论文中,巴罗选取的经济发展指标有4个项目。一是人均收入,二是教育程度,三是城市化水平,四是寿命预期值。然后看宗教能否让这些项目的数值变得更好看。 巴罗和合作者女助手McCleary搜集了1981年到1999年59个国家的宗教状况和经济发展指标,并且获得了Gallup调查,世界银行和密歇根大学等6个组织的帮助,得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这份完成时间长达5年的报告确凿无疑地肯定了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强相关性。 巴罗说,“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共同体。诚实能让俱乐部信息流通无障碍,热爱工作则加强俱乐部的财政实力,而节俭同成本控制有关,对陌生人开放则有助于俱乐部的扩张。” 不过,巴罗的研究表明,尽管宗教气氛浓厚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如果该国天主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太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变得缓慢。也就是说,宗教的组织化和组织的规模化将损害经济发展,占有经济资源,而且把人们在市场上的工作时间抢夺过来,变成了在教堂里的“宗教虔诚”时间。 McCleary说,“巴罗和我希望那些经济学者做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能够引入宗教文化变量,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模型处理方法,我们希望后来者运用它们并改进它们。” 巴罗论文里还有一个非常新颖之处,在于他把教育同宗教进行分离处理。马克斯·韦伯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处理的。巴罗推翻了过去有关经济增长的一个假定,认为只有教育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非物质因素,实际上,教育的确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但只是在个人主义层面上,提高了个人的能力,而在提高整个生产函数和制度函数的内在融洽程度和内在效率做得并不多,相反宗教可以做得比教育好,宗教改造并抚慰人心,宗教让劳动者友爱,满足和快乐。 过去人们认为,全民教育水平的确反映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度,但这是值得怀疑的。“比如美国,同西欧相比,美国的整体教育水平低于他们,但是美国比他们都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国家。” 实际上,就我所知,能够支持巴罗看法的事例的确很多。比如在过去30年间,东亚大部分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韩都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着基督教文明在该地区强烈扩张的倾向。而且,南韩是观察这一趋势的最好范例,南韩是东亚儒教文化最浓重的国家,而它向基督教文明转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其次是新加坡和日本。 “宗教气氛淡漠的地方,经济低增长也是题中之义。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故乡,过去的东德。”巴罗说。东德是目前世界上宗教热情度和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 缺失地狱的不同 我在读巴罗这篇论文时一直想,既然东亚事例表明:儒教文明大规模地向基督教文化转向,是市场经济内在结构对于宗教的选择和渴望,那么儒教在市场经济的融洽程度上比基督教稍逊一些的是什么呢? 是地狱!市场经济不仅仅要挑选出好的行为,还要惩罚坏的行为。市场经济需要宪政,法庭,警察和看守所,这些训诫肉体的地方,也需要另外一种地方,如福柯说的那样,“训诫精神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宗教里的地狱,火狱,炼狱。 没错。儒教文明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精神的畏惧感,没有神,没有灵魂的施虐者,没有终极惩罚。儒家文明从家庭伦理出发,很缠绵地与体制权力调情,也会很慈祥地发展出平和的交往哲学,总之,没有生命中不能不祈求之“轻”。 尽管很多中国人认为儒教其实不是一种宗教。不过,我倒是更愿意接受经济学家Luigi Zingales把儒教当作一种宗教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韦伯所定义的新教伦理也开始需要变迁了。据我所知,东亚国家的儒家文明向基督教过渡,是向韦伯时代新教伦理过渡,如当时的新教徒一样,这些国家的人民受到了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教导,更愿意刻苦工作,存钱和往上爬。而现在,那些韦伯时代的老牌新教伦理国家关注的是国民生命质量和体制的“社民主义”,他们走到了“后韦伯”时代的新教伦理道路上来。 这有点让人感伤。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韩国时尚品牌女装招商 |
| 超值名牌时装折扣店 |
| 虫虫新女装漂亮才被抢 |
| 亚洲火爆前卫时尚女装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中国1000个赚钱好项目 |
| 失眠、抑郁症新突破! |
| 男人--让你幸福到底! |
| 近视眼手术暑期大优惠 |
| 3个月,重振男性雄风 |
| 中国特色治疗精神病!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