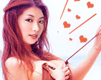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我们的“存在主义”-沈烨/文 萨特在1980年去世了。
第二年,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作为严格意义上的1980年代的第一批(1980年出生的都自觉被划分成1970年代“老人”的尾巴)出生了。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萨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已故的哲学家,注定在我们主动去触及他
的思想和文字之前,不大可能有机会出现在报纸新闻、电视节目或者Internet的门户网站上(呵呵,除去这三种途径,想要攻入1980年代被信息挤得满满的大脑,恐怕不太容易,什么?人文科学著作?!——你不是1980年代生的吧?!)。
十八岁以前当然是一片空白,不排除有天才早早地被哲学陶冶了情操,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尚苦苦挣扎在数理化的题海中不能自拔,哲学这个东西不用看就知道是条贼船,上不得。
恍恍惚惚迈进大学门槛的时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
1999——关于这个数字和这个年份,当时有无数的故事传说预言噱头。总之,大家似乎一下子找到全人类集体疯狂的理由。就像当年人们说“少废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样,“世纪末”三个字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借口。我们还没有看过存在主义,但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肯定、甚至无限放大自我存在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纪末情结”给了老萨特重返舞台的机会——在集体恐慌的情绪中,我们饥不择食地开始寻找能够让未来有更多意义的真理,存在主义作为关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学说就这样被囫囵吞了枣。而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意识似乎并不需要觉醒,作为“泡在蜜罐里长大的一辈”,作为各种媒体现场报道的忠实拥趸,特别是作为独生子女,我们的自我意识与生俱来,并随年龄的增长呈几何级数递增。
萨特对自我的反省是很正常的事,接不接受诺贝尔奖是公众人物的个性与自由,至于他和波伏娃的契约式婚姻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现代的情侣很多不仅与其本质相同,而且直接省略了“契约”和“婚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长大,我们的神经都变得像粗钢筋一样麻木。惟一有印象的,恐怕是哲学家死时巴黎五万人相送的场面(注意,那也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第一,那很像我们小时候读熟了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第二,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很难再找到这样自发的集体温柔与热情。
但萨特还是会被反复提及,他和“黑格尔”、“后现代精神”、“解构主义”一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我们不得甚解但可以标示知识水平的符号。而且,他来自于风景如画的法国;而且,他的传记可以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爱情故事;而且,他已经死了。因为这些,这个符号的分量好像又重了。
惟一遗憾的是,萨特的文字绕得像一场逻辑游戏不说,主谓宾定状补都齐全,居然连顺序也没有打乱,已经跟不上读图时代的阅读规则了。我们只好活学活用,直接在符号上做文章。比方说,如果你听见一个1980年代的人说你这事儿做的“真萨特”,千万不要往存在主义上想,也许他只是觉得你无厘头罢了。就这样,我们曲解了萨特,实现了我们的“存在主义”。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