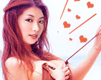地方经济分权奠定中国改革成功基础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03日 14:42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系列之三 甘阳 现在就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一再提出来的问题,即按照常理,中国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程度,教育的
创造性的破坏 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 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解放初期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 “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这个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 “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而她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是后来才形成,而是建国初期就已经奠定的,后来是继承了这一政治逻辑。 未建立起的中央计划经济 另一个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中认为,1949年中国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容,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受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两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 舒曼指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在后来受到了质疑。而1958年,中央又决定将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这样,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被摧毁。 两种集权与分权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农民工人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任何学过一点西方政治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它是否有西方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 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中国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19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中国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也是强调把整个社会结构带进来。我们今天过分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学区分,即两种“集权”和两种“分权”的区别。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比较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时指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的差别就在于美国是分权的,法国是集权的,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集权和分权概念。这就是他提出的“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区分,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区别。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要“政治集权”,而英国和美国恰恰是这种“政治集权”的典型,亦即英国和美国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而法国却恰恰是“政治分权”的典型,即总是被内部分歧撕裂而难以形成统一政治意志。但同时法国却是“行政集权”的典型,即一切具体管理事务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在这些具体事务上地方反而没有什么权力,而美国则是“行政分权”的典型,即各种具体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地方的发展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 行政分权下的经济分权 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 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谢淑丽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 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4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348000个企业,其中只有4000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 分权下产生的活跃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走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 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实际是在 “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改革后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曾一度想走回19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当时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 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已经形成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 乡镇企业的“大跃进“基础 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1980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放权让利”,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但当时很多人其实强调“放权让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 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正是当年 “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于发展乡村工业,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呢? 费孝通的梦在中国1980年代实现了,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从“大跃进”开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1970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19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 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事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未完待续。本文根据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的同题讲演整理而成。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本文同步刊发于《书城》杂志。)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正文 |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韩国时尚品牌女装招商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风情小布艺店生意火爆 |
| 超值名牌时装折扣店 |
| 虫虫新女装漂亮才被抢 |
| 日本服饰时尚冲击波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05年开什么店好赚钱? |
| 防治皮肤白斑外阴白斑 |
| 男人,你想更幸福吗? |
| 中国特色治疗精神病! |
| 3个月,重振男性雄风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