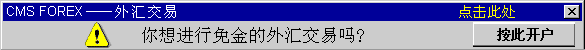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 20:49 中评网 | |||||||||
|
新 望 1996年-1997年,正在人们给“苏南模式”赋予更多政治色彩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苏南经济似乎已停滞不前,而且还发现,如不及时改革还将暴露出隐藏着的许多问题。苏南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时刻。
首先是江苏省委党校的储东涛教授在中央党校无锡科研基地举办的“1998年乡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以《对江苏乡镇企业20年历程的审视》为题目的发言中提出了“江苏乡镇企业痛失领先地位”的观点,储教授以公开出版的几种统计年鉴上的数字明白无误地审视出江苏GDP在全国的比重、江苏乡镇企业在江苏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从1993年之后均呈直线下降之势,已被广东、山东赶上、超过。尤其苏南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储教授初步地指出,“自身机制退化”是苏南模式不再执农村工业之牛耳的内在原因。后来储教授又在《中国市场经济报》、《太湖论丛》、《领导理论与实践》、“江苏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研讨会”等地方发表了《苏南模式的退化》、《乡镇企业:目前的困境与跨世纪飞跃》等文章,目的是呼吁江苏尤其苏南要加快改革。 储教授是江苏地方经济经济史专家,他从发展史的角度来谈苏南模式问题,自然比较有系统,他所运用的数字也很有说服力。其实,理论界对苏南模式既有思路与经验的的盲从和僵化很早就有议论。1992年以后珠三角、胶东半岛、温州等地区经济的斩露头角和勃勃生机,又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思考这一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的1992年6月8日,《新华日报》理论版登有浦文昌的文章《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苏南模式至少在五个方面存在不足: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见事迟,速度慢;破除平均主义力度不大,进展不快;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滞后;城市企业和经济活力不强,发展缓慢;科技进步及其人才意识比较淡薄。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发展是硬道理”,改革的事还顾不上。在1992年—1994年的大发展中,苏南地区在两个方面上了台阶,一是“造城热”中各县市城市建设极大改观,二是“三外热”中外向经济上了新水平。而这两件事也都是由政府做成的。 关于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可能苏南以外的同志不大好理解。我举三个例子,一是政府统一划出地皮,规定楼层高度,各局、委、办“谁家的孩子谁家抱”,没钱,自己想办法去拆借,去集资,有些楼盖起后无钱装修,无法利用,有些高楼的一半房间闲置,有些因没有效益,无法还钱,被法院拍卖或抵押,有些职能部门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权力加重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二是每个乡镇和各有关经济职能部门引资、合资项目数、到帐外资数都有从上面布置下来的硬任务,否则,政绩考核一票否决,此种情况下,为应付上面,出现了很多假合资。为此,苏南各县市97年普遍清理过一次。三是欲来此投资的台韩港日的外商们都知道一个简单道理:要谈投资只能找镇书记,厂长说了不算,镇长说了也不算。了解一点苏南背景和东方文化的外商都知道市场资源掌握在谁的手中。而且他们也深知,法治虽然靠得住,但人治更来得快。正如研究苏南模式的专家朱通华先生所概括的:“县乡干部是企业的实际决策人。”(朱通华孙彬,《苏南模式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这也是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在日益完善、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进程中超常发挥的最后机会了,尽管城建中有浪费和贪大求洋,合资中有虚冒和上当。在这一轮经济高涨期中,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发展,吃到了短缺经济最后的晚餐。也正由于此,在“发展至上”的呼声中,问题被掩盖了,党政力量在市场领域里的作用却被再次加强。 在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几乎所有江苏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苏南模式存在的问题,专家们呼吁,这一地区在原有的体制空间里已达到了该模式的本质特征所既定的发展极限。沈立人、洪银兴、薛家骥、顾松年、吴祥均、张曾芳、万解秋、孟焕民等人陆续开始在《新华日报》、《江南论坛》、《苏州日报》、《江苏经济学通讯》、《太湖论丛》等报刊和会议发表文章。学者们的态度和措辞是谨慎的,一开始是“创新”、“完善”、“新阶段”、“新辉煌”,到后来也有人用上了“质疑”、“面临挑战”、“僵化”、“异化”、“危机”、“突破”、“扬弃”、“告别”等较为敏感的字眼。如《新华日报》1997年9月4日理论版严英龙、沈志强的文章《从热衷“模式”到告别“模式”》,认为模式无非是变量因果方程式或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的描述,应当打破“模式崇拜”。 1997年5月中旬,也就是江泽民“5.29讲话”发表前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杭州大学等在杭州举办了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研讨会。会上,由于中央领导人对多种所有制成分的肯定,一向被低调处理的“温州模式”此时却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于祖尧等人认为,模式的形成可能与历史、文化、地理有关,不应照搬,不应僵化,更不能以“姓资姓社”来看问题。因为该次会议主题是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与会代表们自然而然地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作了比较。张仁寿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的古典发展道路,而苏南模式的制度构造过于接近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民主、监督成本问题突出,因此,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更有生命力,更值得其它地方借鉴。万解秋预测,苏南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改革需要“先死后生”,改革的成本及其高昂,阻力相当大,教训极其深刻。 在这场关于苏南模式变革讨论的最后阶段,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顾介康终于以官方身份出面发言。顾介康对“苏南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优势相伴而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暴露出来的不足和问题主要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顾介康,《论“苏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创新发展》,《群众》1997年第12期) 然而,也有一些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政治方向出发,开始将苏南模式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高度。在没有任何实证调查和分析的情况下,或者走马观花,或者以道听途说来的数字为依据,将“集体经济”与“集体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又将“集体主义精神”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这些大多来自基层宣传、文秘、新闻渠道一些“写作爱好者”空洞无物的“大众话语”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主导。 尤其是,苏南模式关乎一代官员的乌纱帽,他们多数都在台上,任何对苏南模式的“非议”和“否定”是危险的,涉及到对自己以往政绩的重新打量和估价。一些人心里清楚,即就是渐进式的改革,也意味着既得利益明确地丧失。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批评“有人对苏南模式说三道四,口是心非”。1997年10月,《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以《陈焕友反思“苏南模式”》的题目,报道了在江苏省委九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江苏省领导首次公开反思“苏南模式”。之后,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文摘》予以转载。然而随后不久,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江苏经济高层论坛上,省委书记陈焕友又明确地反诘有关媒体“不负责任的传闻”,声称从未说过要反思苏南模式的话。据说,是江苏省委领导受到了来自北京某方面的压力。也是在这一年,由于一位中央领导的一个批示,原定的江苏乡镇企业改制推后一年。在同一次的南京大学高层论坛上,官方与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抢抓第三次机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调整代替了改革,江苏乡镇企业改制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有经济学家说,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每向前迈出一小步都将十分艰难,还会出现拉锯战。苏南模式的变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97年年底,出自费孝通教授门下的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惠海鸣在小范围印行了自己的学术笔记《山涧清流》。惠海鸣深受费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多少了解一些苏南模式社区干部所有制及基层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的这本小册子对了解和研究苏南很有阅读价值。在这本册子的一开头他首先从学理上阐发了“模式”概念和“反思”一词的本来意义,指出“模式”不是“定型”,“反思(Reflexion)”即是“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还反对以个别的现象来代替对事物的总体和本质的把握,对苏南经济的本质把握应当借鉴制度经济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成果。“通过现象看本质,需要理论来探索深层问题。这些原因不是偶然产生的现象,也不是纯主观的错误,而是目前体制的结构性问题。某种必然性决定了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会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体制的结构。我们关心的不是偶然性的东西,而是一定结构产生的后果。应当说通过体制的改革,是可以克服的。”(第2页)“不想探索工厂关闭、债务危机、经济困难、吹牛皮、农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那么,“‘幼稚’的大人物也许认识不到‘苏南模式综合症’的症结所在。”(第11页)作者对苏南存在的体制性腐败有深刻的体察和隐晦的表达,如文中收集了许多反映干群对立的“乡议”。惠海鸣还敏锐而尖锐地揭示出:“地方第一把手的个人崇拜是苏南模式的重要特点”(第12页)。 然而,不改似乎已经没有退路。在储东涛教授不留情面地将痛失领先地位的结论亮给决策者和理论家的时候,事实情况可能比这还糟。转制前,乱集资和企业倒闭引起的债务危机已影响到社会稳定,插手其中的基层官员,甘尽苦来,甚至不敢回家,不敢回办公室。经济质量差,产品积压,效益下滑,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创建、补农和乡镇官员的灰色收入已使企业不堪重负,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后来的转制中,由地方基层官员策划的破产逃债(据张家港工商银行调研室张大典的归纳,逃债手法大约有10种之多)使国家银行成了最大的冤大头。而那些经营较好的少数乡镇企业作为体现和标志苏南模式核心特征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tism)的优等生被“抓大”“扶大”,已收归地方政府,由县市领导亲自经营,成了变相的地方国营、二国营或准国营企业,享受上了特殊的政治待遇和政策。而多数由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的干部举办和经营的镇(含乡及供销社)办企业,即就是勉强转制(有的已经破产,有相当一部分实际已资不抵债)之后依然处在惨淡经营之中。曾在计划经济夹缝中得农村工业头呔汤之鲜的苏南模式因故步自封而落伍了。他们以“四千四万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破千难万险)把旧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但它的内核却无法发育出一个新体制,而始终需要倚赖于旧体制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尤其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之际,它所固有的问题也就最终浮出水面。 苏南这种“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正如谭秋成指出的,社区政府也是“经济人”,在公社制因无效率而失败时,社区基层政府为填补权利资源真空、控制剩余索取权乃是其大办社队企业的历史动因(谭秋成《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结构特征及其变革》,第174页)。在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往往以该企业举办者的官级做本位来衡量出企业的级别。苏南的乡镇企业和县(市)属大集体企业有一项功能就是向乡镇和县(市)机关输送同级别的干部。一个大企业越办越糟,现已频临破产,但这个县有很多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自该厂厂长提拔而来。政府与企业这种同“级别”间的干部交换关系成为一些官员多吃、多拿、多占,追求灰色收入和在职消费的心安理得的理由。而且给正常的干部队伍和企业家队伍建设均带来极大的难度。正如苏南一位有名的大企业家所说“有些企业虽成了典型,纸糊灯笼样样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进一个牛,有的甚至能放进一座小山。让外面来的同志仔细地一个村、一个镇的算算,哪来那么大的GDP!”这类企业的领导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一边讨好上面、一边收获个人利益上。搞企业是为了捞政绩、谋位子。 至于说到农业,情况更是越来越不妙。为了推行样板工程(马路两边的稻棉丰产方),完成“任务农业”,农民种什么,何时种,何时收,悉由上面规定,干部替农户做主,农户的经营自主权被严重侵犯,从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苏南某村曾在1996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主任丁某强行拔掉了陈老汉田里种的小树苗,老汉一气之下拔下了村主任的一咎头发。令丁某无可奈何的是老汉的儿子就是县里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丁主任丢了份儿,自感在村里已无法再干下去,遂到附近一家乡镇企业当了工人。并从此落了个外号“丁秃子”。丁秃子讲起自己当村干部的经历总是一脸委屈。县里对粮棉产量有要求,指标层层分解到乡里、村里,那么,农民的田里种什么将不再是农民自己能决定的事。你拔我的树苗,我拔你的头发,究竟谁之错?苏南个别地方农民为政府的盲目行为真是吃尽了苦头。某村老太太家的房子有点陈旧过时而又在新修的公路附近,“有碍观瞻”,被强行拆除,亲友邻居看不惯,出面阻拦,结果引来近千名警察包围。老太太被拆了房子,亲戚又遭牢狱之灾。这真是穷而有罪,祸从天降。 形势比人强。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南乡镇企业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民间力量、市场力量正在崛起。上述官办、镇办的企业有的在如日中天之时却突然被淘汰出局,有的虽说是“二次创业”,却几乎是推倒重来。在大量“病马”倒下之际,一批“黑马”又猛然间脱颖而出。正如刘禹锡的一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情况在江阴市特别明显,如阳光、三毛、双良、申达、华西,另外如张家港远离市区、远离乡镇的江苏永钢集团等。曾经的“异数”成为如今的“主打”。苏南的江阴等地由于其领导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务实开明态度,藏富于民,经济殷实,近两年发展势头良好。 如果再进一步钻进这些“黑马”型企业的肚里仔细看一看,这类企业基本都最初是亲朋间的合伙创办与经营,多数还是家族经营。这些企业与前面一类相比,所有制层次较低,有极强的“民办性”,甚至还有着浓厚的“合伙经营”或“家族经营”的色彩,而其领导人则相对固定,多有企业家强人产生。这些企业大多属村办集体企业或挂名的村办、镇办集体企业。与由政府创办经营的企业相比,这类企业除了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企业家强人之外,这些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务实经营,不搞虚假。同时,企业独立性相对较强,自主权落得实。其企业经营目标清晰,企业行为高度市场化。企业负责人即使有党政兼职,但基本是以独立的企业家身份“挂名”,是一种“抬举”和“奖励”。这是一种由“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刘小玄等人称之为“新古典企业”。 苏南某些地方曾是苏南模式再创辉煌的典型,情况又怎么样呢?在这里,苏南模式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问题也暴露得最为充分。“创建”中的形式主义加重了农民负担,搞垮了一批企业。因为搬迁或动用流动资金搞创建,表面工作搞上去了,但企业伤了元气,拿不出钱搞生产线改造。精神文明建设以牺牲人们的精神为代价,而且存在反文化倾向。更有甚者,某企业明明早已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但为了顾及该企业“全国典型”和“本市乡镇企业一面旗帜”的面子,应付当时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却宁愿机器空转,奉命忍痛开工(这个企业在参观热潮退去、改制进行之中马上陷入破产境地)。为应付外来的新闻记者和参观团,作假伎俩,花样翻新,令人捧腹,令人瞠目,黑色幽默,登峰造极。双休日不休,且周二、周五晚上加班学习,既是不学习,也要把灯开在那里;作假刚开始是个别数字,后来搞一套作假班子,再后来作假形成了一个条线、一个系统;凡次种种,比当年大寨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休止的扰民工程中,老百姓的权利被屡屡侵犯:围墙要开一个大洞,装上统一的铁栏杆,便于监督院内动静;创建电话村、装冲水厕所都有强行规定,否则断电、子女不让上学。一段时间里,人们表情严肃,诚恐诚惶。市区机关鸦雀无声,乡村基层干群对立,企业家担惊受怕,老百姓不愿上街。 当时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栋材因看不惯虚假之泛滥,写信给上级领导,结果却因此而遭到无休止的打击、压制。吴栋材感慨之余书写了一幅对联,高高地贴在工厂大门,表明一个老党员的心迹:“知难而进脚踏实地干是真,表里如一莫图虚名诚为本”。这幅对联字字有所指,在当时的气氛中真有些振聋发聩。 其实,也有不同声音。《了望》杂志1993年就在一篇文章中对“苏南某县级市”贪大求洋提出异议,警告城市建设、布局、开发、交通规划等工作应谨慎从事,多加论证,不可拍脑袋办事;《文汇报》1995年6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不要再刮“浮夸风”》,揭露了“苏南某个县级市”统计的产值有近办水分。呼吁停止数字大战,对弄虚作假者征设“牛皮税”。这篇文章《文摘周报》等报刊又予以转载;1995年底朱熔基同志(时任副总理)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谈到小城镇建设时,讲起了他对苏南一些地方的看法:“千万别乱提口号。李鹏总理报告中讲,尽可能少占耕地。”“书记到上海转了一圈,提出要建成‘白天像新加坡,晚上像小香港’的城镇。不能这么提。”“有的口号你们认为很正确,别人听不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很好,但把城市建设推到全国不得了,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1992年以来,小县城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伟大的成绩,但是花了很多钱,又不创造生产能力,超前,国力受不了的”(《镜报月刊》1996年2月号,周颖如,《朱容基对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1997年6月5日《华东信息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对张家港农民将新收割的麦子埋了做肥料表示纳闷,而事实情况是,市委领导人一声令下,6月2日之前所有麦子必须上场。老乡们埋了的麦子是未成熟的正在灌浆却奉命必须收割的麦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的调查通讯《女中学生一定要做B超吗?》,记者认为,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也罢,将女中学生作为育龄妇女来加强计划生育防范与管理也罢,每学期做B超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中学生本人也认为是对人格的侮辱。无端成了被怀疑对象,精神压力很大。之后,《文汇报》、《江苏法制报》等多家媒体转载并谴责了此事。评论家刘洪波在《南方周末》撰文认为,“如果这也算精神文明的话,那起码不是社会主义的!”;1999年10月16日《服务导报》的一篇文章对苏南某地多年来取消双休日的做法表示置疑,认为不符合国家有关法规(2000年5月1日苏南某地正式宣布取消长达8年之久的双休日加班制度)。 而就在苏南个别地方“一把手工程”调子唱得最高且有推广蔓延之时,党内一些媒体却表示出另一种忧虑。1997年4月—8月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仅《党建研究内参》、《领导科学》等杂志就前后刊载了杨洪榜《搞好对一把手的监督》,枝江组织部《一把手直接管理财务弊端多》,黄梦其《应纠正滥签“一把手责任状”现象》,杨洪榜《谁来监督一把手?》,姜宁《一把手高度集权的外部原因分析》等文章。其中姜宁的文章指出:“滥且乱的‘一把手工程’不仅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而且破坏了我党长期形成并一贯坚持的集体决策和分工负责的科学管理体制,形成了实际上的‘一长负责制’,权力也随之高度集中。” 苏南个别地方在“创建”中,门面之摆饰,安排之巧妙,招待之周详,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与苏南十分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有关。资源乃至普通民众都掌在官员手里,自然运作自如,左右逢源。而这也是苏南地区城市化不足的原因,市民阶层、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知识分子力量弱小,乃至于被完全忽略。说到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产物。这种对上不对下的运作机制以及吴文化中小处精巧阴柔大处充满浓厚封建等级色彩的僵硬体制,极大地满足了一些“儿科政治家”。 一个地方的地方精神有其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和社会心理基础,张家港的变化主要得力于勤劳、聪明、温顺的张家港人民。如果说张家港是一个成功典型的话,那也完全是因为张家港人民付出了极其坚韧的努力和牺牲。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更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部门赋予是“典型”就可以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权。 十五大之后,人们的视线从苏南、从张家港转到了浙江温州、山东诸城,转到了广东顺德。人们再次公开地将苏南与温州加以比较,并掀起了一股“温州热”。 温州成了“热州”。而这时,理论界“扬温抑苏”的倾向明眼人也一看即知。张义、周虎城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3期上的《江苏乡镇企业与浙江对比引发的思考》一文较系统地将苏、浙乡镇企业进行了比较。文中对江苏乡镇企业增长趋缓的原因归结为: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负担沉重,使企业失血太多;外贸出口增势受挫。1999末—2000年初,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前后登载了四篇文章:林建生,《苏南经济缘何增长乏力?》;新望,《夜扶苏南——从江苏南部一些地区有城无市蜕为空壳说起》;赵伟,《温州力量》;严士凡、林代欣,《走温州的道路是一个基本的选择》。林建生将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汲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严士凡、林代欣的文章也讲到了苏南:“看到一路上农村居民的房子都是同一个样子和档次,我想这一模式不会再给经济发展以动力了,苏南模式的历史任务不克避免地要结束了”;王一新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指出苏南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并指出,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可能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赵伟对旧苏南模式的诟病,则是价值判断层面的指责:“官富民穷”。赵的指责,言微意重,直抵要害。 “温州热”对好面子而又头脑灵活的苏南人带来了不小的刺激。1998年后,苏南一批一批的官员们放下手头日渐清淡的接待工作,南下浙江取经。官员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收获是巨大的。然而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内突然放弃自己的“典范”位置,改掉那些曾引以为自豪的苏南模式的优越性,这个脑筋急转弯还确实有些难度。事实上,这场姗姗来迟的苏南改制却也并不彻底。 不彻底的原因还是对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认识问题。实际上,还是意识形态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以“村办企业”为例。苏南多数村办企业的改制采用了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这种改制虽然解决了经营者持大股的问题,但产权整体上依然是模糊的。要不要社区、企业集体股和要不要集体控股的问题从公社制的失败及乡镇企业改制的目的本身就可得到明确的回答。林毅夫1993年在纽约就早已提出过这个命题,并曾引起一场论战。制度经济学认为,传统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殖。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陈剑波,1993;韩俊、张庆忠,1993,孔泾源,1993;谭秋成,1998)这些道理业已成为共识。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苏南改制只走了前半步,又踟躇不前。可以说,这次改制并未达到产权清晰的目的,或者说,产权清晰了,但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随着人员组织关系的变动,企业经营独立权将难以保障。而且还遗留下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同股同酬问题(集体净资产的增加并不是按股分红的结果,这与《公司法》相矛盾),集体财产的不可分问题(《乡镇企业法》的规定与《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的有关条文相矛盾,前者明显滞后)。 怎么办?今后的趋势:集体股变债权是一个办法;亦可将土地征用折出集体股;城郊则可拿出集体股搞类似于广州天河区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还可以将其按贡献、技术、职务等做配股,量化到个人,不仅享受分红,还可考虑继承;或继续出售给职工、干部、技术人员;还可考虑拿出一部分给改制前后已退休的老职工搞养老保险,这些人在企业创业发展期的高积累低分配机制下,对集体财富的创造是有贡献的,“分给”、“送给”他们一些集体股也是说得过去的。 2000年6月,正在笔者写作这一段文字时,张家港市体改委的一位副主任告诉我,市长再次考察温州归来,市里可能有大决心,新举措。他们最近正在着手准备“二次改制”,因为股份合作制不受《公司法》保护。看来,苏南改制的后半步即将启动。在今年的“三讲”整改中,苏南一些地方对原先的错误或过头做法也得到了纠正。或许“二次改制”能为苏南乡镇企业和苏南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一个飞跃性的变化。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本人私下里总有一种担心,在行政背景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应的改革之前,企业改制、经济改革会不会发生扭曲?会不会在绕完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老路上?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后,苏南将进入无模式时代。然而历史规定着未来,一种模式的历史终结不会像切年糕一样截然断开。苏南乡镇企业有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背景,不是说改就可以改过来的。更不可能以另一种模式取而代之。即就是“二次改制”得以顺利开展,改制后的苏南企业还会面临许多十分复杂而又特殊的问题。当然,主要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问题。苏南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附www.dadafa.com两位网友对本文的评论: 评论1:情况确实如此,我作为苏南人很是担心,但文中提到的温洲模式本人不敢苟同,很多人都知道,浙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假冒伪劣产品,现在在假冒伪劣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资金上搞二次创业,感觉上是肮脏的。 夜迷茫,2000.07.25 评论2:记得还是在大学里,参加一项暑期社会调查,内容涉及到苏南乡镇企业的一些情况。幸亏那篇最后还获了奖的调查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不然它时时会勾起我羞愧的因子。也许可以把原因归结于身处大学校园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但是那里面的一些表面的、想当然的推论不可掩盖地表明我那时缺乏足够的分析和辨别能力。 以政府主导型乡镇工业的飞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长期以来确实为苏州以及整个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崛起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它的缺陷亦是与生俱来,对它的反思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展开。人们都是健于遗忘、不擅反思的,尤其当反思触及到曾经引以为豪的过往的时候,严肃而认真的反思会让人觉得格外刺眼。有一种人不肯反思,原因很微妙,是出于身处某种位置和立场的需要,千万别以为他会天真到看不到现实存在的种种弊端。 乡镇企业的发展中积累的问题无法在其自身的体制环境内解决,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制。和本文作者关注不同的是,我对改制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导致的“流失”更加关心,这些“流失”使得改制更象是一场掠夺而远离体制创新的初衷。难道这是脱胎换骨的代价吗? 所有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神话”,最终都将面临破灭的命运。如果不肯反思的话,那些主要演员必将以闹剧收场,而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新望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