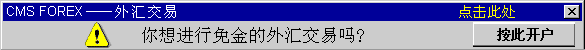|
新 望
毋庸讳言,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苏南模式风光不再,江苏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江苏地方经济史专家储东涛教授早在1998年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对此,江苏境内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有点“集体失语”。为什么失语?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有些事大家心里清楚,不便直说;还有一种情况恐怕是有些道理至今还没有弄明白。譬如说文化观念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价值观论者”遭遇阻击,苏南的变化使“吴文化论者”遇到了同样的难题。那么,究竟与文化有没有关系?
这些年来,我先调查研究乡镇企业改革及发展出路,后又旁骛农村城市化尤其苏南的城市化问题,之后,推及苏南历史、文化、观念、体制诸方面深层问题的思考。每当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之时,深感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的“精神制约”、“制度安排”在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我的思考和看法受到储东涛教授的支持。他认为,区域性经济社会特征中的区域文化视角是最具解释力的要素之一。
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向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支撑。华东地区这些年来形成了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与其文化不无关系。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永嘉文化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而吴文化则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也与其特有的岭南文化大有关系。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肇源地之一。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都不应忽视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如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等)必须了解区域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否则,再好的发展经济学,再精当的厂商理论也显得苍白无力。虽然说不能从观念来推导出现实,但可以从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来解释现实,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的既定性,变革的困难性,发展的特殊性。经济学、社会文化学在中层理论和中观问题研究中将有相互融合之势,这或许是制度经济学一个新的“增长点”。文化沟通历史与未来。任何人不可能轻易地对文化分出高下优劣,但我们可以着眼于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分析区域文化传统究竟有那些因素在其中起着作用,起着什么作用。
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撰写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对中国为何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中国未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鼓舞力量;顾准对东方式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也是建立在与西方尤其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民主文化传统的比较基础之上的;诺思说:“社会生物学家的一大贡献就是把他们的观点引入人类社会的生存特征中去,但他们肯定舍弃了至少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并存在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明显的事实,即人类文化所产生的多样的、矛盾的和无效率的情形。”所以在诺思那里,经济学、经济史和意识形态也是统一的。
在我即将出版的《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一书中,为研究说明苏南之特殊性,我提出了一个“江南小三角”的经济文化区位概念。“江南小三角”在农耕、人口、交通、商贸、乡土工业传统、水利与组织等诸多方面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和外在的独特性。而印证和确立小三角区位概念最有力的证据是吴文化的存在。这二者所涵盖的区域大致重叠。吴文化是小三角的文化底蕴,或者说小三角的地域文化就是吴文化。这一地区属太湖流域,所以也称太湖文化或水文化。如果以最直观的山水地域特征标志来划分和比较区域文化类别的话(如雪域山文化,秦陇高原文化,齐鲁中原的平原文化,巴楚山水文化等),水文化的概念则更准确地反映了小三角地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吴文化是典型而纯粹的水文化,且是一种内陆河湖水文化,与包容量较大、开拓风险意识很强的海洋文化又有所不同。
小三角、水文化、苏南人、苏南模式以及苏南的现状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尤其水文化的经济价值观在苏南的经济社会变迁中居于某种支配地位。水文化的经济价值观有4个方面的基本取向和特征——勤劳,精巧,柔韧,秩序。
勤劳。两熟制或三熟制使小三角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是优越的气候和水田之利赋于此地民众先天的美德。勤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业剩余的增多,正是这种明显的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民众有了普遍强烈的追求剩余的冲动。勤劳吃苦是吴地民众基本的价值观。它主宰并衍生了吴文化的方方面面。刻苦、认真、本分、负责,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做事必底于成,这是一种难得的敬业精神。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就是美好的,这在今天仍是多数民众的生活信条。尽管这种追求和忙碌已在农耕之外了;
精巧。勤劳者必然节俭、节制。与节俭、节制相联着的便是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节制享受,细水长流,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是早期民族资本家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吴文化中的这一伦理传统也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盆景、园林、建筑、绘画、刺绣,吴地民众深受江南仕风之熏染。在情和理的选择中,他们重理,在义和利的选择中,他们重利,重理重利成为吴文化的又一特征。他们擅长经济事务,但人情观念淡薄,亲兄弟,明算帐。无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更合乎游戏规则。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小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是从这种文化传统中汲取了很高的营养,“数目字管理”使这里的企业在成本财务的管理上基本都能过关,粗放式的内部管理很少见到。这种精巧之上的勤劳正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所最最缺乏的;
柔韧。小三角历来赋税重、统治严、压迫深,民众柔韧、隐忍、阴柔的性格便在高压而又富庶的天堂里逐步养成。仕风薰染,人民文而化之,但始终带有一点忧伤、无奈、败落、轻薄的梁陈遗风。做人、做事追求一种“水性”标准。迎来送往,以柔克刚,工于心计,委曲求全,能协调,会妥协,深得中道智慧。水文化其阴柔的一面是恬静、美观、妙不可言,精灵婉约,惟妙惟肖,惟精惟美,擅长竞智和技巧性强的工作;
秩序。主要指组织制度的严密性和成熟性,如科层制、等级制之下人民的各安其份,上下有序。民众这种组织化程度来源于水利之需,但过早产生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发育并未自然过渡到现代民主组织。较强的组织性也正是小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点,并一度成为优势,如有利于有组织地开展运动或发展经济。乡镇企业的最初产生和“创建”的开展即得益于此。也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治安及社会稳定,尤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
吴地民众的经济价值观是上述四个方面特征的综合,这些特征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经济、地理基础,无可选择,是有待发掘的一份宝贵遗产。但当我们今天以横向比较的眼光来评价这份遗产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另外一个方面:缺少伟岸、大气、崇高、苍劲、雄浑、正直和力度,缺乏光明磊落,大义凛然,方方正正,坦坦荡荡;在竞争和追求剩余的过程中,间或出现心理负担和心理健康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幸福快乐)被忽略;过分的算计导致了规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真诚的合作相对困难,坠入阴柔的陷阱;好面子,但缺乏一种大格局,走向形式主义,“面子工程”,“盆景工程”泛滥;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大与小、上与下、死与活始终处在矛盾之中;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渗透着封建礼制的官本位、等级制色彩,缺乏平等观念,由集权到分权的改革也就进展缓慢,市场力量、民间力量过分受制于党政力量,而且官本位(权力的无限延伸和唯官价值观,所有人的价值、地位均换算成行政级别)一旦与吴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结合在一起,“当官意味着发财”也就容易被民众普遍地接受,导致腐败的制度化、世俗化。
在苏南,由于严密的等级秩序观念和旧的僵化体制之残留,政府对企业超强干预,党政力量在市场领域溢出,集体财产社区干部“灰色私有”,造成企业自身经营机制退化,企业负担沉重,失血太多。旧苏南模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tism)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面前面临着严峻挑战。“任务农业”、“政绩经济”显露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弊端,并呈现出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特征。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均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关。而吴文化价值传统和意识形态惯性使身在其中的人们对这种结构性缺陷习久不察,助其成焉。大家普遍认为,每干成一件事都要靠“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如此,所有制结构调整亦如此。政府忙得首尾不顾,市场力量始终缺席。这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体制(荣敬本,1998),将不同岗位基层干部(如分管农业)的日常工作细化为若干分数(如100分)授以奖杯(如“丰收杯”金杯)。分数决定奖杯,奖杯表示政绩,政绩决定升迁。这一制度安排激励出了两个结果,要么社区干部设法控制更多资源(通常以集体公有制的名义),办成更多“实事”,撒胡椒面一般换取分数和“杯子”;要么弄虚作假,糊弄上面。的确,计划体制下,这种制度安排不失其灵敏性,但在市场条件下这却是一种极为僵硬的运作机制。且不说宏观环境和市场变化,另外如私营经济的发展、农业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改革等压根就在“杯子”以外。据我的观察,农村基层社区干部大多是世俗精英,他们最具趋利避害的“经济人”理性。他凭什么要去考虑“杯子”以外的事?他凭什么要去鼓励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干卿何事?除非创新和例外来自上面(只能来自上面)。这时最常用的手法是,领导发一个“号召”,群众搞一场“运动”,干部树几个“典型”。如今,这一套制度已发展成为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在苏南,以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和经济管理体制(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两个转变”已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下一步,应当推动以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为内容的“第三个转变”,而制度变革尤其应以思想观念变革为先行。惟如此,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才能为苏南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吴文化的经济价值观在苏南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作用,需要我们仔细考量。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份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沉重的。
在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由于机动船代替木帆船,长江航道得到迅速开发,海运兴起,河运(尤其是运河)相对衰退,运河的运输地位和苏州的码头集散作用、流动功能随之降低,商人资本外迁,城、市分离,原先繁荣、前沿、创新的商业都会成了单纯的衙门府邸,成了保守、封闭的的“闲庭”、“后院”、“孤城”。苏州几百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商贸中心地位让位与上海,苏南的地缘位置内陆化;在上一个世纪的下半叶,由于杂交稻和石油农业的出现,带来农作物产量的革命,苏南千余年来的“社稷粮仓”作用不再倚重。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结束,“俯仰东南”的畸形财政逐步得以改变,得水田之利的苏州农业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人口与旧产业的矛盾促使其经济结构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期,而周边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发展较快,对苏州的资金、人才都产生了很强的吸纳效应(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苏州两个新区的兴起才使这一状况得以遏止和改善),苏南地位再次衰落;在本世纪里,苏南的制造业优势还将面临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而观念与制度的超越是苏南当前能否走出低谷的决定因素。世纪之交,瞻前顾后,苏南改革与发展面临着全面的、严峻的考验。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