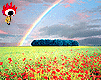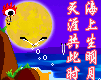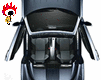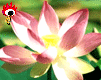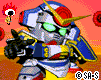上投摩根富林明:在中国基金业中走得长远长久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20日 17:13 科学与财富之价值专刊 | |
|
秦倍钧 问:“上投摩根富林明”一口气念来很长,国内投资人对上投比较熟悉,您能否对“摩根富林明”这一品牌渊源作些介绍。 王鸿嫔:富林明最早是在英国开始做共同基金的,欧洲可以说是富林明家族的根据 地,007就以富林明家族成员为原形。和其他欧美家族不同的是,大约30多年前,富林明就进入了亚洲这个新兴市场,当时,富林明与香港的本地强势公司怡和集团成立了合资资产管理公司怡富,股权各半。 1999年,怡和集团由于战略调整,把其股权出售给了富林明。2000年,顺应90年代后期全球金融业购并浪潮,美国大通银行买下了富林明。其实,在购并富林明之前,大通银行旗下也有资产管理公司,但一般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总不是令人满意,大通也不例外。同年,大通又购并了JP摩根。实际上,大通是所有购并活动的主体,大通的老板很务实,他说既然要做资产管理,那就不需要出现大通的名字,只要出现富林明就可以了,加上合并后JP摩根也补充到资产管理业务,“摩根富林明”就成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品牌。 除了资产管理业务之外,集团在全球的投行业务以JP摩根为品牌拓展,一般商业银行业务由摩根大通银行出面。摩根大通目前在中国大陆有三个分行:上海、北京、天津。 问:您讲得非常精彩,“摩根富林明”这段历史对国内投资人了解“上投摩根富林明”很关键。接下来能否谈谈作为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职业经理人,您个人对两岸基金业有什么理解及感受? 王鸿嫔:其实我到大陆后被问到最多的就是两岸基金业有何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化。 在台湾市场,我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阶段,这十几年也是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这个经验对大陆市场是比较宝贵的。我经常对同事讲,对于怎么做对,我并不见得有多大把握,毕竟中国大陆市场太大了;而对于怎么做会翻车,我很有把握。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各人在聪明才智方面的差距并不太大,差的只是经验。我在与同行及主管机关交流时也讲,有些情况大陆没碰到过,没有意识到会出问题。但对于我而言,由于经历了很多训练,加上JP 摩根对做事的方法要求很严格,长期训练下来,很多事情对我而言是本能的反射。 举个例子,有位同事告诉我,大陆有个分行对我们产品的认同度很高,有些客户需要预购。我当然知道目前行情不是很好,基金并不好卖。当下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做不可以。我其实在台湾也碰到过“提前预购”这种状况,显然这是违法的。我告诉这位同事:你去查一下基金法,没有公告之前,基金公司是不能向特定地区一部分投资者提供预购的。后来在午餐时,有同事说根本没有想这样做会有问题。我说,当然有问题。如果一部分投资者可以提前预购,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对其他地区的投资者不公平呢? 我想我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我被训练得“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并不就是官僚,官僚是一回事,严谨是另一回事。在一些管理细节上,我想能够给大陆带来一些价值。 台湾金融业可以说比较早就进入了战国时期。我自己在台湾富林明干了12年,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同事在香港怡富干了20年。我对同事讲,我们思量所作的每一个决定3年后是否会后悔,我们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 作为富林明,一开始进入亚洲各地都是与当地公司合资开业的,而澳洲、泰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以合资公司名义在当地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富林明合资成功的关键就是本地化。本地化有两层意义:真正了解当地客户,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采用本地的经理人。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找个“大鼻子”做投资,我说我们证明过,“大鼻子”做不过本地基金经理。我们在亚洲的70位基金经理人,95%都是亚洲人。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市场做得最好的都是当地人。在上投摩根富林明,你基本看不到“大鼻子”。我们公司目前的绝大多数人才具备大陆本地市场经验,一个例外是做“基金会计”的同事,他在香港怡富工作了 20年,非常专业。为什么要从香港把他找来,这是因为以后开放QDII,多国货币,多个交易所交易,多种避险工具,内地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金融业人才流动率非常高,但是这个公司比较独特,我工作了12年,来自香港的这位同事工作了20年,证明公司内部文化留得住人。 在台湾,我也会被问及营销方面的经验。我说,基本上我完全不需要讲理论上的知识,这些MBA教科书上都有,关键是在实际中,你究竟有没有站在客户立场上思考问题。在台湾这些年,自己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的经历。我认为最难的是为投资人的利益着想,究竟该怎么做。往往你自己觉得很好的选择,可能并不适合投资人。全世界投资人都有一个习惯—— 看排行榜买基金。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买最好的可能并不适合你。现在大陆才100多只基金,而我进台湾 市场时就有800多只基金,有投资欧洲的、日本的、泰国的等等。因此,如果在800多只基金中排行前列的,可想而知其所投的市场早已经涨起来了。我曾碰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台湾一名退休教师,在银行买了26只基金,总计投入资金折合人民币六七百万元,他买的全部都是名牌基金,而银行投资顾问推荐的依据就是各种基金排行榜。问题就出在他在买入时没有考虑时点,实际上,银行的推荐并没有帮客户的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敢不敢对客户说“NO”。哪些有所为哪些有所不为,这才是你的附加价值。 记得在1999年,摩根富林明旗下基金在亚洲市场的表现很强,其中泰国、韩国基金表现得特别好。在1997年金融风暴时,这两个国家也是受伤最深的。经过2年多的改革,这两个国家坏账率下去了,GDP有所增长,因此,韩国、泰国两个市场冲得很快。当时,我们就意识到单一市场的风险很大,因此告知营销人员不准主动推销两个市场的基金,如果客户要买就买亚洲区域型基金。这样,相对风险较小。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后来我们看到销售报表,投资这两个市场的基金销售额依旧大量增长,显然销售人员仍在“煽火”,在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们受到了批评。在今年4月,我们在亚洲地区4个中小盘基金干脆停止认购。当时宏观调控尚未出台,我们已经感觉到行情过热,如果钱再进来,一来会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找不到价位好的股票,如果硬去买,也要损害其他投资人的利益。 这样做,我们受到的压力很大,压力不仅来自于投资人,内部销售人员也表示为什么不让我做生意。不过2个月后就有客户来信感谢我们。我想我们全球的团队运作了150年,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你可能觉得在当时来看像个傻子,可是从长期而言会受益的。客户受益,公司才会受益。我们希望对大陆基金业的贡献就是——合法合规绝对可以做好一家公司,而合法合规最后才能生存下去。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今年第一,二季度之交,不少人在讨论券商能否将销售基金的数量与今后基金在券商那儿的交易量挂钩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在全世界摆明了是违法的,事实上也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摩根富林明活了150年,资产还在不断壮大,我很难相信如果这样做它还会生存下来,不这样做充其量少卖几个亿,但这样做最大的风险是公司会因此关门。 基金公司要为投资人尽善良财产管理的义务,可是如果根据券商代销量创造交易量,那么,你把投资人利益放在哪里?任何一个投资者拿到基公司和券商签订的补充协议都可以把基金公司告倒。对我而言,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本能的反应。我不觉得人的聪明才智有多大区别,我们只是被训练得这样。 JP摩根内部有很多训练课程。我从去年来做合资公司,许多时间又在外地,尽管如此,还是参加了总部的网上培训,其中包括洗钱防治法、信息技术、控制风险政策等。好在其后的相关考试我都通过了,分数还蛮高。后来我感到,这些东西已经被我内化了,成了本能的反应,我的形容是像“呼吸”一样平常。不单单是我,我的同事今后都会落实这些观念。 另外一个对我比较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融合到同一个公司文化中。虽然大家都讲中国话,但彼此在理解上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大家都能明确方向,工作上默契地配合,最后结果不会差太远。 问:合资基金公司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很大,能否透露一些“上投摩根富林明”的情况? 王鸿嫔:我们公司有60多位员工,对我们而言,员工人数倒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资源放在哪里。其实,无论是JP摩根还是上国投,都有能力组建一个大公司,可是除了资金上的压力之外,找人也很不容易,更不要说把大家的观念融合在一起。我们在内地的策略比较注重长期,短期微调会比较谨慎。记得在筹建时,我对同事讲,要把眼光放到10年后,在募集第一个基金时,第二只和第三只基金已在议程中。现在我想的是明年的工作目标和三年目标。等到第一只基金募集结束,我们打了一圈仗回来,我们就会明白资源要放在哪里。 我们不希望打混仗,行情不好时发保本基金,行情好时发股票基金。我们现在需要加紧把不同类型的产品线建好,中国内大陆市场很大,我们要走得够长久。 问:我们还是来谈谈“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基金”设计的初衷。 王鸿嫔:当初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首先思考的是作为合资公司,能够带来什么不同。我们希望这个产品能够有一个长期卖点。现在中国大陆有100多只基金,可能很快就会有1000多只。因此,包括基金的命名如何显示出区别来,我在不断地问自己这些问题。 那时候,我们看了许多大陆机构的报告,发现其共同特点是关起门来做调研,但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法逆转,就算你不走出国门,海外竞争者也会不断涌进来。哪些公司能够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我们需要用国际投资人的视野来看大陆上市公司。尽管同样是大陆企业,H股市盈率硬生生要比A股低许多倍,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值得投资的A股。 无论在哪里,WTO开放的过程都有阶段性。如果一层层筛选下去,会发现金融业、电信、媒体、国防产业等都在不同阶段受到国家的保护。中国一向具备成本优势,而开放后,企业不仅仅要在大陆拿第一,如果参加奥运会,至少要进前八强。同时,中国企业要具备内需优势,占据大陆广大市场。中国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无论产量、消耗量都排名世界前列。此外,像港口、公路企业具备垄断优势。中药、白酒企业有文化优势。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是,中国企业要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不能老关在家里。 记得这次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我去一家水泥公司调研,这家公司在香港及台湾地区上市。该公司认为其是宏观调控受益者,理由是宏调帮助其淘汰大陆竞争对手。其实温总理讲话后,A股还比中国香港、韩国、印度等市场跌得少,但这家公司的股价还是翻红了。 中国的企业要意识到,如果无法应对眼前的变化,下一波的挑战一定会被淘汰。大陆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一定有可以活下来的,可是竞争将很残酷。 三年、五年后,现在中国的五大优势——成本、内需、自然资源、垄断、文化可能会有变化,可是用国际视野检测中国优势企业的方法不会改变。 问:“中国优势基金”这个名字很漂亮,你们公司广告中代表上投摩根富林明这只基金形象的“毛笔”也很漂亮。能否讲讲这支“笔”的由来。 王鸿嫔:当时广告公司设计了许多方案,最后选择“毛笔”确实不是我的决定。每次设计送来,都会让新来的同事看设计是否易懂,是否有东方味。由于我们是合资公司,怕别人说洋味太重。其实,摩根富林明是第一批拿下 B股席位的海外资产管理公司,其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很大,比如H股、红筹股、B股。可是一般投资者不了解这些,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个简单易懂又富有东方味的基金标识。 我们对此还做过调研,无论北京、上海、广州,认同的基金标识几乎一致 ——金鸡蛋,财神爷。可是这和我们公司的品味不太符合,因此最后选择了 “毛笔”。这个过程其实也预示了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与大陆投资人进行沟通。 问:对于合资基金公司,目前普遍评价是蛮高的。你感到对比众多合资对手,上投摩根富林明的独特性在哪里? 王鸿嫔:大陆众多合资基金公司,暂且不论中方和外方,背景其实是不同的。即使是大陆机构投资人也都不很清楚,各家金融集团各有擅长,能够面面俱到的并不多。如果以投资理念划分,有些擅长主动型,有的是被动型。被动型的指数基金中,管理资产金额最大的是美国道富银行。摩根富林明没有发行过各类指数型基金,一直以管理主动型基金为主。摩根富林明管理的7000多亿美元资产中除了全世界中央银行、政府社保资金之外,世界500强的80%都是其客户。摩根富林明管理的共同基金与专户比例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有些金融机构管理固定收益比较强,比如说富兰克林,同时其在新兴市场的股票投资也比较强。像国联安的安联的强项在于保险。JP摩根富林明专注于资产管理,刚才讲的7000多亿美元全部是做资产管理业务的。合资基金公司中的外方有些是从银行体系来的,有些来自于保险体系,各家的专长不一样。 问:最后想问您的是,台湾地区的同质性很强,而大陆是一个差异性巨大的市场,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王鸿嫔:中国大陆市场很大,我不会想一下子通吃。因此我会设定一些阶段性的目标,3年、5年要做到什么。具体的东西还不太明确,不太方便讲。股东的要求是先求好,再求大。面临中国大陆这个独特的市场,先求大往往是事倍功半。股东给我的头三年的目标有三个,按照优先顺序,依次是长期稳定的经营业绩;好的客户关系,这里面有些量化的指标;合法合规,不能吃任何一个处分。股东没有给我财务目标。实际上,如果这三个目标都能达到,自然会实现财务指标。 今年6月,一位摩根富林明集团的主管来上海参加公司开业的活动,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加入富林明,快40年了,期间石油危机、冷战、各种金融风暴、柏林墙倒塌,各种大风大浪他都经历了。他对我说:mandy(我的英文名),你要把这三件事做好,后面自然会顺起来。但这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没做好,你的财务目标就不能实现。我想,特别是对于我们销售部门的同事,除了需要累积一定的客户量,赢得客户满意度是同样重要的工作目标。 所谓高的客户满意度不完全是基金业绩,基金业绩很难每年都名列前茅,但如果能够提供好的服务,让客户相信你,客户忠诚度自然会很高。 我经常会问同事,你究竟有没有站在客户立场上来想问题。不仅仅是想,而是真的去做。记得公司在分布不断电系统时,系统只能维持一半约30 名员工在断电时继续工作。因此,需要进行优先顺序排列。董事长,总经理,部门总监,一级级排下来。为什么要这样排序呢?我说,如果断电的话,什么最重要?什么不能断?交易不能断,客户如果要查询基金资料,也不能断。所以,基金经理不能断,基金会计不能断,客户服务不能断,最不重要的就是总经理、董事长,又不接电话,又不做交易,断就断了。因此,我们的流程和别人不一样。 我还听到一位客户反映,我们的公司介绍手册和其他基金公司的不一样,开头没有董事长、总经理讲话。当时,我们把所有的基金公司及银行介绍手册拿来,讨论公司介绍中什么是人家最想看到的,什么是最不想看到的。我说如果我是客户,会直接把前面老总讲话都撕掉,那是浪费钱。对客户而言,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公司的投资团队和投资流程。我对同事讲,首先要取悦客户,取悦领导在其次,常常这样想,行动的思路就会不同。 公司的文化就是要敢于相信专业。我现在的专业在于管理,我要确定每一个人在岗位上是否称职,公司运行方向是否正确。我们公司投决会主席是基金经理吕俊,他们是市场第一线人员,我不会去干涉他们的投资决策。如果大家都去看盘,那么谁来考虑公司3年、5年后的位置。在一些管理课程中也有测试:总经理在日常工作安排中,如果考虑未来时间低于5个百分比,可见这家公司没有什么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分权分责,要相信同事。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基金债券 > 新基金业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