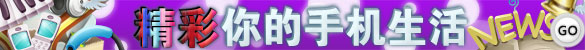为生活和自由调色:走近著名油画家向光



《肖像》向光作

《黄花地》向光作

《三匹马》向光作
心灵自由赋予艺术家灵感之翅,艺术家方可飞翔。飞翔的方向要向着爱美、爱生活、创造美的方向。我们要融入生活外师造化,又要用绝大部分的生命翱翔在理想国度中得心源,那么一切苦乐虚实,皆在笔墨有无间以艺进道。——向光
“我的脸啊,就像一张抹桌布,气色不佳……”在电话里,向光半认真地向未曾谋面的拜访者这样描绘自己。见面之后,这位年已75岁,手握画笔却超过半个世纪的老油画家,老顽童似地冲着我们直笑:他分明面光红润、鬑鬑生白须,一派仙风道骨。
早在1994年,向老先生受美国缅因美术学院邀请前往讲学并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被誉为“具有欧洲绘画和中国绘画双重传统的现代绘画”;而在他贵州任教的20余年间,培养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中、青年画家。在一些评论家眼里,这位对贵州油画有开拓性贡献的油画大家,一直隐于市而不事张扬。
“我不是油画大家,但我是有独特画风的油画家。”坐在一瓶栀子花香营造的清凉世界里,向老先生本人像极了一幅静态的人物写生画。
大虚大实:中西双重传统下的现代绘画
向光挂在墙上或者印在书页上的画作,初看起来让人瞠目:画中意象充满着粗狂的原始气息,丝毫没有精雕细琢的工笔刻画。《百合》、《无色瓶》、《花与果》等景物系列,充满质感的造型与肆意欲滴的色彩,浓烈得略带夸张与虚幻;更有甚者,在表现树林和马儿狂奔的作品《行空》系列与《林中之舞》中,画图里的马和树木似乎与天上的云彩融为一体,充满着抽象意味的狂草意象。
《世界艺术》杂志主编徐亮说,向光的画大都是心灵跳荡、情绪抑郁或奔放的那刻所作,其作品几乎都是趁灵感降临时一气呵成,在较短时间内迅疾把新鲜的思维和感觉在画布上固定下来,狂草奔放。他的画是具有中西绘画双重传统的现代绘画。
向光自己也说,西方外来的形式可以融合在中国绘画的意象里,“就像不同的宗教在最高层次是殊途同归一样,中西绘画传统在最后也是融为一体的。”
1957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系时,主要学的是苏联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技巧。在严格的西式油画学院派的训练下,向光开始学会用形式语言来认识世界,用线条和色块来解释和展现美的构成。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只有上界才有美,但几何形是美的。”他掌握了开启美学之门的一把钥匙。
接触到表现主义中抽象、夸张的意象后,他意识这和中国绘画的“虚境”传统有相通之处,而现实主义则类似于“实境”传统。向光说这印证了中国画论的核心一句:“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
向光思索开来了:“艺术家要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总是要发现一点新的东西吧。如果只是满足一般的成就,那么很可能充当留声机、翻拍机的角色,停留在匠人的层次。好的艺术家就是要创造美,引导美,用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要做艺术家的向光下定决心“自我”一些,闯出一条新路来。
他开始融合中西绘画传统,“就像一群人到朋友那儿去玩,看见朋友花园里一簇花很美。有的人摘下几枝插在花瓶里,花无百日红,很快就会枯萎;有的人采下几株种在自己的花园里,花还是原样;我是施行嫁接的办法,花才可以旧貌换新颜。”
“开始时,多少会觉得中西传统的冲突,但一旦心里有了融合的倾向,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融合了。至于现代形式不必多虑。生活在现代,很自然的会流露出现代意识。”向光认真地补充说,“不过,现代意识虽然无处不在,但绝不等于抛弃传统,就是现代化了的。没这么简单。没有爹妈,自己从哪来的呢?”为了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站在传统沃土的他时常是刮目观异、洗耳闻新的,“一个人一生随时要想到更新自己。艺术家的身子可以老,心是不能老的。”他对自我的要求是,每个笔触间都要能做到“无一笔无来历,无一笔无新意”。
向老将他的绘画体系用“自由、自在、自信、自为、自圆”来概括:心灵自由是一切灵赋的本源;自在是个性的独立王国;自信是在自知自量基础上冲向未知的敢死;自为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精神辐射;自圆是完善自我的内省过程。
好艺术家骨子里都有“逍遥”、“虚室生白”、“唯道集虚”的道家气象,“自由、自在、自为”划入此,故能“大虚”;好的艺术家同样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时,能够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具有自强不息的儒家风骨,“自信、自圆”归入此,故能“大实”。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绘画生涯的向老,身体力行地融合着“道家气象”与“儒家风骨”。
而在作画的实践上,他擅长多用画刀。“这能很好地表现一种大虚大实的气象,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画风。”在艺术境界上多处谈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向光,在此明确强调说,“而这一切之先,是自己要爱美、爱生活。”
以艺进道:以出世的态度绘入世的画作
“俞伯牙跟着老师成连学琴,三年小有成效。但还不能精神寂寞、神情专一。有一天,成连去东海蓬莱山,独留伯牙。十多天过去了,也不见成连回来。此时的伯牙延颈四望,只见海水扬扬,只闻群鸟悲号,在一片孤寂中,伯牙受到了大自然强烈的震撼,生活上的遭遇,使得整个心境都受到了洗涤,才达到了艺术的最深体会,完成了他对美的感受和创造。”向光说这是一个“移我情”的摄物归心过程。
在“文革”期间,他也遭遇到了一片孤寂。“在我读中央美院的时候,就因为‘只专不红’被划为‘白旗’颇受不公正待遇。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最偏远的普定县。”从此将贵州视为自己故乡的向老说,在此期间,他深刻体会到了在绘画创造中苦乐相生的过程,“苦的首先是心志,是尚不成熟的学术迷茫,其次是创作环境差。我下车后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遍地的茅草棚,原来是当地的居民为了积攒过往人的粪便而搭的。一路泥泞,满地牛屎、猪粪,简直无处下脚。当晚在一处楼阁睡觉时,就受到了蛇捉老鼠的阵阵惊扰……”条件虽然艰辛,向光还是冒着“资本主义作风”的风险,将居所地板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用旧报纸把四壁和顶糊了两层……安身的阁楼成了“安乐窝”。他要时刻保持身心的洁净,“天地的变化是无情的。但艺术的天地,是感情天地,理想天地,爱和美在那里永生。”
做什么事都特别上心认真的向光,下地劳动时,插秧、挑担子比真正的农民都狠,一次抡秋的活干下来,一口气便可割到五十窝稻子;可以挑一百三十斤重担走十里不歇肩;一顿可以吃三碗苞谷饭……“作为有过长期战斗、劳动、学习锻炼的我,在大山大岭间挥汗淋淋,在崎岖道路上足迹层层,目的是恭行‘劳筋骨、苦心志’的理念。追求世事在内心冲突的平衡,为艺术事业积淀朴厚的底蕴。”向光说。
几乎没有时间作画,绘画题材也受到严格限制,他开始在画“毛主席像”中磨练画技。“文革”时的普定县,曾建起了几面长十米,高八米的墙,他扑在墙上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在北戴河》等巨幅油画。每逢赶场时,这几面墙前便人头攒动,场面壮观,此事一度轰动四方。也就在这段期间,向光极大的磨练了自己,他又快又好的画技广为人们所称道。
“毛主席像”画得好,浩劫期间的向光被借调到了贵阳。冷静看待政治运动的他,始终以一个艺术家的要求自律着,并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向光当了九年的“逍遥派”,成了一个“文革”的旁观者,有空就带着一批年轻的画家到贵阳及其周边的各个山头、丘陵去写生,这批画家日后也各有所成。无形中,向光对贵州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打倒“四人帮”前后,调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的向光,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那时他两个小时画出的肖像画,已在任何展厅都挂得下,他说这些“没有持日旷久、脚踏实地的艰苦和寂寞,是单纯在书斋里画几幅画所换不来的”。
“心灵自由赋予艺术家灵感之翅,艺术家方可飞翔。飞翔的方向要向着爱美、爱生活、创造美的方向。我们要融入生活外师造化,又要用绝大部分的生命翱翔在理想国度中得心源,那么一切苦乐虚实,皆在笔墨有无间以艺进道。”向光的方向,就是要以出世的态度绘入世的画作。
“入世的所见所闻只是我绘画的一个药引子。”而今,近十年来不再写生的向光,只靠印象便可旁若无人地书写心中的山壑意象。他以攻守有备的立世胆气,自信人生三百年。
向光而生:我心里种着一颗绘画的花种
有一次,向光受邀给120多个中学美术教师上课。“他们见我一个老头子,一个个东倒西歪地坐着。”向光接着说:“你们的眼神告诉我,你们嫌我老了,但我深信我有机会不断证明在许多方面你们比我老。今天初次见面,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那就是一条垂直线、一条水平线构成的一个十字架,你们把它带在胸前,永远不要拿下,将可受用终身。这是一个视觉坐标,也是一个人生坐标,无论是初学者或大师都离不开它,这个十字架在我这里解释为:做人要直,处事要平。”
这些学生立马被震住了。
成名以后,他在心中画着这个“十字架”,时刻自戒自圆着。他在《老树独白》中写道:“名利的危险远胜利斧的威胁。最近有人要为自己及活着的画家们建造一座座豪华坟墓,树碑立传,名曰载入史册。他们还要载入我的姓名,这可不行!本某一无所成,不堪史册之誉。请不要拿我殉葬,请不要把我活埋!我还有长长的开花的使命。”
向老以这样一种不宽容不妥协的姿态,坚守着艺术上的美以及自我。早在搞“四清”时,他就曾反对领导让农民挑红土把白墙涂红,搞“红化”的做法:“你们把墙涂红了,还有瓦呢?涂了瓦,还有山呢?树呢?还有蓝天、白云呢?……”
出身湖南富有地主家庭的他永远记得第一次“画画”的情形:“7、8岁的时候,从未学习过绘画的我突然兴起,用木炭在大门外的白墙上画了一群鸟。长尾的,短尾的,穿格子衣服的,穿点子衣服的,飞的,跑的……正得意,祖父持一根竹枝走来,令我跪在自己的第一张壁画前。”忽然,背后一个声音,中断了家审。“孺子前程未可量也!”是向光的外公笑着对祖父说。这幅“涂鸦画”没有被擦掉,历经了许多风雨,依然清楚。
这一画就画了半个多世纪,“画有能力决定我是什么人、想当什么人,以及会变成什么人。”向光说,以往只是一个参照,没有什么比未知的魅力更大了,我们一生下来便在未知的牵引下走向死亡,而我们要有冲向未知的敢死,这也是他能永葆艺术青春的诀窍,而艺术青春也会反哺他的心田绿地。
“孩子们,我是来抗衰老的,你们的年轻对我是一种大补。”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年轻人的向光,永远想到的是以后会怎样,他是洗耳闻新、向光而生的。心里种着一颗绘画花种的向老,通过嫁接开的花,开得越来越像他自己,正如他笑言的,“我天生是要开花的”。
至今一入画室,便如入无人之境的向光,仍能连续画5、6个小时不觉疲倦。一生沉浸在绘画的缠绵苦乐之中,随时随地有幸福陪伴着的向老,优哉游哉。
向光简介
193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954年调北京军区文化部“战友社”任美编;195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肖峰油画工作室。1962年毕业,分配到贵州基层,1975年调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教至1994年。向光在艺术教学过程中,学风严谨,见解独到,培养了不少颇具影响的中青年画家,对贵州油画有开拓性贡献。
2000至2004年,先后受聘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
早在1994年,受美国缅因美术学院之邀,向光教授前往讲学并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被誉为“具有欧洲绘画和中国绘画双重传统的现代绘画”。在超过五十年的绘画生涯中,其作品不断发表于报刊杂志,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展览,并有不少作品被国内外单位及个人收藏。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