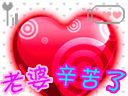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十多年前拙劣的账外经营手法始终不死,意味着操作风险依然巨大,也就意味着有理由对当前改革的顺序进行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银行案件恰如“矿难”和“禽流感”。
与矿难相同的是,在现有的银行组织管理框架下,处于科层结构末端的支行所发生的
种种交易恰如数百米下的矿井,高层管理者与基层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只能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加以描述,其心态亦只能是自求多福。与禽流感相同的是,金融交易风险往往在瞬间就可以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传染,特别是票据融资,在一系列的承兑、贴现、转贴现过程中,大量的银行都可能被拉入一个致命的交易。
当然,恰恰是这些现象构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依据,由此进一步提示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实施正确的银行治理。
刚刚案发的中国银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的9.146亿元承兑汇票大案,在技术手段上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几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银行信贷账外经营的翻版——银行内部人“借用”重要空白凭证实施账外放款,绕过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以进行“地下金融交易”。
由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深刻的:第一,为什么如此不具备技术含量的盗窃行为可以在十多年间连续重复?第二,地下金融这一似乎只能与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形式相关联的操作,如何不断出现在正规金融机构层面上?第三,面对涉案金额巨大的银行案件,我们需要的是等待改革绩效渐进式地显现的耐心,还是需要在既定的银行改革大方向下,认真踏实地思考某些具体步骤安排的轻重缓急,以此寻求最优的金融转型顺序安排?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单个银行的管理体制、银行体系的风险传递,以及当前的银行金融服务体制进行多层次的思考。
不统一的法人与地下金融交易
银行法人治理已经是一个被说滥了的名词,但是,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按照西方经典的法人治理理论进行中国式银行改革的实践之时,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迅速出现在我们面前。
比如,我们关心的内部经营者与外部所有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中显然被夸大了——有理由认为,无论银行的最高层经营者面临怎样的激励或约束,其经营银行的积极性是无需加以怀疑的。其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自身是否具有向所有者负责的正确激励,而在于其管理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法人。法人的统一性在于,在一家银行内部,其分支机构是否能按照法人的整体经营方略进行操作;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依然需要着手解决“名义上的统一法人、实质上的诸侯银行”问题。
反思四马路中行的案件特征,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不统一的银行法人内部的地下金融组织体系。
一是“寄生牟利”。简单地说,四马路中行的票据案是一种账外经营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诈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串通,故意使用过期或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属于票据欺诈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票据是否在交易前或交易进行中就已经“作废”。
事实是,《金融时报》在2006年2月11日公告双鸭山中行的34张票据作废,而案发则是在之前的2月7日。票据流通的基本特点是其“无因性”,这是各国的通例,即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票据的接受方只要明确知道票据的真实性,就可以放心接受并进入下一步转贴现、再贴现等交易。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票据接受方的建设银行莱钢支行,并无证据显示其存在交易环节上的过错,问题出在出票的四马路中行。事实上,“作废在后”而“交易在前”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了中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主要负责人通过账外经营以寄生牟利的手段:其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在交易期间并非假票或废票,各种签章也具有完全的真实性,惟一的问题是,作为法人的银行自身被基层的操作者蒙在鼓里。因此,整个交易并不完全适用于《票据法》所定义的“票据诈骗”,而是中国屡禁不止的账外经营。
账外经营的初衷,是交易的直接操作者依托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的地下金融交易,目的是通过寄生于正规金融组织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或关联融资利益。因此,交易的基础不在于银行外部,而在于银行内部的基层管理者,后者的寄生牟利是整个交易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共谋交易”。虽然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作为持票人的民营企业主朱德全与四马路中行的利益交易关系,但其共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自2003年3月起,四马路中行的96张承兑汇票被“盗用”,如果没有里应外合,其盗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问题在于,双方的交易行为却严格属于共谋以损害银行权益的行为,且必然存在某种利益分割。
一方面,银行的账外经营因其地下金融的特点而几乎无一例外具有“高利贷”性质,这种高利贷实际是一类风险贴水,是对冒险违规的补贴;另一方面,借款人也面临着风险-收益的衡量。只要资金成本在社会平均成本附近,且属于自身可承受范围内,接受这种交易本身并无不妥。但是,由于是账外经营,整个银行将面临极度危险的状态,大量资金通过账外流入实体经济,导致所谓的“贷存比”、“资本充足率”、“风险资产总额”等水面上的统计指标根本无从反映水面下的真实风险。
三是“偶然事发”。人事轮换导致银行案件事发是另一个通例,四马路中行的情形也不例外。恰恰是后任行长不认前任行长的账外账,才导致之后的票据宣布作废。这一案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常规的内部稽核为什么无法发现合规性上的漏洞,操作风险是否必然在人事轮换之后才能被发觉。案发的偶然性导致了犯罪的低风险。
因此,这里的问题依然在于,中国的分支机构众多的大型商业银行能否真正在制度上建立纵向一体化,各层次信息流、数据流完整通畅的管理体系。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追究责任人的体制进步,但是,真正需要问的依然是:谁应该为银行不统一的法人格局承担责任,是具体责任人还是银行管理制度?
系统性金融风险下信用基础的动摇
票据是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债权、债务凭证,其高度流通性体现在票据融资的承兑、贴现、转贴现、再贴现等一系列过程。至少在当前,银行间的票据交易,实际上把各家行的信贷在整个银行体系内进行了重新组合,而这种资产的组合实际上意味着风险的传递。四马路中行票据融资案,就充分体现了风险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流转。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其结果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基础的动摇。
一是从非系统性风险通过传染与扩散,演变为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票据的签发行与票据贴现行往往不是一家机构,如果票据本身存在权利瑕疵,其贴现行因贴现导致资金已经交给持票人,往往面临损失。我们回顾案发一开始的情形,中行宣布票据作废,实际上是并不承认自身承担的承兑责任(无条件见票即付),这意味着建设银行承担了中国银行法人治理缺位导致的事实上的信用风险。倘若贴现的机构又发生了转贴现,把债权进一步转移到其他机构,其风险就具有了传染性。
我们不能肯定,在庞大的票据流通市场上,到底有多少汇票具有地下金融的色彩。这一疑问是合乎情理的——毕竟在四马路中行主要负责人轮岗之前,其签发的56张汇票经历了承兑、贴现和承兑行支付,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因此,整个事件可以视同四马路中行发生的单个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通过票据交易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传染;尽管交易过程中并未出现症状,但如果发案就等于死亡。这种因法人治理上的漏洞导致的地下金融如果具有普遍性,则整个市场的风险难以设想的。
二是信用基础和金融生态的进一步恶化。票据存在的惟一理由是流动性;银行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信用;票据造假的结果是两者存在的理由几乎荡然无存。有大量的个案证明,社会信用基础的薄弱,与银行自身内部控制和交易形式有关。
四马路中行的案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账外经营导致具有权利瑕疵的票据在银行间票据市场流通,那么,银行之间的不信任将导致信用基础的动摇:各方对于对方承兑的票据持怀疑态度,其结果是市场流通性的下降,而对于票据而言,便捷流通几乎是其存在的惟一理由。缺乏流动性意味着市场的萎缩。另一方面,银行基层内部人自身的造假行为,证明了银行不仅仅是金融生态环境的受害者,也是恶化金融生态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其行为颠覆的是银行赖以生存的惟一理由——信用。
改革次序需要重新评估
四马路中行案件给我们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十多年前拙劣的账外经营手法沉渣泛起,意味着操作风险依然巨大,也就意味着有理由对当前改革的顺序进行思考。
显然,目前按照从所有制到管理流程的方式进行改革,那么,机构的扁平化、风险控制的条线垂直化等管理模式,是否必须滞后进行?显然,当务之急是把一家银行变成真正统一的法人,至少其总行对支行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其次才有理由进入股权、产品创新乃至服务等层次的变革。毕竟,对于银行而言,安全性永远是高于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第一要素。
对比电信、石油行业的重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中存有“重上市,轻重组”的取向。这里或许包含着“以上市促重组”、“以开放促改革”的无奈,但现实的教训提醒我们,应当在坚定改革决心的前提下,对于银行改革的步骤做出更理性的安排。如果各家银行均以上市为核心目标,并以上市时间表倒推安排各项重组工作,极易使改革更多地停留在财务重组层面,而上市前对于银行治理结构、业务模式、风险控制等深层次的重组则难以展开。
电信和石油行业改革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以重组为本,改革才能真正取得理想的效果。中石油在2000年上市之前,按照业务板块对整个集团进行了脱胎换骨的纵向重组,财务实现了垂直管理,取消了多法人层次,完成真正的商业化改造。
反观几大国有银行,除了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拨备覆盖率等财务指标在大量公帑注入后达到或接近了国际水平,并未进行针对性的组织结构调整、建立战略单元;统一的财务管理、信息管理和风险控制系统均未建立;人事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改革行之未远;分行一级的改革尚未完成。总体上看,改革仍停留总行层面,并未触及到银行庞大的真正肌理,银行经营运行机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七分重组,三分上市”,四马路中行案的教训,再次提醒人们这一被市场重复了无数次的基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