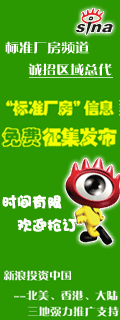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超女超男是对艺术的玷污”,全国政协常委兼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先生的这一说法引起轩然大波。4月24日,他就此进一步明确表态:“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参加超女的被害了,看这个节目的也被害了,我就这么一个看法。”(4月25日《华夏时报》)
对于超女超男是否“是对艺术的玷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有发表意见的
权利。我不想掺和。可是,“不应该允许超女存在”的高见一出,我却觉得有掺和的必要了。
“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有何凭据?是因为其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因为其有悖于公序良俗?似乎并没有见刘忠德先生给出这方面的有力论据。
“开窗开门新鲜空气进来,肯定也有苍蝇蚊子进来”,刘忠德先生只不过是霸道地将超女定性为“苍蝇蚊子”,并武断地认为“观众是在用扭曲的心理、不健康的状态看这个节目……不能让我们的年轻人在娱乐和笑声当中受到毒害”。别人是否怀着扭曲的心理观看、是否在笑声中受毒害,刘忠德先生又是如何知道的呢?这是想当然,还是拿着大棒压人?我不是超女迷,自然谈不上刘忠德先生所说的被“害”,可是我身边的“玉米”、“凉粉”、“盒饭”们的思想、精神似乎依然都很健康,没见被“害”成啥样。
超女或许不是什么“阳春白雪”,但即便是属于“下里巴人”,难道就连存在也不被允许了吗?要知道,“下里巴人”才“曲低和众”,而且超女并不比其他一些流行的文艺更粗俗,反而有可取之处。对某一种文艺的风行,只要它合乎法律、不乖风俗,还是不要管得太具体得好。
在逝世前两天的1980年10月8日,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他认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出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的,也限制不了的”。这是赵丹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惨痛经历写下的肺腑之言,振聋发聩。他曾经在“管得太具体”中,多少年想演鲁迅而不可得,“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更曾在“管得太具体”中,只能在“牛棚”中空耗年华。为何不引以为戒,却依然想管得细致而微,以至于要不允许某一种文艺存在呢?既然“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赵丹语),那更大可不必将某一种文艺扣上个帽子予以封杀。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巴金据此认为,“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超女之所以受到追捧,或许也与其把文艺交还给人民有相当的关系——公众得以更直接地参与,并在积极的参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乐趣,文艺变得更可亲可近。
罢黜超女,就能让所谓的高雅文艺独尊起来吗?实在很不见得。人民为何对某些所谓的高雅文艺不待见,大约与其失去了人民性而只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也不无关系。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有价值的自会流传下来,没有价值的最终只能湮没无闻。强行扶持什么,不见得有效。强行封杀什么,也终于是徒劳。对于文艺的兴衰更替,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心态。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见识更高明,更不要想当然地替公众作出价值判断。要相信人民能把握好属于自己的文艺。
在刘忠德先生的所谓被“害”与“管得太具体”之间,我宁愿选择被“害”,也不愿选择被管得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