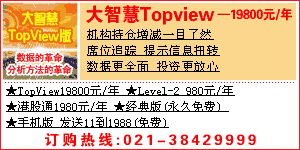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沉重的书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8日 10:17 经济观察报
胡蓉萍 小晨走在中关村南大街那一片红白校服中。她背上的双肩书包里装着各科课本、各科笔记本、学校的练习册、“轻巧夺冠”和“龙门题库”练习册、习题、卷子、水杯。她走得很快,脑袋与双肩使劲向前努着,这样的姿势可以帮助她与身后的大书包抗衡。 这是10月普通的一天。清晨的迷雾还没有散去,晨练的人们刚刚出了家门。小晨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初三一个普通数学实验班的学生。书包里的一切,还不是她所有的装备。“副科的书都放桌位了,主课的都得背着。” 这一天在《曹刿论战》的晨读声中开始,在每日例行的“统练”中结束。 放学后,小晨在学校附近的麦当劳等爸爸。她的桌子上除了一包薯条的空间外,已被化学卷子和草稿纸摊满。月考的成绩出来了,小晨没有进前10名,这让她觉得很郁闷。“我在看到底错在哪里,怎么没得分。” 所谓月考,就是每个月都有的考试,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时间。10月份的月考是在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天进行的,于是,整个长假期间,小晨都在准备月考。这一类型的考试是北京市海淀区统一考试,分数出来后全区、全年级、全班统一排名。 “的确是要练要学,但是很压抑,考试太高密度了——可也没办法。”考试几乎天天有。人大附中初三都是周一考语文、周二体育、周三数学、周四物理化学和体育轮流、周五英语。 这被称为“统练”。这种考试不进行统一排名,但时不时会公布均分以及均分以上学生名单。 最后的中考冲刺阶段,又有若干次模拟考试。已考试卷、带回家作业的试卷、试卷参考答案,每天都在她书包中占有一席之地,厚厚一大叠是常事。 小晨爸爸难得有空接她一次,“主要想帮孩子扛书包回家”。小晨在麦当劳看化学试卷的样子让他想到自己,那个年代的学校生涯是另一番景象。放学路上,把书包随便往草丛里一扔,就拿出毽子来和同学游戏,或者成群结队地去抓知了、抓蝴蝶、抓草蜢、摘草药、挖野草,或者独自享受连环画。他感慨于那份童年应有的轻松心境,多年以后自己的孩子却体味不到。 他那个时候,同学们的书包有的是家里自己缝的布袋子,有的是斜挎式的军用书包。“这种书包不大,里面隔成两层,一层放书,一层放笔,所有的课本加起来也就是五六本,那时候课本都薄,纸张也没那么厚。如果装小晨的这些书,带子立马就断。” 上个世纪70年代还在小学当教师的谢奶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她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前半堂课讲课,后半堂课做练习。问题当场解决,不留到课后。” 不过,进入80年代之后,一切都在改变。小晨爸爸初中毕业的1982年,关于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文件就已经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1987年,相似的内容被列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间,教育主管部门颁发过6份“减负”的文件。 文件越来越多,书包的份量却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书包的份量几乎暗示着学校老师和孩子们面对高考应有的重视程度。 1995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绍兴一中副校长王柏根清楚地记得,儿子1992、1993年读小学时很轻松,三点半就放学。“但1995年之后就不行了,越减负越严重。”有40多年教龄的谢奶奶也有同感。1995年她尚未退休,“从那时候开始到我退休,讲课、补习的邀请就没断过。” 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自1995年以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第49份关于“减负”的文件。 在北京,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门仍在下达“禁止补课令”,严禁中小学校和各种社会补习班提前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毕业生举办升学补习班。同年,北京、广东、河北、浙江、江苏等地纷纷出台有关规定或采取措施,禁止举办收费的“奥数班”和叫停奥赛。 2007年10月,如果你来到北京市人大附中,很可能在校门口看到那些各路补习班的推销员。一个推销员的口号是“体现全新家教模式,承诺百分百”。他说,这家家教中心以北京为基地,成立11年已扩张到四个大型培训基地、18个教学部,50多个教学点,800多名专职教师,且学校采取“教练式教学,将学生当作场内运动员对待”。这11年,也是舆论高喊“减负”的11年。 这些培训学校还为学生的书包量身定制了他们自己编写的各科教材。“把重点都列了出来,特别适合考试。” 孩子们不堪重负。小晨说:“我们初三也有很多长白头发的,高中的哥哥姐姐更多,有的一个班级有一半。至于近视,基本上都是了。” 据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对东北76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进行心理检测发现:35%的中学生具有心理异常的表现,近30%的小学生心理素质处于不及格水平,而优秀或良好者仅占8.2%,原因是巨大的压力下 “心理超负荷运行”,“长期紧张在心理中的积淀”。 60多岁的退休教师谢奶奶回顾她40多年教学生涯的时候,还是觉得她的第一批学生学习最轻松愉快。60年代初,20出头的她经常和学生一起拔草、捡稻籽头、爬树、爬竹竿,做泥娃娃。“那时候很多孩子甚至都不用书包。” “爬树爬竹,我常常和孩子们说要脚上带点摩擦力才能爬得上去。”谢奶奶回忆说,“看到两只船往前自然划动,到了一定的距离会自然吸引,就很好地理解了流体力学,并且相互联系了起来。” 在谢奶奶临退休的时候,她很心痛地看到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表,都是家长到社区里面盖章了事,根本没有真正去实践,“都去上辅导班了”。她很遗憾以前的老方法并没有机会被事实证明它的好处。“但是我还是坚信,那是快乐的教学方法。老师也快乐,因为不用抓升学率!” 绍兴一中王柏根副校长说:“现在老师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学生考试成绩是硬考核指标,我们没有尝试的权力,必须适应高考指挥棒。”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柏根用他的军用书包和五六本指定教材这些“全部家当”考上了当时的杭州大学 (现已并入浙大)。他的儿子2004年考入吉林大学金融系。“那一年,我们全家都觉得解放了,整理儿子中学用过的教材、参考资料、复习题,整整一个书柜。” 现在的孩子在学会踢毽子之前就知道:上小学的目的是为了上好初中,上好初中的目的是为了上好高中,上好高中的目的是为了上好大学,上好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好工作。 今天,对于小晨,即便是练琴这种课外活动,也有考级压着。很多时候,她的书包里还装着画笔、调色板、口风琴。大人们把孩子们所能玩的东西都编排出能考级的内容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职业,可孩子们所能玩的东西都变了味。 甚至连书包的生产厂家都明白,孩子的肩膀已经不能承担那么重的份量了。他们专门为学生生产出了带拉杆和滑轮的书包,卖得很好。西单商场的促销员拍着胸脯说:“重量再增加一倍都没问题,绝对不用再担心书包带子断了。” 为儿子自编教材的儿童作家郑渊洁则再次愤怒了:“将学生书包的拉杆和滑轮拆掉,装在国家身上,让学生的书包越来越轻,国家的分量越来越重。” 当年简易的军绿色斜挎书包如今已成为“古董”,开始被批量生产,印上五角星、毛主席像或者雷锋叔叔,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纪念品。当小晨爸爸在北京市的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看到这些熟悉的物品时,常常感到困惑。他想不明白,今天的孩子背着装有各个学科、各国语言、各种厚词典、各种新型文具的书包,究竟要去向哪里?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