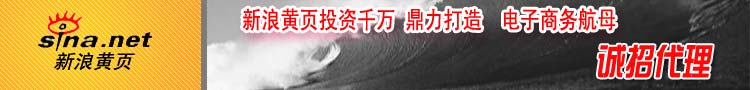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上)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9日 23:28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 现代化总会带来问题,尤其是文化和价值层面。 今天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能在不同价值体系比量中,清楚自己的立场,还说得清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呢? 对中国而言,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富强,它也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 问题的关键是,当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塌之际,怎样为解除文化危机寻找一个立足点?传统的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该如何发用? 本报以此颇看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的对话,以期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困境有所启发。本文将分两次刊发。 是为“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系列之二。 ──与金耀基教授对话 文/刘梦溪 1. 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 刘梦溪:您在我个人以及一般知识界人士心目中,主要是一位文化—社会学者。您与其他从事同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的不同之处,是您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感和现代感。您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两书,内地知识界也很重视。您似乎想用现代的方法解开传统的锁链,冀图消除沉重的中国人的现代紧张。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背后,一定贯注一种学术精神。请您谈谈您的专业选择过程和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精神旨趣。 金耀基:我的研究主要环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不能不碰到文化问题。对长期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开始我只是个旁观者,后来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进去。但我发现,整个问题不是中西新旧文化论战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想改变论争的语境。这是我在三十余年前写《从传统到现代》的缘由。 我对社会学发生兴趣,是1964年去美,接触到了社会学的新理论,尤其是哈佛帕森斯(Parsons)的理论。当时社会学理论对我有影响。所以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那一篇,有我的乐观性,也可以说有些过分乐观。不过,我也对现代的有些趋势忧虑。所以,我也写了《现代人的梦魇》。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必须要现代化,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过当时我对现代化尽管非常殷切,可以说是拥抱现代化,但始终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 Paz)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可也是唯一的理性出路。中国何尝不是如此?现代化总是会带来问题,但这是唯一的出路。除了现代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问题只是我们应如何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现代化。 中国向来是一个有自己特殊的文明秩序的国家。但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瓦解了,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怎么建?从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不在解构,也没有一样不需重构。当时是清末,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所谓二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王韬(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著名报人)看到了这种变化是文明秩序的变化,不是朝代的变化。尽管很多人对中国传统的某些方面很执著,但是也在变,不得不变。往哪里变?现成的文明秩序摆在那里,这就是西方的新文明秩序。需知道,西方本身的传统秩序也经历了强烈的变化过程,这变化先从欧洲到美洲,等到西方的现代化通过军事与经济敲叩中华帝国的大门时,西欧与美国已被现代化全面改造过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所以常相混淆,原因就在这里。说到底是欧洲先走向了现代化,在世界文明秩序里建立了最早的一种现代性模式,这也是目前唯一的支配性模式。由于当时西方现代化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凶毒面目出现在中国,所以,中国一方面不得不“西化”,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总有厌惧感,总有抵拒意识。 如果不出现西方的现代型文明秩序,今日世界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一个文明秩序发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今日不论在哪个城市,西方的、东方的,都有现代的东西,如机场、五星级酒店、大学、工厂,软件的、硬件的,相同性很大,它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国家出路思考问题。十九世纪以后,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总是不知不觉被拉进大的文化论争?从早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戊戌维新,无非都是为国家找出路。曾国藩或者还可以说是为了清廷的利益,到了新文化运动,就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了。但中国之为中国靠什么?没有中国文化还能形成中国?为了中国的发展可以牺牲中国文化?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有时还会改变方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连在一起。 刘梦溪:这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寻找新的,于是便全部抛弃旧的;一种是既要新的,又要旧的,但找不到整合的途径,陷入两难;还有一种是为了既有文化秩序的失落而痛苦,如王国维就是这样。陈寅恪说,越是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当这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便越感苦痛,所以王走向了自杀的道路。在王国维之前,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也是因此自杀的。 金耀基:王国维的死有深刻的个人因素,当然他选择的文化意义不可低估。印度的甘地,也是受现代的冲击,但他不想工业化,为的是要保持住印度的文化认同。尼赫鲁不是这样,他也为印度,但却推动工业化,走向现代化。胡适,也是如此。但他提出“充分世界化”,也就是西化。所以如此,因为西方现代的模式已经摆在那里,成为唯一的参照系,没有别的路好走(“五四”的知识分子是不惜去掉中国文化以救中华民族的)。直到今天,谈民主、人权,争论的也还是中西问题。整体地讲,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的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导,这里当然涉及文化霸权的问题。 2. 文明秩序的“旧”与“新” 金耀基:今天谈精神文明,首先应该问是什么精神文明。十九世纪后,中国的固有文明遇到西方的挑战,一败再败,已被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干所抛弃。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大陆成为主流,但如果说开来,也是一种西方思想,是“反西方的西方主义”。 刘梦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涉及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到底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以前内地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强调对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金耀基:“批判地继承”应该是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理念或者态度。 刘梦溪:这个口号又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连结起来,对传统作截然的二分,其实是很困难的,未免过于简单。 金耀基:我的立论是不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说到底,现代只有从传统中来,所以我三十余年前写的书叫《从传统到现代》。讲传统,不能不讲文化。从十六世纪到今天,世界的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形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俄国,想改变自己的经济模式,希望进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简单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文明秩序。 刘梦溪:所以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个常新的课题。晚清以来这一百年,不管枝蔓出多少意外之笔,大题目、中心题旨,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问题。“命定地走向现代化”,这个讲法很深切,只是在中国道路太不平坦了。 3. “软心肠”与“硬心肠”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确极不平坦,走了不少弯路。二十世纪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又是传统解构的过程,香港、台湾、大陆,都是如此。解构的过程也是重构的过程,解构与重构同时进行。当然谈这个过程,有时会感到痛苦,这涉及到传统价值解体、失落。中国的事,软心肠不行,我有软心肠,有时也只好硬起心肠。 刘梦溪:是的,传统价值的解体,难免令人有失落感。而且许多问题不好深究。深究,会伤害所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在学理上应该如此;在心理上,难免有所不忍。 金耀基: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他研究社会学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忍受多少,看到真相,有时是痛苦的。研究中国文化也是这样。中国的绘画、书法、建筑,大家都知道很好,但中国文化中也有许多东西实在不好,它阻碍现代化,不能不扬弃。人应该有两副心肠,太软心肠,不敢面对问题;太硬心肠,对应该保护的东西不知珍惜。 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重新发掘自己的历史,探讨传统文化是否有转化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当然有变化,从先秦到汉,到宋,到明清,都有不同。但根本上是农业文明没有改变。所以清末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许多人不知所措。某大臣看见西方轮船驶过,风驰电掣,惊悸之余,不觉晕倒、呕血。最初理解的现代化,都是关于技术方面的,如造炮、建船、开矿。康有为看到政治制度也不行,才有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的意识。中国历史上是政教合一(不同于欧洲的政教合一)、王权至上,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思想家,但没有人怀疑过君主专制的政治形式(Form)。 刘梦溪:明末,黄宗羲、唐甄等曾指出过君权泛滥的危害,有的批评相当尖锐,甚至说周秦以来当皇帝的都是贼,当时被称作“天崩地解”时代,很大的一股思想潮流。 金耀基:他们所讲的不全算是新东西,先秦思想家就提出过。抨击君权无限扩大,要以百姓之命为命,指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君主不得据以为私,这种呼吁,代不乏人,根源是民本思想。顾炎武看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认为三代之盛,可以徐还,即回到过去的理想境界。中国一直有一种历史观念,以为现在的问题是先前的理想境界被破坏了,改变现状的办法和出路,是如何恢复到往昔的理想境界。直到十九世纪末,在西方的挑激下,才真正思考新的政治形式。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做皇帝,这就有了西方民主的观念。在孙中山手中,中国第一次出现民主的政治形式。新文化运动是思想革命,是对辛亥革命的补充。严格地说,孙中山不是中国文化“化”出来的人,夸大一点说,他是一个边际人,是中西文化的边际人,也因此,对中西文化都有一定欣赏,对中国传统政治,他是革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有一副软心肠。 我觉得,近人对孙中山在政治革命上的成就估得偏低。应指出,中国的文明秩序,归根结底是以政治秩序为中心的。 刘梦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政治是中心,但民间的空间是很大的,始终存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民间社会。特别是乡村,天高皇帝远,朝廷的政治触角不一定都能接触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传播,在民间传播得更为广泛。 金耀基: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量是绝不能低估的。魏特夫(K. Wittfogel,美籍德裔汉学家,1896-1988)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有一章专门讲“国家强于社会”,此书虽有夸张处,但它看到专制主义的本质。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中央权力确实退缩,民间以是而有空间。但整个局面,还是国家强于社会。传统中国始终未出现过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徐复观先生对中国的专制政治的性格谈得很清楚。民间社会的作用,还是有它的制限。 刘梦溪: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也有在朝在野之分。宋以后程朱的思想被朝廷认可,王阳明的思想则主要影响于下层社会。被朝廷认可的思想,作为道统,与政统、治统既相一致又有矛盾。 金耀基:道统与政统一直存在。孔子被尊为素王,是道统的代表。历代君主都尊孔,但道统与政统的紧张性是存在的,它对政统构成某种洗涤作用,但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东林党人,作用是留下了风骨,但毕竟无法以道统来“制衡”政统。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以身殉道,成仁赴义,惊天地、泣鬼神,在道德上诚是了不起,但对政治起的影响很微弱,实在是代价大、作用小。 传统杰出士人的风骨、气节诚然可嘉,但也带有浪漫与悲剧的性质。是“血染的风采”,这不是合理的秩序所应有的,在民主制度之下,何必用血染的风采把历史长廊染成这样悲壮?应该是平常人、平常心、平常制度。民主其实是平常人的制度。 刘梦溪:您这番话,让我感觉到了政治理性的力量。制度与人、理与情,有时有矛盾。中国传统社会本身,我认为存在着多重制衡的关系。官府、民间,在朝、在野,固然有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作为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释、道三家,彼此之间也有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给知识分子以相当广阔的个人精神空间。但这些资源怎样在今天发用,仍然是极大的问题。 金耀基:今天的新儒家中,有些学者就在思考传统资源怎样在今天发用的问题。 4. 新儒家问题 刘梦溪:台湾思想界对新儒家意见比较大。新儒家本身似乎也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在新儒家中成就最突出了,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体系化以后,自我完成了,突破也就难了。杜维明先生更注重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与东亚经济秩序的联系比较紧密,他研究活的东西比较活。 金耀基:这个问题可以讲几点。十几年前,台湾《联合报》开过一个会议。我说,提倡儒家思想,最大的挑战是它与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相干”。它最大的危机是变得不相干。换句话说,在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构(现代化就是新文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在人间伦理秩序的建构方面,新儒家能提出东西,就是相干的,否则就不相干。这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期待。 现在的新儒家,例如杜维明、刘述先,他们了解现代化的挑战,他们讲新儒家,直接、间接都希望与新的文明秩序的建立有相干性。讲到新儒家,可以说是儒家在中国文化舞台退隐后的“重来”。二十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出现之后,学术的主流掌握在胡适一些学人手里,儒家学者已处在边缘位置。一九四九年后,钱穆、唐君毅等先生南下香港,则不啻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自我放逐。 刘梦溪: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被放逐、处在中心之外,也不是坏事,反而可以在学术上获得独立,学风也因此会更为纯正。二十世纪一些被世潮冲到边岸的学人,今天去掉尘埃,重新评价,反而见出他们学术思想的恒在性。我个人颇同情也很理解这种处境。我在台北,一次去士林外双溪,这个地名使我若有所悟。我说这就是我的文化定位,我可能应该算是“士林”里面的“外双溪”一族罢。 金耀基:四十年代末,许多学人到了香港,香港那时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一边缘地方。但钱、唐等(较后,徐复观、牟宗三先生也去了新亚)先生在香港办校讲学、著书立说,宣扬中国文化,蔚然成气候;而七十年代之后,香港经济飞跃,更成为世界金融贸易的中心。更可一提者,由于东亚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思想界转而重视传统价值的思考。尤其是日本的发展,说明传统是可以和现代相接相容的,儒学之重来与东亚之现代化是不能分开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前居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初叶之后则每况愈下。严格言之,五四运动并不是完全打击中国文化,而是对儒家的“去中心”,削弱儒家的地位。 刘梦溪:是这样。晚清诸子学的复兴,就是为了耗散、消解儒家的地位,这在章太炎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有一篇《诸子学略说》,专门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金耀基:当然,在今日的思想学术舞台,新儒家并不处于中心位置。儒学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中国时的支配性位置。不过,一批关切中国文化生命的学者(包括新儒家),是在二十世纪儒学隐退之后(几次重返都没有成功),为儒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发用来作学术努力,这是很有意义的。 刘梦溪:他们对儒学有虔敬之心,对传统资源的现代作用怀有热忱。 金耀基:声音已经不是苍凉,并且有自信。 刘梦溪: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新儒家》,不知您怎样看? 金耀基:余英时先生这篇文章极有分量,他对老师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的定位自非泛泛之论。钱先生是大儒、通儒,但他不愿把自己归为特殊定义的新儒家,这一点,我们要尊重,更值得新儒家的深思。余英时作为历史学家,对新儒家提出很冷静解构性的阐释,但他完全没有要抹杀新儒家的意思。 刘梦溪:新儒家所关切的,无非是当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塌之际,为解除文化危机寻找一个立足点,这初意是极好的。余英时先生只是觉得新儒家的努力无法达致社会起信的作用,也担心偏向否定科学的极端。杜维明对儒学的推动,与现代社会生活、现代经济秩序结合起来了,在学理上已是变化了的新儒家,或者应该算是新儒家的新的支派。 金耀基:是的。中国固有文明秩序的解体,固然涉及思想文化层面,但真正的解体还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所以新儒家若要在中国现代新文明秩序的重构中起作用,不能不结合社会的各个制度层面与日常的生活世界。 刘梦溪:陈寅恪就说过,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制度法律及公私生活方面,而学说方面,反不如佛学和道教的影响大。因此这就有了矛盾,也可以说是学人之思和生活之理的矛盾。 金耀基:文化不落实到行为,是不落实的文明。文化必须充分体现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落实到政治、经济,特别是家庭社会的生活中,所以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文明秩序。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旧的文明秩序一直在解体中,当然,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在探索一个新的文明秩序。我觉得新儒学不但对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化可以有贡献,它还可以对“现代性”的批判提供资源与智慧。 5. 中国文化的耗散与重构 刘梦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陷入的危机,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除。传统资源在现代社会能否发用是一个问题。前几年我曾提出,中国文化由于自身的特点不容易凝结为传统,而有传统也不容易传承,这是更为严重的危机。 金耀基:中国文化的危机,当然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有关。事实上,许多非西方社会,面临西方的挑战,都出现传统本土文化的危机。不过,在中国这种文化危机感特别强。有一点似可提出,一百年来,中国的精英,不论是政治人士或知识分子,其解救中国危机的方案,几乎都以打倒或清除中国文化为要务。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文化传统的传承怎能不出现断层?何况有时还有像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系统的破坏。不过,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十分强韧的,中国文化有危机,并非中国文化就死了。我相信,在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中国文化的材料与资源的融入,当然,也必然会借取移植外来的文化。 刘梦溪:文化需要移植、嫁接,不移植不能勃发生机。 金耀基:佛教之入中国,产生宋代的新儒学,并发展了中国式佛教,便是最明显例子。再冷静地看,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就移植了无数的东西,从经济制度到电影、音乐,不论是穿的、住的、行的,有多少不是从外面移植来的。这没有什么不可,但只是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稀薄了。我们对传统批判得太过分了。结果是二十年代的中国人“看不起”传统,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看不见”传统。这样,又如何谈保存和发扬文化传统? 刘梦溪: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常常是一面讲要发扬传统,同时又极轻视、极轻贱自己的传统。现在主要是传统价值系统崩溃而又找不到重构途径的危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传承既然缺少合适的渠道,那么重构也难得取径有门。而在此过程当中,个体的精神危机早已产生了。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精神的定在性,不知从哪里来,也不很明白到哪里去。陈寅恪说晚清以后的中国成了非驴非马之国,我看不仅仅是痛乎言之。文化失衡了,中国人立足的根基在很多人身上看不到了。文化人、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最有精神的定在性的,实际上,正是这个阶层最缺少精神的定在性。 金耀基:在文明秩序交错影响的过程当中,特别需要你说的精神的定在性,但拥有这种精神有一定难度。这需要对传统的价值有一种体认、执着与认同。 刘梦溪:曾国藩是有这种精神的。咸同时期的“中兴诸将”,不少都有这种精神。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有这种精神。陈寅恪本人也有这种精神。明清易代,清朝的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手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定在性消磨得很厉害。清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张扬。后来,扭曲得更厉害了。 金耀基:对价值的失落与混乱,就不易有精神的定在性。不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可能更困扰,不同价值的内心交战,更使中国人立足的根基著不上力。这也许是中国现代人的一种处境。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价值已无或很少旧士人那种宗教感的执著。现代的西方人,也有这种通象。现代西方人,正如韦伯所言,所面对的是一个“解魅的世界”,意义都发生了问题。这也可说是“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 刘梦溪:精神的定在性,是与信仰相连结的。没有信仰,谈不上精神的定在性。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俗世化的世界,连宗教都走上了俗世化的路,个体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非常难找了。 金耀基:大概这就是现代人的命运吧。
【发表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