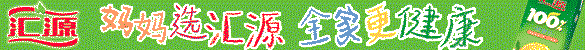|
刘 晗
2005年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一百年。以“历史的终结”扬名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特地撰文纪念指出,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所展现的不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宗教因素。实际上韦伯将现代性(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归于新教伦理,曾支配和影响了几代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无论韦伯的具体论断是否正确,
其试图揭示西方文明传统的独特性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重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这本1993年就翻译过来的大部头同样是从宗教来切入西方文明传统,但与韦伯关注新教不同的是,伯尔曼更看重天主教教皇革命对于西方近代法律传统乃至整个文明的影响。特别地,伯尔曼在论述商法的时候集中探讨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似与韦伯针锋相对地指出,“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天主教会不仅不谴责金钱或财富本身,而且确确实实地鼓励追求金钱或财富,只要从事这种追求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商人的经济活动就像其他世俗活动一样,它们不再被认为必定是‘对拯救的一种威胁’;相反,……被认为是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并且“法律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一座桥梁”。
看来,这部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法律史书就不仅限于法学,而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其处理的问题和韦伯旗鼓相当。韦伯的论题完全可以限缩成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西方能出现独一无二的法律秩序。
伯尔曼异乎寻常的追问,什么是“西方”?在他看来,“西方是不能借助罗盘来找到的”。地理上的边界有助于确定它的位置,但这种边界时时变动,因为西方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概念。“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伯尔曼透析了西方文明的成分,但又超越了诸种因素,从而统摄了整个西方的概念。
实际上,由以上诸种古代文明传统型塑的西方传统中,自然法与实在法、神法与世俗法之间的张力,乃是整个法制演化的动力关键所在。两者的张力如何在近代进行调和,西方的法律自治传统如何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中世纪,在多元的世俗组织(庄园、城市、王室)的欧洲世界中催生,乃是伯尔曼分析的着力所在。伯尔曼指出,1075年到1122年的教皇革命(格里高利改革)促成了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的诞生。随之而来的是职业法律家阶层、中世纪大学的法学院、法律专著,以及法律作为自治的、完整的和发展的体系的概念等。更重要的是,教会成为了第一个世俗利益集团,受教会法治理,是现代类型的国家(伯尔曼特别指出教会贬低了王权的作用也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兴起提供了条件)。并且,教会秉承神法治理,是一个拥有高级法(Higher Law)背景的世俗组织,从而将自然法与实在法、神法与世俗法完美结合。教皇革命因此也整合了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和罗马法传统,形成了整个西方大统,并传续千年。
同时,教皇革命在创造了教会法的同时,还催生了世俗法体系。教会法虽然在契约法、婚姻法上很见效力,但“几乎完全不涉及诸如财产法、犯罪和侵权行为、程序、继承等这样一类规则”,而这恰需要世俗法的补充。并且,这些“现世的”和“世俗的”组织及其法律(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固然存在缺陷,但也趋向着自然法、神法,被期待模仿教会法,从而与教会法构成了完整的近代法律体系。此外,现代人们普遍憧憬的法治观念,也诞生于教皇革命促生下的世俗法体系,因为每一个教会和世俗团体的首脑都应当采用和维护其自身法律体系,依法而治(Rule by Law),同时该首脑又受法律约束,也即在法律之下统治(Rule under Law),最后由于教会法和世俗法的管辖权二元体系,两者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于是两种权力只有通过承认法律高于两者才能和平共处,因此形成了法治(Rule of Law)的共同承认。
由此,伯尔曼就从教皇革命以及其诞生的法律体系中总结出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十个要素: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法律人的职业化、法律职业者在有高级学问独立机构接受培训、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的复杂辩证关系、法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法律被人信仰、法律的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历史性、法律高于政治权威、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西方法律传统的思想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的紧张关系。其中最后一种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的周期性冲击(宗教改革、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等)。但西方法律传统存活了下来,且由这些革命所更新。
伯尔曼的鸿篇巨制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为解决在他看来的西方法律传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千载而下,西方法律传统的前四个特征依然存续,但后六个却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了严重削弱。伯尔曼写道:“对种族、阶级、性别和世代的基本划分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特征。信仰的纽带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亲属关系和土地的纽带已经让位给各种模糊、抽象的民族主义。随着稳固的社会共同体的崩溃,对于以法律为手段去保护精神价值不受腐败的社会势力、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侵害,西方人不再具有信心。”而《法律与宗教》中伯尔曼的慨叹:“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
在西方法律传统已延续近千年的21世纪,重读此作对于国人之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重温伯尔曼总结出来的静态的十条特征,并试图将之移植到中国来,而毋宁是借伯尔曼富有历史感的文字,从动态上进入西方法律传统,重新阅读西方。在一个礼法政教架构基本稳定的社会,法学自然可以退身为法条解释和政策分析等技术性细节,但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对历史的追思切问就是法律人无可回避的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刻,那恒久的问题再一次逼迫人们做出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法律与革命》的末尾,伯尔曼用引文说道,“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一如他在导论中对教皇革命的赞叹:“为了设计未来,他们不惜试图回归过去。”我们尤其需要伯尔曼似的忧患感和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要回顾西方,还要回归自己。或许,套用席勒那悖论式的句子,“我们的过去还没有到来。”
(建议阅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法律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