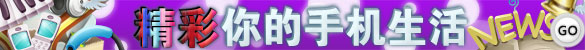中国金融:防通缩还是防通胀
防通缩还是防通胀
——访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本刊记者 赵雪芳
目前中国经济尚没有形成通胀压力
记者:随着前5个月信贷投放的较大幅度增长,很多学者有了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的预期;而CPI、PPI数据连续5个月负增长,也使经济尚未走出通缩的论调加剧,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形势?
左小蕾:CPI和PPI连续几个月的负增长,说明当前中国经济依旧处于通缩状态。因此,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呈现的恢复态势主要是政策刺激效果显现,民间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仍有待进一步激活。价格水平,不论是PPI还是CPI,还在下降和低位运行,通缩仍然是主要担心。当前中国经济尚没有形成通胀的压力。
在全球化特别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论是
全球“流动性”输入,还是全球大宗产品的价格输入,都是中国通胀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也没有通胀形成的外部条件。
但是,中国经济上半年创纪录的货币投放规模和速度,已经引发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特别是“已经形成”新一轮“通胀预期”的观点越来越强烈。我认为,对于这一观点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首先,有必要对“通胀的担心”和“已经形成通胀预期”的观点进行严格的区分。到目前为止,这次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人们产生了对通胀的担心,说明人们已经对货币增长可能带来的通胀后果有了一种知识性的认识,但不能说这就是通胀预期的形成。认识到通胀与货币增加有关,承认通胀预期的影响,都不意味着这次创纪录的货币增长已经形成通胀预期。许多分析担心大规模的货币增长可能会引发“将来”的通胀,这个推理从经济学常识的角度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和近期就要发生的“通胀预期”,或者说对通胀的心理预期的形成,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已经形成通胀预期”的判断,不仅仅存在对“不确定期限的未来”通胀的担心,而且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已经切实影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正常行为,将会导致真实通胀的发生。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消费行为仍比较审慎,不存在为了避免减少价格上涨而出现抢购的现象;生产者还在消化存货,没有囤积商品待价而沽。当前中国经济显然没有形成所谓的“通胀预期”。
其次,通胀预期形成不是与货币增加如影随形的。大量经济学实证研究显示,货币增加与通货膨胀发生一般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时间。我们应该注意到,大规模的货币增长一般是应对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政策行为。在经济没有被有效激活之前,货币发行遭遇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陷阱”,不可能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真正通胀预期形成应该是在,经济不仅开始复苏,而且经济的有效需求已经被激活,为拯救经济增加的货币已经随着经济活动开始较快循环,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和货币创造能力,推动经济较快增长进而带动价格水平也加快上涨的时候。没有任何通货膨胀是与货币增加如影随形的。
美国2001年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直到2004年才出现全球大宗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和房地产价格的膨胀。所以通胀的担心应该发生在经济开始复苏以后,而不是今年。为了防止高通胀卷土重来,明年下半年要特别注意政策的调整。
防通胀要把握好时机
记者:很多专家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短期内我国经济要防通缩,但中长期要防通胀,您认为未来在防止通胀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左小蕾:应该肯定的是,中国货币政策从2004年开始的调整,全面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对遏制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通货膨胀水平的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首先,防通胀要把握好时机。美联储前主席马丁先生有句名言: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防止通胀应该何时出手。在这方面,我认为,货币政策要把握好两个时点,一个是国内经济稳定的时点。这应该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虽然中国目前没有指标来界定经济增长是否恢复到稳定水平,我们可以从潜在增长率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为9%~9.5%,这个指标稳定至少两个季度以上且相应的价格水平呈上涨态势时,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稳定水平。第二,应该配合参考就业率的改善、工业增加值的上涨、消费增长率的提升等一些增长质量指标发出的信号。第三,PMI以及发电量这样一些领先指标持续在50% 以上的较高水平或者较长时间保持增长态势。符合这些条件时,货币政策应该开始适度紧缩。
具体来讲,货币规模紧缩可以有几个选择。第一,提高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减少对过剩产能行业的资金投入,推动较大的产业整合;第二,保持M 2的增长率在稍许超出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上涨之和的水平上,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与价格水平上涨所需的货币需求,使经济各方面都平稳而不是高风险的增长;第三,减少银行新增贷款规模,降低乘数效应。只要合理运用利率工具以及一些数量工具,准确把握调控时点,货币政策防止通胀的效应应该非常显著。
其次,中国经济控制通胀还要注意外部因素。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通胀的输入型特征非常明显。比如,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通胀,与2004年开始的资本流入,以及结汇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也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球大宗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密切相关。
关注信贷大规模增加风险
记者:有报道指出,前5个月投放的巨量的信贷资金,除了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进入中小企业,您如何看待当前大规模的信贷投入及其潜在风险?
左小蕾:今年前5个月,银行新增贷款5.8万亿元,预计上半年会突破6万亿元,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从积极的方面解读,银行系统能够如此迅速回应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大规模调动资金配套财政投入,显示了金融体系的调整弹性,也显示了我国经济体系的调整弹性。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走出这一轮经济困境的重要保证。相比较美国、欧洲的金融体系几近瘫痪的局面,中国金融系统在恢复经济增长中充分显示了活力。
但同时,银行突发式的大规模信贷也带来诸多隐忧。首先,未来银行坏账增加的风险加大。这些贷款较大部分是配套政府项目信贷,有极大的政策性因素。对项目的审核、风险的评估、收益和还贷能力的分析是否到位,是否能够严格操作,是否会带来银行坏账的上升以及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政策性新增贷款的大幅增加伴随的低投资效率,是银行体系不可忽视的隐忧。其次,银行新增贷款虽然增加较多,但要达到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目的,还需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乘数效应。如果这只是一个静态数字,只是一个“存量”概念,资金的周转不是很活跃,不能产生乘数效应,说明经济尚没有恢复活力。第二个问题,是否能够拉动民间投资。如果银行贷款把有收益的投资机会抢占,产生对民间资本的排斥作用,没有拉动民间投资,这对恢复经济的活力,对保8%增长,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要保8%的经济增长,总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至少要达到15万亿元,仅靠银行的信贷显然不可能达到如此的投资规模。但是在经济下滑期间,企业利润下降,民间投资审慎,政策需要采取“不与民争利”的措施,比如采取贴息、补助等措施,以及通过让民间资本参与有利可图的项目等方式,争取引导民间投资达到 1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第三个问题,银行新增贷款是否流向中小企业。从保增长、保就业的角度看,扶植中小企业是这一轮经济恢复增长的关键。
此外,还要关注如此大的信贷投资规模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这是银行信贷规模增长是否能够推动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投资增长就可以通过工资传导到最终消费,进而再增加投资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创造就业,投资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这将进一步拖累今后的经济增长。■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