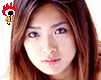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陈燮阳:一切都与音乐有关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6日 16:09 《全球财经观察》 | ||||||||
|
他带着一只不锈钢水杯和三支细长指挥棍,辗转世界各地演出;他在莘庄的别墅里种满鲜花,闲时爱欣赏花团锦簇。已经65岁的陈燮阳回望自己大半生,一切都是与音乐有关。站到指挥台上,背对着观众的时刻,便是他最沉醉最快乐的时刻 文|苏德
上海交响乐团在湖南路105号的大院子里,甬道两旁布满乔木群,越走向深处越是平坦的安静,偶尔从排练厅里传来断续的大提琴声,显得更为幽谧。下个月,上海交响乐团就要赴台演出,因此这些天,平均每天5小时的排练时间对每个参演团员而言是逃不掉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陈燮阳。 从排练厅下来的时候,陈燮阳已经满头大汗,顺势朝团长室的皮椅上一靠,倦态显然。接着,他开始修改一张节目单。他脱下眼镜,凑近了节目单仔细看,一笔一画地勾勒,格外谨慎,圈画到自己熟悉的曲目,还不自觉地哼出声来,像个刚进音乐学院的孩子。节目单搞定后,他顺手从面前桌子上拿起一只不锈钢细长水杯,倒了些水,边喝边说:“它跟着我快要跑遍全世界了。” 从外表来看,花白的头发,精瘦的骨骼,陈燮阳有些吝啬言辞。但面对面交谈的时候,若有些言笑,气氛也还融洽。问起这几十年来跟在他身边最“情深”的东西是什么时,没想到面前一只普通水杯的“情深度”竟然超过了指挥棒,成了一位指挥家最离不开的物件。 作为一个著名指挥家,陈燮阳个人也会接到很多演出邀请,往往是接连着跑几个国家,和不同的乐队合作。无论到哪里,陈燮阳说自己都离不开这只细长水杯,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是习惯了,到哪儿都带着,就像是个跟随自己多年的朋友。而对于指挥棒,他也有自己特殊的喜好,只用得惯材质轻巧的几支,也随身带着,如今常用的那一支跟随他已有三年光景。“每到一个国家,和当地乐团合作,除了用英文交流外,就是这一支指挥棒,它是我站在舞台上所有情绪的表达。”他说。 每次出国表演结束后,如果还有休息时间,陈燮阳也会和团员们一起在当地看看,在摩洛哥的海边散心,在俄罗斯剧院瞻仰。这种旅行演出的日子,给了他工作之外闲散的短暂度假。 现在回想第一次站上舞台,背对观众的情景,陈燮阳还是记忆深刻。 “乐队指挥和其他成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必须背对观众,但对于身后观众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又要了如指掌。”陈燮阳第一次作为指挥登台还是在音乐附中念初中的时候。在那之前,他学的是钢琴和作曲,但学校老师非常敏锐地发现他具有作为乐队指挥的统领气质和熟悉各种乐器的长处。后来,陈燮阳自己编写了一组交响乐,交给班里的同学组成乐队演奏,自己就做了这个乐队的指挥,开始将背部对向观众,双臂张开,面朝演奏者。 “当时的感觉很兴奋,整个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紧张又完全随性的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再一次面对观众时,如潮的掌声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满足感。”陈燮阳说,自己可能天生就是适合做指挥的人。只要站上舞台,灯光亮起,他就是整个乐队的领袖,一切都会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后来,即使是背对观众,陈燮阳仍然能从演奏厅的安静程度来洞悉观众的反应。“如果台下的观众在演奏过程中出现一些骚动,这很容易影响到台上整个乐队。有的时候,观众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想咳嗽一下,或者说一句话,这似乎司空见惯。可对于一场演出而言,是很伤的,这时候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情绪来感染整个乐队,让所有的演奏者能够完全集中精神于我的指挥棒。这就是做指挥家最关紧的地方。” 陈燮阳说,指挥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既要无我忘我,又要牢记自己身系整个乐队,他必须带着整个乐队走,驾驭曲谱。因为,即便台上所有演奏者都进入忘我状态,完全沉浸于音乐,多年来的条件反射仍然会让他们“听命”于一支纤细的指挥棒。所以往往在略显嘈杂的演奏厅里,他要给整个乐队的就是一个完全无他的世界,这全然靠他指挥的感染力。 和陈燮阳合作过的演奏家、音乐家很多,大家都知道在排练过程中,他从来不会发火。即使作为交响乐团团长,在日常排练中,他也绝少会对团员发脾气。 “有的指挥家会骂演奏者,尤其在某段总是排练不好的时候,老出错。但我不这样,因为谁不会出错呢,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演奏正确了就行。你急,其实他比你更急,因为整个乐队都等着休息吃饭呢!”这时候的陈燮阳又有了长者慈善的宽容。25年前,当他第一次走进上海交响乐团的大门时,身份已经是这家远东第一的百年乐团的团长,从那时起,他便将此视为自己的家。现在团里比陈燮阳年龄大的团员也有,对于他们,陈燮阳始终视如长辈,而比自己晚进团的团员则都是他的孩子。这二十多年来,在团里待的时间远要比在家里多。 这些年,陈燮阳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假期。每到周末,若是有空,他和爱人都会开车去位于莘庄的别墅。在院子里,陈燮阳种了很多花,每当花开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繁花锦簇,他说自己心里会有满足的欣慰,是忙碌过后的恬淡。而唯一愧对爱人的,是陪她的时间太少。 偶尔,陈燮阳还会约上一些朋友在市中心住所附近的咖啡馆或者酒吧一起聊会儿天,聊音乐也谈人生。音乐已经占去他大部分的人生,这辈子和音乐是脱不了干系了。 在不熟悉的人看来,陈燮阳有些冷漠,说话也比较露骨且苛刻,但他说自己还算是个随和的人,只是不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把自己完全打开了给别人看。说起自己的名字,“燮理阴阳,是中国古语里面阴阳调和、百事顺畅的意思,念起来也挺威风。”陈燮阳说小时候经常会有老师叫不出“燮”这个字,反倒让更多的老师记住了这个外表看来性格有些怪怪的孩子。 最后,陈燮阳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走回排练厅。在一楼楼梯口,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海报,里面的陈燮阳正横握着一支指挥棒笑对镜头。他说这几年团里的运作经费有近三分之一需要靠演出来筹集,因此作为一团之长要当好这个家,还真不容易。 当推开排练厅大门的时候,里面独坐着一位拉大提琴的演奏者,抬起头来看到陈燮阳,叫了一声:“陈老师。” “你刚才有个音拉错了。”陈燮阳露出宽蔼的笑容,走过去,站上指挥台,翻开乐谱。用手一边比画一边哼唱,即使演奏席上的其他座位空空如也。 上海交响乐团在湖南路105号的大院子里,甬道两旁布满乔木群,越走向深处越是平坦的安静,偶尔从排练厅里传来断续的大提琴声,显得更为幽谧。下个月,上海交响乐团就要赴台演出,因此这些天,平均每天5小时的排练时间对每个参演团员而言是逃不掉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陈燮阳。 从排练厅下来的时候,陈燮阳已经满头大汗,顺势朝团长室的皮椅上一靠,倦态显然。接着,他开始修改一张节目单。他脱下眼镜,凑近了节目单仔细看,一笔一画地勾勒,格外谨慎,圈画到自己熟悉的曲目,还不自觉地哼出声来,像个刚进音乐学院的孩子。节目单搞定后,他顺手从面前桌子上拿起一只不锈钢细长水杯,倒了些水,边喝边说:“它跟着我快要跑遍全世界了。” 从外表来看,花白的头发,精瘦的骨骼,陈燮阳有些吝啬言辞。但面对面交谈的时候,若有些言笑,气氛也还融洽。问起这几十年来跟在他身边最“情深”的东西是什么时,没想到面前一只普通水杯的“情深度”竟然超过了指挥棒,成了一位指挥家最离不开的物件。 作为一个著名指挥家,陈燮阳个人也会接到很多演出邀请,往往是接连着跑几个国家,和不同的乐队合作。无论到哪里,陈燮阳说自己都离不开这只细长水杯,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是习惯了,到哪儿都带着,就像是个跟随自己多年的朋友。而对于指挥棒,他也有自己特殊的喜好,只用得惯材质轻巧的几支,也随身带着,如今常用的那一支跟随他已有三年光景。“每到一个国家,和当地乐团合作,除了用英文交流外,就是这一支指挥棒,它是我站在舞台上所有情绪的表达。”他说。 每次出国表演结束后,如果还有休息时间,陈燮阳也会和团员们一起在当地看看,在摩洛哥的海边散心,在俄罗斯剧院瞻仰。这种旅行演出的日子,给了他工作之外闲散的短暂度假。 现在回想第一次站上舞台,背对观众的情景,陈燮阳还是记忆深刻。 “乐队指挥和其他成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必须背对观众,但对于身后观众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又要了如指掌。”陈燮阳第一次作为指挥登台还是在音乐附中念初中的时候。在那之前,他学的是钢琴和作曲,但学校老师非常敏锐地发现他具有作为乐队指挥的统领气质和熟悉各种乐器的长处。后来,陈燮阳自己编写了一组交响乐,交给班里的同学组成乐队演奏,自己就做了这个乐队的指挥,开始将背部对向观众,双臂张开,面朝演奏者。 “当时的感觉很兴奋,整个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紧张又完全随性的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再一次面对观众时,如潮的掌声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满足感。”陈燮阳说,自己可能天生就是适合做指挥的人。只要站上舞台,灯光亮起,他就是整个乐队的领袖,一切都会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后来,即使是背对观众,陈燮阳仍然能从演奏厅的安静程度来洞悉观众的反应。“如果台下的观众在演奏过程中出现一些骚动,这很容易影响到台上整个乐队。有的时候,观众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想咳嗽一下,或者说一句话,这似乎司空见惯。可对于一场演出而言,是很伤的,这时候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情绪来感染整个乐队,让所有的演奏者能够完全集中精神于我的指挥棒。这就是做指挥家最关紧的地方。” 陈燮阳说,指挥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既要无我忘我,又要牢记自己身系整个乐队,他必须带着整个乐队走,驾驭曲谱。因为,即便台上所有演奏者都进入忘我状态,完全沉浸于音乐,多年来的条件反射仍然会让他们“听命”于一支纤细的指挥棒。所以往往在略显嘈杂的演奏厅里,他要给整个乐队的就是一个完全无他的世界,这全然靠他指挥的感染力。 和陈燮阳合作过的演奏家、音乐家很多,大家都知道在排练过程中,他从来不会发火。即使作为交响乐团团长,在日常排练中,他也绝少会对团员发脾气。 “有的指挥家会骂演奏者,尤其在某段总是排练不好的时候,老出错。但我不这样,因为谁不会出错呢,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演奏正确了就行。你急,其实他比你更急,因为整个乐队都等着休息吃饭呢!”这时候的陈燮阳又有了长者慈善的宽容。25年前,当他第一次走进上海交响乐团的大门时,身份已经是这家远东第一的百年乐团的团长,从那时起,他便将此视为自己的家。现在团里比陈燮阳年龄大的团员也有,对于他们,陈燮阳始终视如长辈,而比自己晚进团的团员则都是他的孩子。这二十多年来,在团里待的时间远要比在家里多。 这些年,陈燮阳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假期。每到周末,若是有空,他和爱人都会开车去位于莘庄的别墅。在院子里,陈燮阳种了很多花,每当花开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繁花锦簇,他说自己心里会有满足的欣慰,是忙碌过后的恬淡。而唯一愧对爱人的,是陪她的时间太少。 偶尔,陈燮阳还会约上一些朋友在市中心住所附近的咖啡馆或者酒吧一起聊会儿天,聊音乐也谈人生。音乐已经占去他大部分的人生,这辈子和音乐是脱不了干系了。 在不熟悉的人看来,陈燮阳有些冷漠,说话也比较露骨且苛刻,但他说自己还算是个随和的人,只是不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把自己完全打开了给别人看。说起自己的名字,“燮理阴阳,是中国古语里面阴阳调和、百事顺畅的意思,念起来也挺威风。”陈燮阳说小时候经常会有老师叫不出“燮”这个字,反倒让更多的老师记住了这个外表看来性格有些怪怪的孩子。 最后,陈燮阳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走回排练厅。在一楼楼梯口,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海报,里面的陈燮阳正横握着一支指挥棒笑对镜头。他说这几年团里的运作经费有近三分之一需要靠演出来筹集,因此作为一团之长要当好这个家,还真不容易。 当推开排练厅大门的时候,里面独坐着一位拉大提琴的演奏者,抬起头来看到陈燮阳,叫了一声:“陈老师。” “你刚才有个音拉错了。”陈燮阳露出宽蔼的笑容,走过去,站上指挥台,翻开乐谱。用手一边比画一边哼唱,即使演奏席上的其他座位空空如也。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财富人物 > 《全球财经观察》2004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