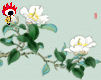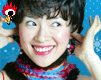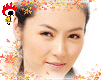| 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4月17日 17:14 经济观察报 | ||||||||||
|
吴晓波/文 无论企业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1930年,当传教士之子亨利·卢斯创办《财富》的时候,他便隐约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生阶层的辩护士。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他所代言的阶层“到底有什么含义”,有一天,
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特征,因此他是一个全神贯注于物质财富的人。a,俗气的;通常保守的;死板的;b,口语,普通的,粗野的和愚蠢的;c,资本家的。 “怎么能这样?我在失望之中,像一个在学者面前受伤的孩子似地冲了出去。”卢斯在一篇演讲中这样愤愤不平地叫嚷道。事实似乎正如创作《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的戴维·西尔弗所言,“直到20世纪40年代,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作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 但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T型车的车轮碾碎了贵族们脆弱的尊严”,企业家以他们骇然的敛聚财富的速度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而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一个强势阶层,他们开始被一层层地涂上“国家英雄”的金身。哲学家A.N.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论证:“伟大的社会是企业家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而卢斯发表于1954的《商人的品质》一文,更是表达出强烈的使命感,被视为财富阶层的一次宣言。卢斯写道:“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商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会服务者。” “商人必须对他们所想要的这种社会、这种制度有明确的自信,并且他们必须站出来为维护这些自信而战。” 公众对企业家期望值的提高,还与他们对政客的失望成正比。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发达,任何政治活动都以空前的透明呈现在公众眼前,那份斡旋于“政治纱帐”之内的神秘感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人们开始厌倦政客们的喋喋不休和出尔反尔,特别是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曝光,政治家的人格信用降到了最低,呼吁成功的企业家来掌控国家的声音一度竞成主流。这股“企业家崇拜”的热浪,到李·艾柯卡身上终于达到了巅峰。 1964年,艾柯卡主持开发出一款名为“野马”的车型,一时风靡全球,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轿车,他因而爬上福特汽车总经理的宝座,并当上了《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 1978年,艾柯卡的光芒终于让老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了刺眼,他被一脚踢出福特公司,理由是他“缺乏礼貌”,太具“侵略性”。这时候,已经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留了这位54岁的落魄人。憋了一口气的艾柯卡果然没有让新老板失望,他很快开发出一款K型车。K型车是如此的成功,仅仅用了四年时间,艾柯卡就把克莱斯勒从破产的边缘拯救起来,一举成为在美国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三大汽车公司。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创业神话。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在首都华盛顿,人们纷纷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好莱坞的明星里根可以当两任总统,那么,担任过两大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艾柯卡为什么不可以当总统?在热心团体的拥簇下,艾柯卡放下公司工作,开始四处演讲拉票,“我必须承担起伟大的使命,是轮到企业家来领导这个国家的时候了。”他大声疾呼,台下溅起轰天的掌声。 因为党派政治的因素——尽管有不少民众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之一的民主党从来就没有把他列入候选人的名单,艾柯卡最终没有去正式参选美国总统。可是,这却极大地激发出他参与公众事业的热情。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柯卡的个人价值和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却在他任期的后半段急落了31%。因写作《基业常青》而出名的吉姆·柯林斯如此描述这位商业奇才的后期职业生涯——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退休年限,以至于克莱斯勒的内部人士开始嘲讽他“想一辈子担任克莱斯勒的老总”。当他最终退休时,仍要求公司继续为其提供飞机和股权。后来,他甚至同著名的收购艺术家Kiek Kerkorian联手发动了针对克莱斯勒的敌意收购案,弄得天怨人怒,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在吉姆·柯林斯最近发表的《第五级领导者》一文中,艾柯卡成了“卓有才华但利己主义超级膨胀的第四级领导者”的典范。 “艾柯卡崇拜”的峰回路转,生动地呈现出了企业家的职业特征:它有如此现实的绩效标准,任何偏离了这个价值的行为——无论它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的真相 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 任何观念的成熟和清晰,从来都不是直线的,它充满了反复、曲折甚至偶然性。对企业家使命的认识,便也如是。F.A.哈耶克在他的研究中,一再地为商人的趋利性进行了辩护,他把那种“鄙视利润的人”称为是无知的禁欲主义者,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里,他断言,“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认识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哈耶克同时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商人工作的关键,他们其实已无暇顾及其余,“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那么,在趋利性的前提下,企业家是否还存在“适当”的公共使命?彼得·杜拉克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是他让企业使命真正回到了企业本身。 杜拉克认为,在剧变的时代中,企业家最主要的责任,是为机构创造不相同的明天。具体言之,企业所要界定的使命,即应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杜拉克一再强调,企业所要达成的使命,一定要落在企业以外的社会中,而其最主要的是“创造顾客”。 这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管理学意义上的使命界定。它剔除了所有不现实的、虚幻及被夸大的“使命激素”,而让企业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职业的层面。 近年以来,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等华尔街金融丑闻的相继败露,使人们看清,无比诱人的成长蓝图很可能只是金钱游戏的借口,信誓旦旦的承诺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圈钱阴谋,企业家的道德水准遭遇空前的质疑。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曾经被夸大过的企业家及公司使命感进行了反思。2003年1月,严谨的《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两面派:企业公民的真相》的文章中详细地描述过这一转变——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上世纪90年代企业界最流行的名词之一,如今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发布年报时都隆而重之地介绍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善行。CSR本身也形成了一个行业,拥有全职职员、网站、时事通讯、专业协会以及庞大的顾问队伍。富时和道琼斯也推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这是好现象吗?也许不。从伦理角度看,CSR有着明显的硬伤:花别人的钱做善事。企业经理人只是受托管理股东们的资产,把原本应该支付给股东的钱拿去做好事,其实很值得商榷。而且,社会政策的扶持方向应该由经理或非政府组织来决定吗?在民主社会,那是选民和当选政客的责任……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 事实上,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困扰也依然存在,“社会使命感”尽管光芒万丈却与企业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形成矛盾,这让他们陷入不可能的取舍。在2003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哈佛大学的企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发表了题为“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的长篇论文,他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一棘手的命题进行了梳理。波特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以为,“企业从事公共事业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而实质上,则应该集中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 也就是说,波特一把剥去了那层很容易被当作借口而且虚幻得让人沉重的“公司使命”外衣,而从竞争的角度来为企业的公共活动重新定位。企业可以利用慈善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而只有在企业的支出能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企业的公共活动和股东的利益才可能交汇在一起。进而,波特甚至还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让企业家可以找到能同时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既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又能提高其所在组群竞争力的慈善活动领域。” 理念的梳理,至此应该已经清晰,关于企业使命,我们似乎可以有以下的认识: 一,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企业应当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和使命 二,企业的公共使命的体现,归根到底,应当服务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三,那种脱离了企业现实利益的公共使命,要么是盲目的、紊乱的、缺乏可持续性的,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 企业使命:从玫瑰色到深蓝色 玫瑰色与深蓝色的取舍很显然,对利益的直接追求和公司存在的现实考量,远远超出了公司对于抽象价值及公共责任的热衷 当我们以思想史的方式对企业及企业家的公众使命进行了梳理之后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看看在企业内部它又是怎么衍变的。 对于任何公司经营者来说,有两个问题属于“始命题”:一个是“公司是什么”彼得·杜拉克要求每一位CEO在上任前必须先思考清楚这个问题,一个是“公司为什么”而企业使命则与后者有关。在管理学上,“企业使命”是一个专用名词它是一个公司对长期持久目标的设计和界定,是“要去完成的任务”,将反映出这个组织的价值观、长期宗旨和优越性。当我们将一些国际著名公司的公司使命一一罗列出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便会陡然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这是一家饮料公司的公司使命陈述:“我们致力于长期为公司的股东创造价值,不断改变世界We refresh the world。通过生产高质量的饮料为公司、产品包装伙伴以及客户创造价值,进而实现我们的目标。” 是的这个声音来自于神奇而不可一世的可口可乐公司因为除了它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家饮料厂敢于用一瓶加汽饮料去“不断改变世界”。从60多年前盟军攻克柏林,到不久前美军占领伊拉克,世界看到的第一批照片中肯定有一张当地居民——而且大多数是儿童欢乐地饮用可口可乐的图片。还有消息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伊拉克的商业项目就是“筹建一个可口可乐罐装厂”。 可是如果你认为可口可乐式的公司使命是一个仅有的个案那你又错了。当我们注目于那些诞生于19世纪末或上世纪初的美国百年大公司的身上时,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发现同样的气质:它们均有着亨利·卢斯式的改造世界和称雄全球的志向,从它们至今还在沿用的公司使命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出一个崛起中的商业帝国主义的远大抱负: AT&T:我们立志成为全球最受推崇和最具价值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丰富顾客的生活,通过提供新鲜有效的通信服务帮助顾客在商业上取得更大成功,并同时提升股东价值; 时代华纳(Time Warner):我们力求成为最受尊敬和最为成功的媒体公司——在我们的经营范围内成为领导者;以优质、卓著闻名于世。我们成功的灵魂在于聚集最优秀的人才,包括世界上最好的记者和作家,并使大家创造性地思考和工作;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创建于1850年):成为全球最受人尊敬的服务品牌; 通用汽车(GM):成为客户满意的行业领先者; 通用公共事业(GPU):为人们提供满足今天需要和实现明天梦想所需要的能源; 强生沃克斯(Johnson Wax创建于1886年):我们将成为这个自由经济市场中负责任的领导者; 考夫曼(Kaufman创建于18世纪中期,美国西部最大的住宅建造商):我们要为人们建造梦想之家。 价值观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引领者,现代生活的创造者,这些玫瑰色的梦想词汇散落在这些百年公司的成长历程上见证了一代企业家的自我期许。 当我们的目光从这些百年公司移开,转到那些在近30年里诞生的、新兴的、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公司身上的时候,情况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遥远的抱负不见了,工程师式的专业声音响起,世界从细节开始被改变,玫瑰色被更为理性的深蓝色替代。 微软公司创办之初,比尔·盖茨曾用一句话来陈述这家并不被看好的公司的使命:让每张桌面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台电脑。 日后,在回答记者时,盖茨说:“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一使命,自1975年公司创立以来始终持续关注于此。这个使命已经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得全世界人都改变了做生意的方式。这个使命也在塑造着未来。” 2000年前后,微软公司重新也是更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公司使命:在微软,我们的使命是创造优秀的软件,不仅使人们的工作更有效益,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更有乐趣。 这无疑是一个更为精准的使命陈述,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这些信息:微软只做软件,是一家“不制造计算机的计算机公司”;微软是一家服务主导型公司;微软认为“乐趣”与“效益”一样会给企业带来商业机会。 跟可口可乐并非惟一一样,微软的使命感也可以在与它同时代的公司身上得到呼应—— 朗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世界最优质、最新的通讯设备、产品、技术和客户服务。以优秀的人才和技术为依托,我们将成为以客户为主导的高素质企业,并为股东提供稳定的高额回报; 苹果:致力于为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学生、教育工作者、设计人员、科学家、工程师、商务人士和消费者提供最先进的个人计算机产品和支持; SUN:成为最好的通信技术服务提供者,使员工得到最好的专业经验,使股东得到良好的投资回报,受到社会和大众的认可; LSI(美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公司):凭借我们在半导体设备方面所具有的迅速设计和批量生产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百视达(Blockbuster):成为全球领先的可租借娱乐器材公司提供卓越的服务、优质的选择、便利的条件和理想的价值 保德(Baldor):成为设计、生产、销售电动发动机和驱动器的最优秀企业。 很显然,这都是一些十分清晰的阐述,是一种“专业化的公司使命”。今天进入全美300强的公司中——特别是那些新兴的、居于中坚力量的大公司,其公司使命的表述往往非常专业和简洁它有着明确的边界感而很少掺杂不可捉摸的、容易被夸大的要素。 杰弗瑞·亚伯拉罕是一位非常有心的美国学者,他举数年之力,先后向全美1600家顶级公司进行了征询,名单中包括《财富》1000强、《福布斯》500强以及“全美百家最佳公司”到2003年为止他共收到了875家公司的回复其中375家公司有自己清晰的使命陈述。 在此基础上,亚伯拉罕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其中一项有趣的工作是,他将300多个公司使命中出现的热门词汇进行了统计,共列出69个关键词,结果出现最多和最少的10个关键词分别如下: 这是一组十分耐人寻味的“关键对比”,是玫瑰色与深蓝色的取舍很显然,对利益的直接追求和公司续存的现实考量,远远超出了公司对于抽象价值及公共责任的热衷。 可以说:从可口可乐式到微软,从“抱负化的使命”向“专业化的使命”衍变,是美国过去一百年公司使命衍变的轨迹。 中国企业的使命错位 中国企业必须在使命认识中从玫瑰色走向深蓝色重新回到“基本面” 历史往往是如此相似。今日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商业至上的奢华年代从这里迸射出的炙热的商业热情,常常让人想起20世纪初期的美国,那个亨利·卢斯大声颂唱的财富创世纪那个对商业顶礼膜拜深信技术的进步将洗去一切贫困、不平和忧伤的大年代。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如果拿美国百年商业史作为参照体一个让人不无尴尬的事实似乎是我们今天对企业家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司使命的认识正停留在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之间。 为了写作本文,我和我的助手们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收集中国企业的公司使命。结果我们发现,很多大公司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使命陈述,它往往与公司的宗旨、远景、战略目标及成长理念等等交结在一起。然而经过细致的剥离我们仍能清晰地梳理出这些公司在使命认识上的一些共同之处: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往往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纠缠在一起,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式的崇高感,仿佛公司就是为了完成某一项遥远的社会使命或实现某一个“国家目标”——如成为中国第一个跨国品牌——而存在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十字架”型的使命。 另外,我们还每每看到“借口型”或“口号型”的公司使命,它常常是为了“捍卫或振兴民族工业”(迄今很多中国家电企业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为了“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山东某集团的公司使命),为了“让国人寿命延长10年”(沈阳某保健品公司的公司使命),或为了探索某一些体制上的创新(它常常出现在那些率先闯入垄断型行业的新兴公司的使命陈述中),这些堂皇或遥不可及的使命感似乎能够让企业在经营行为中天然地带上某种光环甚至成为获取某些利益的最好理由。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往往是不聚焦的,很难体现专业化的执着,从使命表述中,你基本上搞不清楚它到底专注于哪一个领域,它在哪一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期望在哪一部分成为该行业甚至全球的领先者。这应该与当今国内企业普遍执行多元化的战略有关,在这一点上,中美大公司的差异性非常之大。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还往往与股东无关,在价值取向上十分模糊,从中我们基本看不到公司对其出资方所应当作出的承诺。这种对“有限公众利益”的漠视与它常常表现出来的对国家乃至民族利益的高调宣示形成了一种十分刺眼的对照。 这些年,当我在从事中国企业成长史研究的时候,我经常会自问一个问题:中国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究竟有多远﹖差距是规模上的、技术上的、资本上的,还是战略能力上的﹖或许都有。或许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将一一超越。 但是,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迄今还没有意识到差距,那就是对企业的使命认识。 当我们还陶醉在“The Glory and The Dream”(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幻象中时,我们的强大竞争对手已经奔跑在另一个专业化的世纪跑道上。 我们必须认识,在当今竞争激烈和日趋全球化的商业世界中,公司日渐成为一个纯粹的、追求“有限责任下之有限利益”的商业组织,企业在社会进步秩序中的角色扮演日益单纯,它对道德进步和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化,让公司去承担过多的公共责任,对企业家和社会而言,都是冒险的。如今广受推崇的商业偶像从GE的杰克·韦尔奇、IBM的郭士纳到2004年红极一时的日产汽车CEO卡洛斯·戈恩,与当年的亨利·福特、J·摩根,甚至稍近的李·艾柯卡等相比都要离公共利益和政治话语远得多。 任何使命的实现都是需要成本的,不真实的、被夸大的使命感正在消耗着我们并不积厚的能量和资源,进而让我们在战略设计上往往容易多绕弯路,甚至陷入自掘的陷阱。 这样的声音是必要的:走出卢斯式的激情和艾柯卡式的崇拜,中国企业必须在使命认识中从玫瑰色走向深蓝色,重新回到“基本面”。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营管理 > 正文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