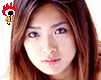唐士其:法治究竟是什么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9日 17:03 《商务周刊》杂志 | ||||||||
|
唐士其 如今,唐士其教授略显凝重的脸庞上时常挂着微笑,但这与20年前那个初登北大的懵懂少年已经截然不同了——那时候,他被同学们戏称为只以读书为乐的怪物,在他并不宽的床位上,有且只有一个刚好能容下他瘦小身躯的空间,其余全部被浩瀚的书海所占据,不过,这却为他日后争取到了东京大学博士后的席位,并获得了在弗朗西斯·福山北大演讲会上
我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读书做学问是觉得“好玩”,或者说,我希望把我所关心的问题搞清楚,然后从中获得快乐。而前者做学问的目的则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影响政治。 另外,我也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花费在思考上的时间远远大于写作的时间,知名度和“著作等身”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依我个人之见,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知识的真理,而不是追求著作数量的多寡。在将一个问题搞清楚之前就匆匆发表看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知识分子首先应该丰富自己的知识,掌握发言权和话语权,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但是,我也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毕竟,社会总需要有人来关注公众的利益,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社会解释的职责。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解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著书立作。人们喜欢看你的书,社会认可你的思想,那就意味着你自然而然地在影响人的认识和社会的进程;另一种则是直接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就像马克思那样,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构建法治体系。毕竟,法的本意应该是约束国家和政府的,而不是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倘若法律能够在程序上保证公众“上诉”政府的通道,那么就能最大限度的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乱来。但是,我不主张把做学问和社会活动混在一起,否则研究就会溶入太多的主观因素,并很可能导致对真理追求的偏离。换句话说,学术和社会活动完全是两回事,二者应该保有必要的距离。 我自己更喜欢前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读书做学问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职责,我的眼睛时刻在关注着中国,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我希望能较好地将两者分清罢了。 因此,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更多的时间,这可以让我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做最充分的思考。而眼下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花时间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现在仍然很模糊。比如,相对“人治社会”而言,到底怎样一个社会才能叫做“法治社会”呢?倘若一个社会是在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而立法机构又是由部分人构建的,那么这个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算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不能由人来立法,那么谁将承担立法的责任呢? 西欧曾经有大约一千年的历史表明,当时的社会没有立法权的概念,因为人们认为法律不应该由人来制定,而应由神来制定,或者是由传统、习俗等积累而成,如果遇到现有习俗法不能判定的地方,才由法官来做司法解释。与此同时,公众有权对法官的解释进行上诉,以此规避法官的个人主观性,确保公众在法律程序上有一条约束政府的通道。久而久之,就在法官的司法解释和人民的上诉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法律,填补了“神”留下来的内容空缺,一个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也就随之形成了。可见,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关键在于立法主体和司法程序的公正。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发展,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也就是统治者设立的机构,以及“人治”的法律。此时的人们,就好像关在笼子里动物一样被钳制住了,“上诉之路”也被渐渐堵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人是活在铁笼子里的。” 因此,在当今世界,美国、英国等所谓的“法治社会”较历史而言也都是相对的。“法治社会”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也取决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外壳能否为公众提供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甚至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所以美国人常说“上帝在保佑美国”,的确也有几分道理。至于中国,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为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而努力,不管他采取那种社会解释方式。但是,考虑到未来不确定的偶然因素,一个法治社会究竟何时才能实现,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做出解释。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商务周刊百期纪念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