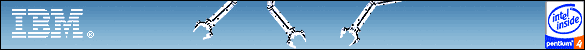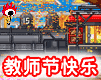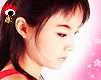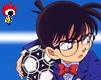| 林毅夫:一个经济智囊的自助、他助和天助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7日 14:32 南风窗 | ||||||||||
|
章敬平 2004年8月17日晚6时许,52岁的林毅夫随着“中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营员们期待的目光,以他一贯的优雅姿态,双手有节奏地摆进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除了着装上的随意庄重之别,林的“课堂姿态”和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朝堂姿态”,并无二致。
过去十数年里,有官方经济智囊称谓的林,出任过4届全国政协委员。 掌声响起来。40多名来自中国各个大学的营员用大学生们独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林的拥戴。营员中鲜有人知晓,10年前,万众楼所在的朗润园一片荒芜。彼时,这个昔日乾隆皇帝第十七子的府邸,这个道光末年被转赐于恭亲王的皇家园林,里面杂乱地住宿着近50户北大的、甚至是燕京大学时代留下来的职工家庭。除了门口两个雄伟的石狮子,朗润园闻不到一丝书香,看不到一点旺盛的迹象,无情的战火和历史的风霜,早将往日王府的繁华淘汰尽净。 反观今日修复一新的朗润园,古朴而有十足帝王气,已然北京大学最有园林特质的经典建筑。悬在湖心岛上莲莲荷叶畔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牌匾,业已简化成CCER,沉淀在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官员的心目中。10年来,从筚路蓝缕间一路走来的这座四进园林,已是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一个非官方的经济决策机构。它不仅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绍介到中国,确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准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成为中国领导人信任的一个智库。身为CCER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从台湾泅水到大陆的林本人,也在10年的磨练中成为海外瞩目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智囊。 CCER是北京大学一个体制创新的研究机构,观察人士对它所显示的勃勃生机的不解,就像台湾岛人不理解林当年为什么来到中国大陆一样。 回望CCER10年和林的惊人的个人成就,林以为所有这一切,皆来自自助、他助和天助。 自助:勤奋,责任感,以及品格 讲演、集体答问、个别释疑、合影,原定2个小时的讲座延长到将近5个小时,林以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事无巨细地满足了学生们的所有要求。在一个本科生很少见到教授的年代,学生们感动不已。 林说,他只是在尽一个教员的本分,他没想过要做教育家,如果有幸成为经济学教育中的大家,那最多是个副产品,就像他成为官方智囊一样。教育家、经济学家、官方智囊、社会活动家、名士—在民间人士和传媒随意授予的头衔中,他最喜欢的是经济学家。 2002年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林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诚信问题记者招待会。是次招待会上,林赢得了经济记者们对于一个本土经济学大师的普遍赞誉。 招待会开始后大约半个小时,在座的政协委员中,有人已被记者提问了好几遍,唯有林无人问津。终于,一个女记者打破了林被动的沉默。他笑意盈盈地听完了她的4个问题,说:感谢你的提问,让我不再担心我会像是一篮摆在讲台前的鲜花。嗣后,作为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第一个在美国攻取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的经济学家,他以西方式的优雅和礼貌,向所有到场的女记者表达了节日的祝福。记者们注意到,林回答4个问题的前后顺序是三二四一,该记者所提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顿显清晰明了。 学界认为,林之所以占据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可能在于他总是把握内部逻辑的一致,以及逻辑推论和经验事实的一致。 林说,他将经济学家和职业乃至理联接在一起,已有25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在他的人生中,原来是一个极大的偶然。很难想象,若无坚毅的“自助”之心,偶然怎么会成为必然。 1979年夏天,军衔上尉的台军连长林毅夫,从金门游过那一弯浅浅的水来到大陆。在他登岸的福建,林被当作宾客参观游览了两个月。而后,他向大陆官方提出工作的请求。要谋职就得知晓大陆社会,要明了大陆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几经辗转,北京大学接受了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他开始研习政治经济学。林与经济学的偶然因缘肇始于此。 这一年,他27岁。现今,向他讨教的很多学生在这个年龄差不多拿到了博士学位。 3年后,林深造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师从于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今天的人们除了“机缘巧合”,可能找不出更为恰当的词句,来描述林是怎么与经济学大师亲密接触的。彼时,舒氏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林的优雅姿态和同样优雅的英语口语,使得他成为翻译的绝佳人选。据称,讲演完毕,舒氏对林表现出溢于言表的欣赏,并以极大的诚意邀请他去美国读书。于是,林未经申请即幸运地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进入全球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方阵,像临摹大师画作的习画者,悉心揣摩诸多经济学大师的治学方法。让关心他的人觉得欣慰的是,借助去美国读书的“东风”,他在异国他乡和分散3年的妻儿团聚了。 又4年,舒氏为他戴上了博士帽。接着,林去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耶鲁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 据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林用4年的时间,拿到了一般学生需5至7年方可拿到的博士学位,且是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迄今,林是1970年代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 观照自己的成就,林并不认为他真的具有出席政协记者招待会的人们眼中的“天分”。他说,他去美国时年届而立,由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美国的巨大差距,他在芝大遭遇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困厄。如果不是一个“毅夫”,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切都不可能。他的成就完全得益于超人的努力,而非其他。尽管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需要治学者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刻体悟,但悟性替代不了勤奋。 与其相信林的天才,不如相信他的努力。林给他的学生的一个座右铭是“成功等于机遇加上努力,而机遇属于平常就做好准备的人”,他在跟学生聊天时,曾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CCER不像北京大学体制内的其他院系,为了CCER的发展,为了给“海龟”们一张宁静的书桌,林不得不扮演一个四处化缘者的角色,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为CCER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林并未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从CCER的网站上可以看出林一个人每年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的数量经常是CCER其他同事的数倍。被问及“林是否像传说的那样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忙于经济学论文的写作”?跟随他数年的秘书陈曦说:这样的问题已接近真实的林毅夫了。 今天春天,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张奇志在CCER攻读《财经》奖学金。他说,在波兰前总理来CCER的那一天,林上了一整天的课,接待这位欧洲前政要前,林在办公室草草吃了一个盒饭,然后主持晚上波兰前总理的讲演。次日,林接着讲演和上课。张感叹林的体力非常人可比,他作为学生在台下听课都受不了,而林却总能精力充沛,有条不紊。 林自以为,身为知识分子,他穷其一生而不停歇的动力,离不开担当社会责任的儒家情怀。1987年,林学成回国。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侯,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回国的则少之又少。问林为什么会成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谈到两点理由: 首先是立志做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看好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经济学的实验场。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和未来。 事实上,他为什么回国,和他25年前为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他曾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过,作为昔日台湾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内地的思想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直接的动机并非台湾岛上猜测的那样,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 根据林的自述,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少年时代阅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屈辱史,便开始思考讨论如何使中国富强的话题。这也是1960年代后部分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的话题。发生在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诸多事件之后的历史,促使林意识到中国强盛的希望在大陆。 一个“自助”的人,不但勤奋,对国家有责任感,还应当有独立的人格。林待人接物,无论达官贵人,还是一般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分寸。《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出身军旅,曾是文学青年,不但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更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林仍然和高有着很好的友谊,对高身上诸多可贵的品质表示钦慕。高筹办《经济学消息报》时,财务困窘,林不仅投资了他的报纸,还为这份报纸积极撰稿。 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CCER副主任李玲称,林的品格,与他的胸怀和人生历练息息相关。林的血脉中流淌的是“六经”的要义,他在台湾省宜兰县读的小学,诵读的国文中大多蕴藏着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忠于国家,孝于父母,义于友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在他读中小学的1960年代,中国大陆正处于传统文化被革命被当作四旧横扫的年月。或源于此,有人牵强地解释为什么同年代的经济学人中,林是少数没有遭际道德攻击的人之一。 林经常出入于庙堂之上,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智囊之一,他身边总少不了达官贵人的身影,他们给予CCER的帮助也可谓善莫大焉。林让人钦佩的是,他没有像坊间传言的些许经济学人那样,以“客卿”或者“幕僚”自傲,而始终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他助:君子不同而和 2004年8月19日,林在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对我说,不能将CCER的集体成就悉数归功于他一人,即便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就,他也不认为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林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绝不是一个人的事。他之所以有今天,仰赖的不仅是“自助”,更有“他助”。 林说到人生难以承受感谢之重,一口气从家人,老师说到朋友和同事们。 今天暑假的“中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就是他大哥林旺松资助的。说到家人的助益,他还提到了自己的二哥和姐姐。据称,他在台湾的亲属资助他的非但是金钱,还有精神。2002年5月,林父辞世,台湾方面考虑到他“叛逃”的历史,声称不放弃对他的追诉,以至林不能赴台奔丧,尽为人子者的最后孝道。林心灵深处的痛楚一般人难以得知,关注他的人们只能从他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时滚滚的眼泪,推测他的苦痛。是他的家人在他最为痛苦的时刻给他以精神支持,对他不能返乡奔丧表示谅解。 25年来,林一直对北京大学心存感念。在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文革的遗毒还到处弥漫的时候,正是这个中国第一高校接受了他,给了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继续深造的机会。倘若没有前校长吴树青以难得的担当,乾坤独断地给以支持和勉励,在1990年代初叶的中国大学探索一个体制创新的CCER,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外部世界的有利,固然举足轻重,若无内部人士共襄义举的志同道合,是成不了大事的。林很感谢周其仁、易纲、海闻、张维迎等人,他声称,CCER是共同智慧共同努力的共同产物。CCER是一盘棋,他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局”的,得要好几个“眼”方可。CCER草创之初,只拥有北京大学地学楼里两间半格子式的办公室,从海外归来的博士们,没有将条件的艰涩归咎于他,却在功成名就时,让他以主任的名义独享了不知情者给予CCER的集体荣誉。 领导者和集体成就之间的道理人人都懂,人们诧异的是,林用什么样的力量将个性差异殊大、治学方法各异的经济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做到不同而和的? 接近林毅夫的人们没有直接回答“不同而和”的秘密,而是间接地叙述他是怎么做到“和而不同”的。 林予人的印象,多是蔼蔼君子之风,待人接物以谦和为主。可他在学术上却始终坚持君子和而不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和故交杨小凯教授的论争。 2004年7月8日,林在始终充溢着他的微笑的朗润园内泪流满面,追悼英年早逝的“论敌”杨小凯。杨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供职于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两年前杨于北京的一次演说中,以一个华人经济学家的学术和社会使命感,提醒中国注意其后发劣势。杨认为,西方经济学家沃森“对后来者的诅咒”的概念,或可在中国发生。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先从技术模仿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倾向,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会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而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种下祸根,因此,具有后发劣势。他认为最好的制度是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先完成英美的共和宪政制度的模仿,等完成了制度模仿才来进行技术模仿,这样才能避免后发劣势。 杨中学时代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被江青定为反革命分子,一生命运坎坷,身世与林一样离奇。和杨相交将近20余载的林毅夫,对杨所谓的后发劣势说提出了全面商榷,并指出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在不具备英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的条件下,在中国完成和英美同样的宪政体制。因此,林主张应该先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不适应的制度。 论争的硝烟尚未散尽,55岁的杨就被癌症夺命于异国。林哽咽着说,他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自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与杨相识时始,20年来,杨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尽管近些年,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然而,公开的学术争论,并未影响他们的友谊,尽管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所谓“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也。 林个人追求和而不同,也一样期待自己领导的组织机构,将“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视为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品格。林主张摈弃狭隘的门户之见,在CCER的历史上,迄今还没上演过党同伐异的闹剧。2002年夏天,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另一个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出乎意料地受邀于CCER。演讲的前一天晚上,住在钓鱼台附近的张,反复受到警示,肇始于CCER一博士后的挑战,他在万众楼的演讲,有可能变成一次不愉快的毁誉参半的口水战。少数人担心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一场经济学饕餮大餐,最终在友好而独立的学术氛围中谢幕。 林的品格中有感恩的一面,正如他常常念叨别人对他的好。回顾朗润园的历史,信奉君子和而不同的林说,是那些同而和,不同也和的君子们帮助了他。 天助:感谢200年来最好的时代 林笃信,个人历史是时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成长为经济学家的机缘,除了自助,他助,还有天助。所谓“天助”,指的就是这个200年来最好的时代。 结束对夏令营营员的讲演,已经是夜晚11时许。走在朗润园中,林毅夫恳切地说:就CCER而言,她升腾的火焰,是众人拾柴的结果,就个人而言,经济学家也罢,官方智囊也罢,无不是时代使然。他感谢这个时代。 林把自己52年的人生归纳成三个阶段:他多年来不肯多谈的在台湾的27年,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从爬上大陆海岸线到从美国学成归来的8年,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从一个台军上尉蝉蜕成一个经济学人;从1988年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以经济中的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分析框架的学术思想迄今,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他用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研探中国经济现象的15年,是他以独特的视角提出新的发展、转型理论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并以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囊身份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15年。 林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时代提供的素材,让他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外受人瞩目的经济学家,并为国内决策者所重视而跻身于高层智囊行列。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高频率地听取过林对经济政策的意见。除了以中共党外人士的身份,在2003年两度出席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外,他还参加过中国最近两任总理的专家问计会。“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林领衔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也为决策层所采纳。 林不愿意过多透露他为中国领导人做智囊的细节。据观察人士的梳理,他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殊大的影响。他在中国农业问题上的研究在国内相当权威,曾担任发改委“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2001年圣诞节,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新阶段三农问题座谈会,林所作《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的报告很受高层看重。此前40天,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座谈会,林出席并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汇报。 林的同事,CCER副主任李玲博士证实,林多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和建议在2004年中共中央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中颇有体现。林倡导的“新农村运动”,有望影响中国农村的未来变革。 身处百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将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时代进程的助益,理解成时代的风云际会。未来倘能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那么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得益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亦将同步提高。 当一个时代的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西方经济学大师开始频频造访中国。大师纷至沓来的时刻,林和CCER充当了他们和中国经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一个桥梁。1998 年夏天,马丁.费尔丁斯坦所率的美国经济智囊团进入朗润园,数位中国经济官员,和他们坐到了一起。马丁.费尔丁斯坦,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他和他的经济学家团队,打造了美国最大的非官方经济政策研究机构。 经由林的努力,NBER和CCER开始了交流互访。6年来,非但央行行长周小川等经济官员,数度与他们展开对话,江泽民也在国家主席任上接见了马丁.费尔丁斯坦,耐心听取了马氏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看法。 尽管林的“智囊”和“桥梁”身份为他赢得了荣誉,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更不会自大地认为自己改变了中国经济版图。他对出席“中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的营员们说,中国领导人并不总是听经济学家的。多数情况下,经济智囊们的意见只是在与领导人所思索的问题不谋而合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尊重专家,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中诺奖得主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而没有照着哈氏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政治家对经济政策的考量比经济学家的限制条件要多得多。林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现实情境的掌握,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和把握,总是对照现实条件的需要,而非其他。 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示乐观。他坚持认为,当下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好时代,不是民运人士所说最坏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8月20日,林在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大胆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有望赶上美国。预测经媒体报道后,引来网民反对声一片,有的甚至是谩骂。CCER有教授为林叫屈,觉得网民们是以臆测替代评论。其实,林说的是经济规模,而不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5亿,再大的经济规模,除以15亿,幸福指数就可想而知了。 勿论网民,即便是经济学界的臆测,林也不愿站出来回击。 据称,1990年代中后期,林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非产权中心论”。在被中央政府高度认同的同时,也遭到了部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抨击,认为他是讨好意识形态。他的身份的特殊性,确实影响到他的行为和话语。譬如,人们从未在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他在台湾的经历,他每每说到台湾地区必称“台湾省”。 对于臆测,林只是无可奈何地一笑置之。25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被人们臆测,尤其是台湾岛上。他说,他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50~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这在实际上怎么可能呢? 林援引孔子的话说,五十以学易。最近两年,常于不经意间背出一段《道德经》或者《金刚经》的林,一直在反思“术”和“道”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说,思辩“道”“术”关系,有助于他对经济学之“体”和“用”的理解,常让他在治学的途路中会心一笑。 问林50岁之后的追求,他说他的追求一以贯之:做个经济学家,左手经济政策,右手经济理论。他最大的乐趣在于徜徉于真实世界的理论创新。从终极目标上说,他希图以经济学家的方式,为造就自己的大时代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两个余月前,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在杭州答记者问时说,林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林不认为自己会获此殊荣,但他对未来一代摘取桂冠拥有信心,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操办“中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的原委所在。林对参与夏令营的营员们说,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希望他们好生努力。他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老师的劝勉,而是中国的时代走向决定的。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林毅夫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