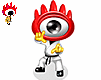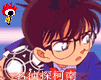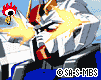| 负熵、交换与文化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2日 16:27 《互联网周刊》杂志 | ||||||||||
|
负熵、交换与文化 许多人埋怨我对网友的评论一概不予置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确实太忙,抽不出时间来一一作答;二是无从评论,有时候一些评论不谈问题,只是概括的评论,令我无从答起;三是许多评论值得注意,但我不想对人家深思熟虑的东西随口作答,想有了时间后再同样认真地回答。陈体慎先生的《负熵成不了经济学的奠基石—评点“负熵与文化—后现
陈体慎先生是一位令我非常尊重的网友。他与那种脱离问题见谁贬谁的愤青网友不同,始终非常认真地专注于问题本身是非的探讨。对我的文章,陈体慎有时全面赞同,甚至替我抱屈,有时却全面反对。这里专门找一篇全面反对的文章,进行切磋。 陈体慎先生(以下简称陈兄)逐段点评,全面批驳了我在《负熵与文化—后现代经济解释之二》中的观点。归纳起来,意见包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价值论、交换论和目的论四个方面,几乎串成了一个系统。我很感兴趣,想分别从这四个方面作答。 关于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学可以不可以将熵包括进来? 陈兄说,“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语言一旦还原为热力学语言,就会变成物理问题,一旦变成物理问题,工业时代的特点和信息时代的特点就被抹杀了。”“经济学包括不了熵和负熵的过程。经济学将熵包括进来,就像经济学把社会科学包括进来一样不合逻辑。”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把熵引入经济学,我并不是第一个“肇事者”,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是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熵这个概念虽然来自物理学,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早已不限于物理学概念的范畴,尤其是在普里高津的耗散理论提出后,熵作为系统论基本概念的地位已经超过其作为物理学概念的地位。申农的信息熵,用熵来解释信息的特点(不确定性及其消除);阿罗的信息经济学,也是用熵的概念进行经济学解释。在国际上,从巴塔耶到布瓦索,熵的思想一步一步从概念演变成为一种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在国内,张明107万字的大部头巨著《负熵与货币—经济学的重构》,第一次以熵为基石,串联起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这种体系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把熵纳入经济学范围来研究,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不仅如此,把熵纳入经济学研究,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第三次浪潮与工业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分野,就在于“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熵,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或不确定性的消除,已经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我相信它进入一般理论经济学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其次,第三次浪潮要以人为本,就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面。经济人理性,本质上是确定性的;而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却具有不确定性。我不太赞同陈兄说的“经济学研究经济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明确表明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关系”。诚然,如陈兄所说,“人的非理性现象在人类诞生那一天就有了,不是在后工业化才产生的”,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历史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样一种超越经济人理性的现象,会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突出特征。而熵的观念,正好引导了一条通向人的体验的路径。我注意到,陈兄以前关于幸福的思考,与我所见略同,只是没有与熵联系起来。而巴塔耶的耗散理论,对此有过富于启发性的论述,我想请陈兄注意这一关联。 当然,如果陈兄的本意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不要用物理学代替经济学。那我想我是不会反对的,而且也是赞成的。 关于价值论:有序和价值的关系 陈兄说,“有序和价值是不同的概念,主流经济学没有这样的说法,有序高价值就高。” 有序这个概念,是熵的延伸。熵代表不确定性、混乱度。一个系统的熵值越高,它就越显得混乱无序,或者说,它的有序化程度就会越低。主流经济学确实没有从系统论角度论证过价值,因此也不会将系统的有序化程度与价值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将系统论引入经济分析,就可以很自然地观察到有序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我向大家推荐张明《负熵与货币》中“劳动输出负熵”这一节。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输出负熵”是一个意思,而有序是指负熵度高。劳动输出负熵,自然提高了系统的有序度,这个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有序与价值是内在相关的。 其实,我本来的观点,是不赞成“有序高价值就高”的。“有序高价值就高”,只是“翻译”主流观点。我的正面观点是,系统与环境匹配(相当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价值的尺度。以匹配为中点,如果熵增趋近中点,熵增的价值就高于熵减的价值(有序低/价值高);如果熵减趋近中点,则熵减的价值高于熵增的价值(有序高价值就高)。前者针对的经验事实是生产过剩;后者针对的经验事实是供给不足。 陈兄说,“生命是耗散结构,但‘熵增经济’和‘耗散经济’都是经济学上所没有的奇怪概念。生产就是减熵,消费就是增熵,这样的论断是不成立的。”我尊重陈兄的看法,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巴塔耶和鲍德里亚,已经非常鲜明地论述了陈兄所说的“奇怪的概念”,而我有条件地认同他们的观点。 至于陈兄所问到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于一项生产或者消费的增熵或者减熵加以度量。无法度量,你怎么用增熵和减熵来研究经济?”我拜读过陈兄的大作《幸福指数》,其中说道,“十几年前我就考虑,既然有痛苦指数,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幸福指数呢?”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正好就是熵增指数呀!小男生小女生怎么说的—酷毙了。就是这个词!COOL(酷)就是快乐的计量单位,COOL就是指熵减的程度,熵减到0,就是“酷毙了”,因为一到零度,人不就冻死了吗?我们说一个MM“美丽冻(动)人”,不就是耗散(熵增)带来快乐的证明吗?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仅不矛盾,而且还高度吻合,完全可以不必争论。 关于交换论:符号交换有特指,相对于象征交换 陈兄说,“商品交换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不是符号交换。” 这恐怕要怪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符号交换,具有特指含义,并非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换。我说的符号交换,采用的是鲍德里亚的专用术语“符号交换”。 鲍德里亚认为,商品交换是“符号交换”。这里的符号交换,就是指等价交换,与符号交换相反的概念不是实物交换,而是“象征交换”,这是鲍德里亚的另一专用术语。 象征交换,是指一般等价物不起作用的交换,比如具有人情成分的交换;符号交换,是指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交换,比如市场交换。两者的区别在于依赖不依赖一般等价物。 我说从感性价值上升到理性价值,是指从具体劳动上升到抽象劳动,而不是说在产品使用价值(功能)上,是否具有感性或理性的特征。陈兄所说的“感性价值的交换为什么会变成理性价值?如果我们把充满感情价值的文学作品交换出售,这部文学作品就具有理性价值了”,我认为应该这样解答,感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本身,是抽象的,如十元、百元。而我说的等价交换使价值形态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是在解释鲍德里亚的一个说法,即符号交换的说法。鲍德里亚的意思是,产品在自然经济中的价值是具体的、不可通约的,这种具体性正好与符号的抽象性相反。在商品经济中,具体价值上升为抽象价值,以一般等价物这个“符号”为中介进行交换。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者所要得到的,已不再是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而是货币这种符号化的一般等价交换物。看来我们在语言上闹误会了。 关于交换论,我的本意是想说,信息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在交换环节上,让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个货币化的可逆过程。这就是由抽象价值再回到具体价值的逆交换过程,也就是鲍德里亚预言的象征交换。按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表述问题,大量使用信息符号的信息经济,恰恰不是符号经济,而是象征经济。信息的作用在于将货币这种抽象符号所代表的社会一般价值,转化成个性化的具体的需求满足(也就是边沁说的幸福和快乐);也就是说,用贴上不确定之源(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方法,消解不确定性于无形。这才是熵的本意。对应的经验事实,是人工智能条件下的P2P,在无序中自发组织、自发协调,实现有序的个性化。 关于目的论:从物质需求满足到文化需求满足,经历着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针对我说的“对于布瓦索来说,经济思想是理性思想的同义语,文化思想就是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经济思想意味着以金钱为本,文化思想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真实意图,是把信息化最终引导到以人为本的目标上来”,陈兄说,“经济思想是理性思想的同义语,那其他理性科学往哪里放?也成了经济学了吗?文化思想是自由的同义语,那封建的法西斯文化思想也是自由的同义语吗?” 这些话很尖锐,也很有道理,抓住了我语言上的毛病,我需要改正。但我想说的实际上是另一个意思。陈兄也谈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是以人为本”。我解释布瓦索“将经济思想延伸到文化领域”的含义,实际落脚点正是在社会生产目的上,不在于说“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而是在说社会生产的主要动机,从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转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强调信息化有一个从形式转向内容的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陈兄推荐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里边有较深的思考。 陈兄评论我的观点说,“美国文化将失之于‘个人知识’的象限。儒家文化将引导经济向‘个人知识’象限回归,很难让人理解。从一般的常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更注重个人的权利、自由、隐私、个人知识产权和个人的知识,儒家文化正好相反。” 我们从宏观上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如何理解信息经济的主体化、个人化趋势?我的看法是,生活质量、文化品味、个人知识这些“以人为本”的福利,固然强调了个人,但与工业化的个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不在一个层面上。比如,欧洲人讲文化品味,看不起美国佬,认为他们缺乏品味,这里的个性化,与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简单地拿一个指标,就可以分辨出来:熵增熵减。文化品味的多元化,具有熵增特征,在物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具有正面的福利效应,可以增进人民的幸福;而合理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通向个性化,完全有可能帮助一个熵减过程的实现。知识与个人知识的区别,也是同样道理。我说的个人知识,不是口语意义上的个人知识,而是英国思想家波兰尼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在这里个人知识是指难以形成文字、只能处在潜意识中的知识,是自然化的知识。如果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概念,可以参见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强调的产权知识,与自然经济中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完全是两回事,信息化会充分调动出类似自然经济中手工业定制方法那样的工艺潜能,实现知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这种更高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复归。 总的来说,我们之间的观点,既有“交集”(如在幸福问题上),也有分歧(如怎么看待经济人),更多的是理解上的误会,希望有机会能够进一步沟通。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互联网周刊》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