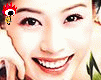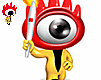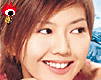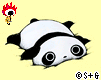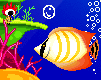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地震局里的“地震”是怎样发生的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09日 18:19 中评网 | |||||||||
|
[案情介绍] 本案所涉及到的争议土地,位于现在武汉地震局也即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院内的中心地带,面积有⒍8亩(458⒊45平方米)。这块土地曾经是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下简称“测地所”)所属武昌时辰站使用的国有土地。这块土地的权属在1970年发生了变化,被行政划拨给武汉地震局,这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却闹出诺大的事端来,与此有关
1978年,中科院向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恢复武汉分院的函”,“决定重建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由于是“重建”测地所,而不是将地震研究所一分为二,所以并没有“分家析产”。测地所在徐东路重新征地盖建了办公楼、宿舍和其他工作和生活设施,并在九峰征地重建了天文台。 1987年中科院武汉分院在武汉地震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武汉市房地产局申请办理了该块土地的房地产使用证。武汉分院申请办证时所使用的土地证明,是其1956年至1970年的建房审批手续,瞒报了1970年中科院的关于测地所划归地震局的111号文件,骗取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证。但当时地震局并不知道此事(地震局看到此证是在1999年打官司的时候),更不知道该证的内容是什么。地震局当时也申办了土地使用证,但比武汉分院晚了11个月,在1988年9月,地震局才拿到房地产证,证的附图列有虚线标明是规划线,地震局有异议。房地产局表示,同年11月将进行土地登记复核,届时会把问题搞清楚的。现在看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房地产局是先给武汉分院办证,而且是完全按照书面材料办的证,并无实地考察或调查了解情况,因此当时真不知道此地属于地震局,地震局再去办证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后,房地产局才知道此前给武汉分院办的证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才在给地震局的土地使用证上列示虚线表示线内土地不能建设,实际上是将错就错地对错误发给武汉分院土地使用证做了某种补救。 1996年武汉分院建成了天文台,在其搬家的过程中就要将时辰站转让出去,遭到地震局的坚决反对,最后转让没有成功。1997年,在武昌区房地产局验证时,地震局再次向区房地产局和区土地管理局反映了此事。但1998年武汉分院偷偷地转让时辰站时,再一次使用欺骗伎俩,向土地局提供了中科院批准此次转让土地的伪证,土地局核准了其土地转让。此间,地震局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0年3 月8日武汉分院与购买土地的武汉银海置业有限公司办完全部手续后,才由银海公司出面告知地震局。 1999年3 月8日,地震局知道了土地被非法转让的事实后,于1999年4 月,以武汉市土地局土地转让违法审批为由,向湖北高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银海公司所持有的WC—国用(1999)0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省高院的建议追加武汉市人民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立案后,依地震局的申请,法院对时辰站的土地实施了冻结。5月26日被告答辩完毕,诉讼正在进行时,省高院根据省里一位领导“此案不出湖北省”的口喻,于6月14日突然通知地震局,决定立即将本案移送武汉市中院审理,同时作出解除时辰站⒍8亩土地冻结的裁定。 此间,银海公司也于1999年4月23日,持该《国有土地使用证》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排除妨碍之诉。武昌区法院、武汉市法院在行政诉讼结果未定前,作出地震局必须排除妨碍的判决。这期间地震局多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的规定,请求中止审理,均未被法院采纳。之后,地震局向湖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2000年1月24日,省检察院提出抗诉书。2000年2月23日,湖北省高院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⒈市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⒉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1999年5月17日,也就是在市土地局已经批准了该土地的转让以后,武汉市政府、市土地局对颁发WC—国用(1999)0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予以公告,在公告异议期,地震局提出权属异议并对1987年权证提出异议,该两级行政机关未予答复。同年7月,地震局针对该两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判决被告必须作为。1999年11月,地震局向武汉市房地产局、武昌区房地产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包括时辰站在内的6块地和73户插花户的产权问题进行查验,该二局未答复,当月,地震局向武汉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二局书面答复查验申请。1999年12月中院作出107号判决。根据判决的要求,该二局有一个回函, 回函证实1987年颁发时辰站的土地使用权证时的依据是市政府(1985)203号文、市房产局(1985)20号文,以及武汉分院当时提交的房地产权属登记申请书以及历史手续材料,但这些材料中并没有中科院1970年的111号文和1978年中科院决定重建“测地所”的文件。 1999年11月5日,国家财政部针对时辰站转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正式立案查处。 2000年2月23日,国管局财务司会同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就协商解决中国地震局所属湖北省地震局与中科院所属武汉分院之间的时辰站等房地产争议问题进行了调解,目前此调解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2000年3月28日,地震局针对1999 年12月29日武汉市房地产局、武昌区房地产局的验证答复向武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依法撤销该二局在双登时对时辰站房屋和73套插花住宅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案件亦正在审理之中。 2000年4月3日湖北省高院不顾上述正在进行当中的种种解决问题的努力,一意抢先作出判决,确认市政府和土地局审批土地转让的行为合法。 5月25日武汉中院在大批武装警察的护卫下,在武汉地震局院内强制地为银海公司开出施工通道。现在银海公司建筑商品房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此间,银海公司与地震局的冲突不断,地震局的办公室被砸、围墙被拆毁、包括两名地震局负责人在内的24人被打伤。几个月来,地震局的工作、科研秩序受到极大地破坏,正常的科研工作已无法展开。 [分析] 这个案件涉及到土地的权属、两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两审法院的判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 土地权属问题 应该说,在本案中,土地权属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谁,本身就是在承认历史沿革基础上的确认。就武汉地震局这块土地而言,既然1970年该地已经行政划拨给地震局,且其后没有任何其他法律文件,对这一问题作过变更,毫无疑问,这地的使用权就是武汉地震局的。这是十分简单、相当容易判断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么明了的问题上出了矛盾,使十分清晰的权属变得复杂起来,行政机关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对本案应当吸取的教训之所在。 二、 关于本案中的第一个行政行为 从1987年中科院武汉分院从武汉市房地产局取得该《土地使用证》的过程中看,武汉分院瞒报了1970年中科院决定将测地所划归地震局的文件,即隐瞒了重大的历史事实,应当说这种“取得”是一种骗取;从房地产局这方面来看,房地产局的发证行为有如下缺陷:第一,房地产局不是适格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证》应由土地管理部门发放,而中科院武汉分院持有的时辰站的《土地使用证》是由武汉市房地产局颁发的。行政机关对此的解释是,武汉市政府1985年的203号文已指定武汉市房地产局负责房地产权清理登记和发证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该土地使用证是1987年发放的,也就是说此时《土地管理法》已经实施,市政府的规章与法律规定不一致,当然要以法律为准。 第二,房地产局发证时所依据的证据不足。武汉分院在登记权属时提交的证据除了1956年-1970年的建房审批手续外,另一个证据是1985年“关于处理分所中房地产争议的处理意见”。但这一文件并不是地震局与武汉分院之间有关这块土地的转移协议。纵观协议,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部分宿舍产权的转移问题,如果从中推断出地震局已将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武汉分院的结论,未免太武断了,对行政行为而言是证据不足。 第三,房地产局发证时程序上有问题。土地权属证书的核发是非常重要的行政行为,但是房地产局既没有调查、核实,也没有实地勘测、丈量,只是根据并不完全的书面材料,就作出这样重要的行政行为,其工作的粗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三、 关于本案中的第二个行政行为 本案的第二个行政行为是1998年武汉市土地局审批该土地转让的行为。这个行政行为同样是有问题的:一是将1987年房地产局违法发放的土地使用证当作自己审批土地转让的证据使用;二是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关于“土地存在权属争议不得转让”的规定,面对被转让的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的客观事实,土地局却称时辰站的《土地使用证》面积准确、界址清楚与相邻的湖北省地震局所持有的《土地使用证》并无交叉或重合之处。但是,土地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996年武汉分院试图转让土地时,地震局多方申诉,在1997年,武昌区房地产局验证时,地震局再次向区房地产局和区土地管理局反映此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局的声称是在表示它不知道两者之间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话,作为职能部门,又怎么能推脱其“不知道”此地存在争议的渎职责任?三是土地局审批土地转让的程序违法。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可见,土地局审批土地的转让,还要经同级人民政府的批准。尽管地震局在诉讼中一直对此持此异议,但是即使到了今天,地震局也从未见过市政府同意土地局将土地出让给受让方的批复。土地局能够拿出来的是某副市长签署同意土地转让的白条,没有市政府的公章。法律行为是要求一定形式的行为,这样的白条怎么能说是政府的批准行为?另外中科院武汉分院是中央事业单位,其转让的土地首先要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立项后,土地局才能审批转让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但到目前为止,土地局也未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四、关于本案中的两审判决 本案中的一、二审判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土地权属争议排除在此案的审理范围之外。一审判决说“土地权属的主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说;“上诉人就时辰站土地提出的权属争议,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但奇怪的是,两审法院一方面说“不管”这一法律争议,另一方面却又认定“分院的《土地使用证》面积准确、界址清楚与相邻的湖北省地震局所持有的《土地使用证》并无交叉或重合之处不具有土地权属争议的特征”。从这一看似矛盾的判辞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终审法院实际上以行政审判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为借口,回避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当进行实质性审查这一关键。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必然要涉及到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是否有事实根据问题的。已如前述,按照法律规定,土地存在权属争议,是不能转让的。可见,这块土地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是衡量有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事实根据,所以两审法院想要回避,却又不得不同时认定不存在这一权属争议,否则就不能证明审批土地转让是合法的,因此法院只好矛盾地确认在这块土地上不存在权属争议。这种不睁眼看事实的做法,怎么能说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法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去认定谁对这块土地拥有使用权,但要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是否存在权属争议。 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除了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外,还要从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有无滥用职权等方面进行审查。在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上,法院应遵循法制统一的宪法原则。但是遗憾的是,法院在此问题上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土地法》第16条第4款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的利用现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其中第5项规定:“权属有争议不得转让”。此案中,土地局审批颁证的行政行为,正是批准了存在着权属争议的土地的非法转让,为了使土地局的批地行为变为合法,终审法院的判决认定:“市政府、市土地局将该土地使用证作为土地转让的法律依据,并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暂行条例》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所设定的法定条件”。这一认定避而不谈市政府和土地局审批土地转让应当适用的《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而断然宣称没有违反另外两个法规,岂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着边际?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中,就是关于该土地转让前,时辰站是否应当进行评估、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问题。市政府、土地局认为自己只负责审查转让的土地是否符合转让的法定条件,土地是否经过评估、是否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不属于审查内容。终审法院的判决进一步为其补充道:“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未将土地评估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作为土地出让转让的法定条件,上诉人据此提出被上诉人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判决的意思是说,国家大法没有规定评估、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的程序,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是不算数的。这种说法与法院上述关于适用法律问题上的说法一样,都不符合法律的适用原则。 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象我国其他方面的立法一样,是分层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下位法不能对上位法进行补充和细化。在我国目前法律法规条文规定往往十分抽象、十分原则的情况下,处于下位的规范,经常是补充性的。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是否适用一个下位法,主要看这个下位法是否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或精神,如果没有违背,执法的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没有权力放弃适用该规范。在前例中,法院避开应当适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而说土地局是依据另外两个法规审批的土地,错误至于:国家大法已经作出的规定,下位法没有规定,那么执法者、司法者就不应当只适用下位法,因为下位法的规定不全;在土地评估问题上,由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5)106号文件的规定没有违反法律,尽管它是下位法,也要得到遵守和适用,它所规定的评估、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批准就是必要程序。 两审法院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武汉地震局考虑到中科院武汉分院与武汉地震局都是中央在汉单位,最初是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湖北高院已经受理该案,收取了诉讼费,采取了冻结措施,但却因为诉讼外的因素,又将案件指定给武汉中院审理,解除了冻结措施,且未向地震局正式出示理由,与法定程序有违,做法上显然欠妥。又如,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中,土地局应向地震局出示其证据,同时要经过法庭质证,否则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但本案中的某些证据,地震局至今未见过,更谈不上质证。证据是案件裁断的决定性因素,司法程序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上述问题的存在,当然会影响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另外,法院应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进行审查,但是终审判决的认定亦有阙失。终审法院的判决说“在无证据证明该宗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市土地局没有进行变更地籍调查和勘丈,不应以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但是查看一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登记规则》、《关于变更土地登记的若干规定》、《关于地籍管理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进行变更地籍调查和勘丈,并不以存在权属争议为前提,而是以实施房地产转让或变更为前提,因此可以肯定,土地局没有进行变更地籍调查和勘丈,违反了法定程序,而法院的判决肯定了错误的做法,当然也就是错误的了。 本案已经终审判决,但本案所涉及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矛盾越来越激烈,这种结果实在是令人深思。人常言:不平则鸣。观察此案的种种现象、拜读两审判决,联想到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看来,人民法院要走上司法公正这条路,还要有一段漫长的过程。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刘莘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