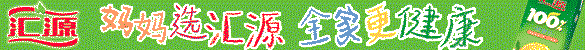|
特约评论员 秦明阳
近来有关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不绝于耳。国际会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公司不久前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这7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到200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G7)的。其中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是最快的,从现在起到205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6%。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说,印度经济几年内年增长率将达8%-10%。美国著名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普雷斯托维茨在其《30亿新资本家: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一书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乐观预测,他说印度经济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维持7%-8%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印度官员也充满了信心。辛格总理去年底表示,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3年内将达到10%。
其实考虑到印度经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再加上中国这个参照系,此类乐观的预测不能说是夸大其辞。印度在过去14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6%,其速度之高和持续时间之长仅次于中国。如果单从时间方面来比较,印度经济改革的1991-2005年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1978-1992年。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宣示中国的经济改革趋势不可逆转,而且中共十四大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历经14年改革和快速发展的印度也可以说正进入类似阶段。
当然,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无疑是后来者,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官僚主义、对企业不利的劳动法、对外国投资的众多限制等常常为人们所诟病。但这些都是改革有待克服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不能被视为改革失败的象征。尽管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预测和印度官员本身的自信都说明,印度经济当前正进入快车道,“印度式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历史。不仅内部出现了强劲的搏动,而且外部环境对其发展也有利。
借力:推进内部改革
印度现任总理辛格无疑是坚定的改革派,更有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美誉。1991年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就致力于经济改革,到2004年担任总理时凭借手中更大的权力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今年年初,他不顾其联盟政府中左翼伙伴的强烈反对和工会的大罢工推行机场管理私有化的举措,就很能说明他的改革意志。
尽管有坚定的改革决心,但辛格发起的改革注定要面对重重困难。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位弱势总理。他所在的国大党未能控制国会议席中的绝对多数,因此不得不跟其他政党结盟。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进行折衷妥协,就改革措施取得联盟伙伴的支持,以防政府垮台。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仍面临很多禁忌或雷区。辛格政府推行的机场管理私有化政策所激起的大罢工就很能说明私有化问题的敏感性。更准确地说,印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去投资化”,而且“去投资化”的比例一般不会超过国有企业总资本的50%。尽管如此,仍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印度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劳动法改革。1947年颁布的《产业纠纷法案》规定,雇佣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不能解雇任何人。但政府很少会批准公司解聘员工。这部缺乏灵活性的法案实际上对劳资双方都没好处,因为它促使印度公司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即便有廉价的劳动力也不充分利用。尽管这部法案已经不合时宜,但各个政党顾忌它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而不愿触及。如何放宽诸多对外国资本进入的限制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尽管印度的改革开放进展缓慢,而且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但这并不妨碍印度经济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事实上,印度在过去14年里的改革动作并不大,但经济仍以超过6%的年增长率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印度现行体制之外出现了新的增长点。这证实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阿瑟·刘易斯的判断:“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他因素。”就印度来说,它是引进了新的技术。它虽然错过了制造业大发展的潮流,却在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下抓住了机会。印度政府虽然在改革现行体制方面步调缓慢,却很少对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等进行干预。印度私营部门在这些行业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并有不俗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印度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本土企业,如软件业巨头Infosys、Wipro等,令国际社会对印度刮目相看。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印度新兴产业的产值、出口额和创造的就业机会等纯粹的经济指标,就未免会低估其作用。
在新兴产业中诞生的一批杰出企业家在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提高印度的国际知名度和声誉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那一代领导人所推行的“费边社会主义”虽然不主张消灭私营企业,但在国家政策上却向国有企业倾斜,厚此薄彼的倾向十分明显,私营企业及其业主相对受到轻视。不过如今这一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经济成就的明星级企业家已经获得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们在国人眼中成了“民族英雄”。其中Infosys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被印度人骄傲地誉为“印度的比尔·盖茨”。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一点对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低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刘易斯认为,商业地位在英国和西班牙殖民扩张时期的贵贱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们后来的发展差异。
他们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影响之一是刺激印度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盛行禁欲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活动。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任何社会中最富有进取心的年青人总是会选择能为他们赢得最崇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而“只有在经济活动中有成就的组织者能获取最高声誉,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心思转向经济活动”。他们所享有的社会地位会吸引更多的人创造财富,而不只是分享他人的成果。此时在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的贫民窟中,也许正有一个少年梦想着成为下一个“印度的比尔·盖茨——纳拉亚纳·穆尔蒂”。
他们对印度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提高的贡献也为他们赢得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曾经无所不管的印度官僚机构很少干预这个既能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又能提高该国国际声誉的新兴产业,更没有对私营部门实施有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社会的革新者,能够引导现行体制向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促使制度性的障碍以更快的速度瓦解。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转变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必定引起制度的变革,而制度的变革又反过来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力量。印度如果进入这个良性循环阶段,其经济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拓路:改善外部环境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自1991年印度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其外交政策相应进行了调整,明显倾向于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这种调整为其内部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营造了比较有利的外在环境,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体现在它与美国、中国及其海外侨胞的关系的改善。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在冷战期间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不过近年来出现稳步发展的态势。美国总统布什3月初对印度的访问将双边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印度和美国这两边都有人将其与尼克松访华相提并论。对于处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初步阶段的印度来说,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目前来说,美国依然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市场、最雄厚的资本和最先进的技术,而且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布什在访印期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经济议题相对被忽视了。但事实上美国工商界一些重量级人物也跟随布什访问了印度。美国目前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布什访印期间两国的贸易官员还宣布提前实现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即到2008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美国市场对印度的新兴行业,如软件和外包服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一直是印度软件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据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40万个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流向海外,印度的服务业无疑将大受其利。
印度能从双边关系改善中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世界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这是因为美国是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最大股东。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去年访问印度时宣布在3年内将向该国提供90亿美元的贷款。
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待印度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亲美立场,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印度支持美国的立场以换取美国帮助印度发展核能的一笔简单交易。
作为印度的最大邻居和一个有待开拓的庞大市场,中国对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能忽视。1962年的边境冲突一度使双边关系跌入谷底。如今在务实外交的推动下双边关系显著改善,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两国已宣布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
对于想扩大出口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中印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美印贸易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有可能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也不断增加。中国的“硬件”企业和印度的“软件”企业相互到对方投资。
对于中印来说,能源合作是一个更重要的领域。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进口石油分别占各自能源需求的40%和70%。能源安全事关双方各自的经济发展前景。如果鹬蚌相争,只会对第三方有利。为了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印度石油部长艾亚尔今年1月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其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能源谅解备忘录。此前双方石油公司已经进行过合作,在去年12月以各占50%的比例收购了加拿大一家石油公司所拥有的一个叙利亚油田的38%的股份。
独立后的印度对引进外资持消极态度,直到如今对外国资本的进入仍有诸多限制,外资的进入经常在印度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反对。这可能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东印度公司恐惧症”还有待克服。回想起东印度公司从一家贸易公司变成殖民政府的过程,印度人有理由对外部世界保持警觉。就现实需要而言,这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
印度对外资的排斥甚至还针对它的海外侨民。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每年吸引的外资只有数十亿美元,而其侨胞的投资仅占其中的约10%。相比而言,中国2004年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其中华侨和港澳投资者的投资额占60%,他们被誉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种力量”。如果说中国这艘航母是由双引擎推动的,印度这艘航母只有一个引擎,其速度自然相对慢些。
不过印度如今改变了态度,不仅在努力为外资的进入扫清障碍,而且张开双臂拥抱侨民。印度政府今年1月7日在海德拉巴市举行的第四届“海外印裔代表大会”上宣布授予16个发达国家的侨胞终身护照,总理辛格更是亲自授予两位美籍印度人终身护照。印度政府此举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为其侨胞提供便利,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
当然,海外印度人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单就印度裔美国人来说,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印度裔美国中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6万美元左右,远远高于38885美元这一全国平均水平。另据《2006全球经济展望》的统计数据,去年全球汇款超过2320亿美元,其中印度收到的最多,达217亿美元,是其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几倍。海外印度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无疑会加强印度经济发展的动力。
总而言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经济正在进入快车道。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有碍经济加速发展的因素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被克服。
当然,这样的预测都是基于印度当前的经济性因素。然而,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一些非经济性因素时常会干扰其进程。恐怖袭击、教派冲突等问题都有可能在印度引发整体性的动荡,经济发展因此有可能减缓甚至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