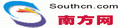大旱之年 谁赚谁赔
每一次灾难,都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据中新网报道,截至3月17日,西南五省份因旱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90.2亿元。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商人从灾难中获益,他们大多根据自己的灵敏嗅觉去下注,也有人仅仅是搭上了便车。
 |
云南文山州的三七因旱而贵 (CFP/图)
三七“牛市”
自去年下半年起,青岛的中药采购商刘辰就开始增加药材三七的储备。往年刘辰只需要储存10吨左右,但现在他的仓库里有近20吨的三七。
三七又名田七,是中药的主要原料,目前有三百多个中成药品种需要用三七作为原料,几乎全国所有的中药制药企业都要购买三七。而三七“偏爱”云南文山州——全国三七产量的97%来自这个地方。
“在这次西南大旱之前,三七的价格已经涨了很多。”从事三七收购已10年的刘辰说。从去年8月份起,他感觉到三七在市场上变得更为紧俏。今年年前,他还从亲戚朋友处借钱来收购三七囤放,毕竟三七不会因长期储存而变质。
事实证明刘辰的市场嗅觉是灵敏的。文山州文山县三七特产局局长吴志亮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制药企业每年对三七的需求量为7000-8000吨;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当地的三七年产量从3年前的上万吨,减产到去年的4000多吨。而且,三七的种植周期是三年左右,很难实现当年就增加产量。
3月上旬,刘辰到了安徽亳州。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他在这个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和交易市场里目睹了三七价格暴涨的历程——从3月中旬的每公斤300多元,涨到了3月底的每公斤近600元,好的品种更在600元以上。
“半个月里价格翻了一番,这时也是西南大旱最严重期间。”刘辰说。据文山州三七特产局统计,截至3月15日,该州三七受灾面积约5.67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94.5%。另外,如果今年三七绝收的话,未来两三年内都会处于供给短缺的情况。
一位在亳州从事中药材交易逾30年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她所见到的最高的三七价格。而且近年来涨得太快了:2008年初是每公斤30-60元,到了2009年6月也是每公斤70-150元,“也就是说,现在比两年前涨了10倍,比去年中涨了4倍”。
在这轮三七“牛市”中,刘辰获益不少:他的收购成本每公斤不到300元,而现在价格翻了一番,按20吨计算,他的账面盈利达600万。“最近卖了4吨,获利100万左右。”刘辰说,最近暂时不再买进三七,然后慢慢地卖出。
不过,在刘辰看来,他只是“小打小闹”而已,比他赚钱更多的大有人在。眼下,无论是制药企业,还是收购商或药商,只要谈起三七,都会提到康美药业,以及它囤积的2000吨三七——这个数字接近去年产量的一半。
上述亳州药材交易人士透露,康美药业“钟情”三七早在2006年开始,当时是文山三七产量的最高峰。几年来,康美药业的收购价都为每公斤30-40元,最高不超过50元,“账面盈利会超过10亿。”目前,康美药业要求只有在10吨以上的需求时才会卖出三七。
在一些同行看来,康美药业成了最大的三七贸易商。甚至有制药企业表示,三七的价格被一个联盟所操纵。不过,直到现在,地处广东的上市公司康美药业仍对各种传闻保持沉默。
三七市场的丰厚利润,还引来了实力更强的资金介入:3月,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公司宣布,将在云南3年内合作投资5亿元打造三七种植基地。“三七涨价是供求关系的反映,未必是坏事。”云南文山州三七研究院院长崔秀明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前几年三七的价格太低,农民都不愿意种植,现在价格上来了,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且提高三七的种植质量,“质量好,卖的价更高”。
辣椒“空城计”
大旱之年,手上囤着逾百吨辣椒,本应大赚一笔。但贵州辣椒商人单雄此时却如同握着烫手的山芋。
西南大旱让贵州遵义虾子镇“中国辣椒城”的辣椒商人们躁动不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辣椒生产基地。现今正是辣椒的生长时节,持续的干旱使辣椒种子根本没法发芽。而在往年此时,辣椒苗子已经长出三四寸了。
今年初灾情逐渐加剧时,单雄从乡下农户和辣椒贩子手中开始收购大量的辣椒。现在,他已囤积了上百吨的辣椒,就等着辣椒“青黄不接”无法接上趟时,出手大卖一笔。
3月初,囤积风潮一度席卷中国辣椒城。“3月18日上午,很多重庆老板都在那里抢购辣椒,一位辣椒商还带我去看了他囤积辣椒的库房。”一位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贵州省相邻的重庆市,一向有吃辣的习惯,重庆火锅更是遐迩闻名,每年的干辣椒消耗量达数万吨。据了解,重庆人特别喜爱来自贵州的辣椒。“北方的辣椒跟南方的味道不一样。”一位重庆火锅店老板说。
3月初,辣椒最高的价格涨到了每斤12元,相当于去年最低价每斤三四元的3到4倍。尽管如此,市场上仍供不应求。
不过,辣椒商们都在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即使面对这样的价格涨幅也不动容,只有少数商家当时卖过手上的辣椒。毕竟,目前市场上的辣椒多数为前两年的存货,尤其是2008年丰产时库存较多,他们囤积的辣椒成本都不高。
所以,到了3月中旬,辣椒商们依然在期待着辣椒价格再次“井喷”的来临,尤其当西南大旱继续蔓延时。
然而,他们的愿望落了空。现在遵义市场上的干辣椒价格已经由最高峰时期的12元掉到了7元一斤。原因是,买辣椒的商人们纷纷避开遵义这块灼热的交易地,转道两湖地区或者是河南、山东的辣椒市场。这让本该火爆的遵义辣椒市场的交易量大幅度缩水。
贵州市望谟县一位辣椒农户告诉记者,他的辣椒地就快要成熟,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来订购的老板,于是他只能通过各种渠道给自己的辣椒做宣传,以增加销量。“价钱比起之前又跌了一些,”该农户说,“我家种的是新品种,要到农历三月初三之后才能收获,以往年份也没有存货,没能赶上之前的火热期。”
单雄之前还幸运地以每斤9元的价格卖出了十来吨,但盈利不到3万元。“否则压了太多资金进去,就影响周转了。”他说。
当初囤积辣椒的这场“空城计”并没有给这些大量囤货并准备打持久战的商贩们带来意料之中的收获,获益者反而是最初出售辣椒的乡下农户和贩子,他们把手中的辣椒卖给这些辣椒收购商的价格虽然不能跟巅峰时期的市场价相比,却借着“短缺”之机小赚了一笔。那些在巅峰时期果断出手的商贩则获益最多。
囤积着逾百吨辣椒的单雄,目前惟一的希望是七八月份辣椒市场的旺季到来,因为“那个时候辣椒的需求量特别大”。
运水比运酒赚钱
老郑没想到,一场旱灾,使得运水比运酒赚的钱还多。
开酒罐车的老郑,平时一般是为茅台镇上的小酒厂运酒。就像电召出租车一样,小酒厂打个电话过来,老郑就去给他们运酒。
在茅台镇,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如雷贯耳的“国酒”贵州茅台。不过,其实茅台镇还有数以百计的“不出名”的小酒厂,例如,茅台镇中区的两条村里就有上百家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小酒厂。
“我运酒快十年了,都没有这一次运水赚的钱多。”在“中国酒都”茅台镇土生土长的老郑有点夸张地说。以前他为茅台镇上的小酒厂运酒,每趟最多赚100元到150元,少的时候才70块左右,而且每趟总要跑个二三十公里。
但这次西南大旱期间,老郑的酒罐车“转行”了——运水不运酒。“每趟可以赚500块,最高峰时是700块,每天可以跑六七趟。”精打细算的老郑说,每次跑的路程也不远,从小酒厂到赤水河抽水,每次运15—20吨水,才不到10公里。
掐指一算,从3月10日起,老郑平均每天赚2000元,最多的一天赚了接近4000元,20天的时间赚了4万多,这几乎等于他去年全年的收入。
一位在茅台镇考察的经销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赤水河的水位的确有所降低,但没有影响到“国酒”贵州茅台酒厂的生产,原因是贵州茅台在赤水河的上游河段较好的位置取水,而且凭借其“财大气粗”可以不惜成本地用水泵抽水。
不过,对于那些势单力薄的小酒厂而言,尽管毗邻被誉为“美酒河”的赤水河,但它们长期以来都是从水厂买水来酿酒,其中一些水厂的水源是处于赤水河上游的四川泸州地区。
西南大旱使得水厂的供应变得不稳定。水源所在地区的村民担心大旱持续的时间过长,破坏了一家水厂通往茅台镇小酒厂的管道,直接导致当地酿酒业“旱上加火”——好些小酒厂不得不因此暂停生产。
到赤水河下游河段取水成为了权宜之计。当地一家小酒厂老板告诉记者,出于对水质和成本的考虑,平时小酒厂都不会直接使用这一河段的水。“现在只好通过水泵在河里抽水,再请酒罐车把水运回来。”他补充说,幸亏现在不是九月初九“投料”的季节——在那时候必须要用高质量的水。
他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酒罐车每次运回15-20吨水,这足够酒厂进行4-5次“蒸”酒酿造;而每一“蒸”酒大约为90公斤左右,盈利为1000元到2000元不等。也就是说,酒罐车每运一次水回来,有助于酒厂创利5000-10000元。
“这样算来,请酒罐车运水还是值得的。”这位小老板感慨地说,500元运水的价格是高了点,但是没办法。如果不这么买水的话,可能酒厂的损失更大,现在因缺水而停工的工厂相当多,已经不止十几家了。
(因被访者要求,刘辰、单雄为化名)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