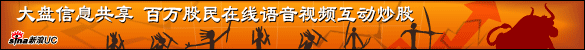不支持Flash
|
|
|
|
我的一九七七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9日 16:50 《英才》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在奔向天堂,我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狄更斯(提语) 策划|天下工作室 主笔|本刊记者 孙雅男 采访|本刊记者 王颖 严睿 罗影 孙雅男 总有一些被特别注明的年代,或关生死,或关存亡,是里程碑,是转折点,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1977年,便是这样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年代。 那年冬天,传来一则最为温暖的消息,在动荡中停顿十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春风重度玉门关,这则消息不仅为苦无出路的工人、农民与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燃起了希望,更使得经历了十年动荡的国家走向复苏与新生。 许是中国史上最受瞩目的一次高考,徘徊在漫漫长夜中的天下学子从此重新获得了掌握命运,选择道路的权力。570 万年龄参差、背景各异的考生奔赴考场,为自己的人生,也为这个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国家,书下历史性的一笔。 那是中国史上唯一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可在无数曾经走过那个年代的考生记忆里,1977年,没有冬天。"为什么在30 年后,当年的那次高考再次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有受访者如是问道。 30 年,对于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或许不过是转瞬即逝,可对于个体的轨迹而言,却记载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沉浮。 30 年年轮印记,当初的稚嫩小苗已成为参天大树。 30 年前种下的因,如今果见雏形。我们不想为了回首而回首,为了纪念而纪念,重要的是,30 年,是可以梳理因果的时候了。 《英才》记者走访了一批出身于七七级的知名企业家,忆及往昔,唏嘘之际,有受访者随便指着窗台上一张不久前在美国举行的企业家峰会的合影,里面的七七级考友比比皆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亚洲区总裁熊晓鸽、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慧聪网董事长郭凡生、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分众传媒总裁谭智??大浪淘沙,经过七七年高考的洗礼,那些曾经在乡下田间,挥汗如雨的身影,如今已然活跃在时代的潮头,成为受人瞩目的企业家,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30 年的断代史再次向人们印证着"时势造英雄"的结论。时代的上下进退,承载着个人的命运沉浮;个人的得失悲欢,折射出时代的发展脉络。那是一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走过1977 年的高考,人人都是传奇。 高考前:知青 王维嘉 从地狱到天堂 口述| 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 "王维嘉,你考上科大了。 “别逗了,你骗谁呀。” …… 当第一个同学带给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完全不能相信。后来,又有同学跟我开同样的"玩笑",我便开始半信半疑。直到我的父母带着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的确是真的。 方圆几里,考生无数。只有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这在当地甚至轰动一时,走在路上,所有见到我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跟我打招呼,那种感觉就像中了状元,真的很high,我虽然没有吃过摇头丸,但我想吃了摇头丸的感觉应该也不过如此,我相信我死后升天堂也就是那样的感觉。 当时报科大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因为科大在当时是全中国最难考的学校,录取分数比北大、清华还要高很多。如今想来,依然会心有余悸,如果1977 年我没有考上,等待我的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18 岁那年伊始,我便成了下乡的知青。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回到城里当个工人。可刚刚下乡,回城遥遥无期,每天在地里干农活,去砖厂烧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欲望也没有想法,精神麻木不堪,自暴自弃。那是一个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尊严,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 直到1977 年10 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生活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已经两年没有上过学的我们跑去问大队书记,想要回城复习备考。"现在是'大干一百天'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回家复习呢?那些东西不重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很重要。"大队书记说。其实知青从农村回城,要贿赂大队书记的,当时的行情是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块手表,在当时是很贵重的。 我们只能边烧砖,边复习。烧砖最累的是做砖坯出炉的过程,热的要命,我们光着膀子,分成两组,一组人做另一组人跑到树荫底下,赶紧算一两道题,5 分钟轮换一次。一天的时间很短,也没人辅导我们。眼看离高考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一干考生决定,不管了,回城。 回到陕西城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全是义务的,分文不取。十年没有过高考了,老师学生都很激动,一个大教室,1000 人都在那里听,老师愿意教,学生也愿意学。 高考前一个星期,我们只能回到农村公社参加高考。料到大队书记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备了干粮。果然,大队书记给我们断了粮,我们就干啃了一个星期的馒头。后来,直到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前一天都没有吃饭。我清楚地记得高考第一天的感觉,早上6 点起来走路到公社,第一场考完出来,又饿又累,只觉得天旋地转。 那一年,陕西省的作文题叫作《科学的春天》。我原本就喜欢历史,尤其是科学史。当时看完作文题目,我便文思泉涌,从哥白尼的日心讲到加利略如何被烧死,一直讲到"四人帮"压制科学,一气呵成,写得心里非常舒服,把多年来对"四人帮",对集权体制的痛恨宣泄殆尽。后来听说,那篇作文得了90 多分,是全省第一名。 1977 年的时候高考还要政治审查,虽然我的出身没有问题,但由于当初的积怨,大队长拒绝给我们出具政审材料。没有大队党支部的盖章,没有人敢要我这个学生。我从上到下的求情却于事无补。直到招生团临走的最后一刻,我们才找到一个很硬的门路疏通了关系。 如今重提当年的高考,是非恩怨已然久远,如果说不曾有过恨意或许虚伪,但我并不恨某个单独的个人,我恨的是那种制度,那种没有监督的集权。当年的大队书记不过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旦手中有了这种不被监督的权力,就会为非作歹。让这些原本可以是好人的人变成恶人。这种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但其实现在仍然会发生。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于我而言,1977 年的高考有着莫大的意义,那种影响要甚于后来我出国,拿博士,甚至创业??那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从地狱,到天堂。 ( 整理| 本刊记者 孙雅男) 高考前:知青 徐刚 政审不合格差点没录取 口述| 上海华普汽车董事长徐刚 前段时间送女儿参加高考,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一晃已是30年,感慨颇多。 1977 年,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下乡、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就在刚刚下乡的三四个月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有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要恢复高考,可以去报名的消息。这下可高兴了,要是推荐上大学,必须要劳动一年,还要和大队书记、主任等搞好关系,而且有名额的限制。 我立刻跑回学校报名,但报名之后,大家谁也拎不清这个试要怎么考,社会上也没有复习资料或者考试大纲什么的,更滑稽的是,考试要考物理,可我们那时候的高中只学过机电,学手扶拖拉机怎么能弄好这样的东西。我们只好跑去跟学校老师说。 老师很负责,很快把"文革"中一些被打成反动分子的老师请回来。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女物理老师,她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不到,就把所有的高中物理给讲完了。不过,我们没有书,只听了个稀里糊涂。 从复习到考试,前后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考试是在1977 年12 月,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考数学的情景,一道在现在看来很简单的排列组合题,我就傻眼了,因为我们没学过这部分内容,所以不会做。实际上,当年考的相当一部分题目是我们没有学过的。 那时候,不是先出分数,而是按照录取名额的110% 或者120% 的人通知,参加体检和政治审查,没有参加体检和政审也就意味着肯定没录取的希望了。一个月后,我接到体检的通知,这才松了口气。然后是填志愿,也拎不清怎么填。我当时报的是浙江大学,这也是我唯一知道的大学。 1978 年春节前后,其他一些同学陆续接到通知书走了。可我的通知书始终没有出现,只好托人去问。这一问才知道,我是不予录取的对象,因为我的政审不合格。原因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而且父亲在"文革"的时候抄过大字报,所以父亲单位的领导说我父亲是"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就在我的政审材料上盖了个印:"四人帮"残余分子子女。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浙江大学等四所本科学院都曾调走过我的档案,但因为有这么个印存在,就都没有录取我。 我父母没办法,只能去求领导,那领导还不错,就跑到教育局又补盖了一个印:可以教育好子女,可以录取。可时间已经晚了,浙大不可能重新再录取我了。这让我很伤心,我真的很想念大学。 后来,台州师专要我,虽然那时候我不大明白专科学院和大学有什么区别,但我想来想去,有书念,能把户口迁回城市,所以就去了台州师专。说实话,我对当个中学的数学老师并不是很感兴趣(那时我被当作中学数学老师培养),我更喜欢文学和写作,所以自己平时其他书看得比较多,学校的活动也积极参加。但正是这样"心有旁骛"的两年学习,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 毕业后,我只教了一年半的书,就被调到了机关工作。1984 年,邓小平提出机构改革,提出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后两项当时都是有指标的。所以,很快我就成了当地一个财税局的副局长,那年我才23 岁,是全省最年轻的财税局长。他们讲,提拔我,一下子把当地的科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拉低了1.5岁。 回想起来,人生机遇向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谁知道哪一年要恢复高考,如果当时我下乡放弃坚持边劳动边学习,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恐怕也过不了分数线;如果念师专,还是紧着专业学,到机构改革的时候,恐怕我也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 ( 整理| 本刊记者 严睿) 高考前:学生 张宏江 第一次有了选择权 口述| 微软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宏江 1977 年,我正好高中毕业,等待我的只有下乡一条路。户口已经迁到农村,但大家都还拖着。那段时间,我经常看见母亲偷偷地流泪,因为我哥哥已经下乡两年,现在她的小儿子又要走上这条道路。 有一天,我正在和小伙伴们疯玩,我父亲所在干校的一个同事告诉我,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虽然我并不像我母亲那样惧怕下乡这件事,但有机会上大学还是更让我兴奋。很快,我跑到离家不远的哥哥插队的地方,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接下来,我开始四处搜集高考资料。我给在北京、上海的亲戚朋友写信,要来了一些油印的复习材料。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干校里一些叔叔阿姨家里居然还翻出一些"文革"前的课本。就这样,我和我哥哥共同拥有了一套拼凑来的高考复习材料。 那段时间,是我十年来最用功的一次。但是由于很多年没有正式考过试,当我拿到高考的理化试卷时,一看到题目脑袋就发懵,觉得要上厕所。当我在好几个老师的陪同下,上完厕所回来,再一看题,几乎都会做。直到交卷前几分钟,我还在不停地算啊算。监考的老师甚至开玩笑地说,"整个考场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做题。"其他很多人早就已经停笔了。 紧张的高考很快过去,在等待分数的时候我已经正式下乡。春节前一天,我哥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被第一志愿录取,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当时,在知青点有人问我,"你的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有到?"我信心满满地回答,"也就这两天吧。" 五天后,父亲干校的一个同事从县城回来,向我父亲恭喜儿子考上了大学。父亲很是纳闷,这都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结果那个叔叔说,"我是恭喜你二儿子,考上了大学。"原来他把我的录取通知书从县里带回来了,我被第二志愿录取,考上了郑州大学电子系。 就这样,我和我哥哥同时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在干校七八百个考生中,也就只有我们俩考上,而我们整个县城总共考上了六个,听说那一年在河南省的录取比率是200:1。 总体来说,我们77 级的大学生都学得很苦,因为以前的基础太差了。回想起往事,我总是感觉自己实在是很幸运。1977 年高考,应届高中毕业生录取比率不超过15%,我成为其中的一员。大学毕业后,我又考上了电子部54 所的研究生。后来我获得丹麦政府的奖学金去留学。 留学的时候,很多外国同学会跟我问起"文革"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们77 级、78 级的大学生有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是11 届的大学生。他们会说,"I understand",但我知道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的。 在感叹,我们这一群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因为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许是因为我的家庭处在干校那个环境,多元的文化让我比一般人的视野要宽广些;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小,没有任何家庭的负担,所以我比一般人更敢想敢做一些。但大多数被"文革"耽误的这批人,他们心理上的阴影比较重,也没有对未来大胆想象的勇气,但这批人干起活来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没有太多的浮躁,同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整理| 本刊记 王颖) 高考前:知青 王辉耀 像是在等着命运的宣判 口述| 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 1977 年高考前夕,我是一个已经在四川农村待了一年半的知青。考大学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时最羡慕的工作就是回城里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那时候书很少,但凡有纸张粘有文字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宝贵,都要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图书管理员可以一天24 小时泡在书的海洋里,各种各样的书任你挑任你看,该有多幸福啊。其实,那时候读书只是一种纯粹的乐趣,我并没有想着有一天,可以靠读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朦朦胧胧中,还是觉得这些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 1977 年10 月12 日,我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干完活回到小茅屋,听到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招生原则很简单: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没有任何地域和"下乡两年以上"的时间限制了。这的确让我很激动,机会来了。 报名的过程很顺利,但竞争还是很激烈。因为高考制度已经停止了10 年,这10 年中积累下来的精英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包括"老三届"。那时候,全国有1000 万知青、600 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大批的回城青年和城镇工矿企业青年。 从公布招生简章到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一开始复习就感觉到了压力。在离考试还有20 多天时,我决定改考英语专业。因为之前英文一直没有丢,而当年会英语的人很少,所以觉得自己还算有点优势。 1977 年l2 月初,高考开始。我寄宿在镇上一个朋友家里,一连三天考下来,人都要考焦了。考完后没多久,老乡来通知,要我们去镇上等候有无体检通知。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在等着命运的宣判。只要上了体检名单,希望就大了。 命运好像在开玩笑,宣布名单的时候,开始说没有我,后来又说有。不管有没有,我觉得都要马上赶到县里的医院去体检。临近体检时,我特紧张,听说一紧张就会血压高,于是有人建议多喝凉水或醋,说这能降血压。我悄悄地打开县医院自来水龙头大口大口灌了一肚子凉水,还喝了半瓶醋。 体检完以后,又通知考外语院校的要去成都口试。口试设在一个中学内,到了现场,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一个个都在叽里呱啦地讲外语,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完了。我以前虽学了不少外语,但口语没有锻炼过。好在我进了考场很镇静,老师先叫我读一篇中文,又读一篇英文,再用英文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口语考试的目的主要是要看你的口齿是否伶俐、发音是否准确。 终于有一天有人让我去取挂号信,取信时我看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名字,立刻感觉命运在发生很大的转变。我骑上我家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上狂奔起来。刹那间,楼房也不那么灰暗了,街道也变得明亮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就这样我成了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77 级学生。 那时候和我中学同届的本班50 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全年级800 多名毕业生,考上的也仅数名而已。这是当年"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观念的结果。我始终相信,命运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等到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我从小就选择了刻苦读书这个命运,最终我做成了上大学这件事情。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虽然它的到来有机遇的成分,但偶然中蕴涵着必然。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 高考前:北京海关员工 高中 我考大学的事上了内参 口述|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 我1968 年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上过良乡,下过房山,在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当瓦工,后来参军,先做警卫,之后到农场当会计,兼管养猪场和豆腐房。 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有一天,卫生科长找我,"组织上要送你上大学,你不要告诉别人。"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到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的手太小,离做妇产科医生的标准还差一点几公分。其实我在部队接生过57 头猪,挺有经验的,但人家还是不要我。 养了八个月猪后,我当上了参谋。在部队干了四年后我离开了,进入了北京海关。1977 年的一天,我的同屋舍友突然告诉我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愣住了,从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上大学这件事情似乎已经被我遗忘了。 直到高考还有12 天的时候,我才开始全面地复习。数学是我相对薄弱的环节,在我们住的胡同里有位管老师,他还在广播里讲过数学,当时他因为骑自行车摔伤正在家里养病,我就去求教于他。管老师非常好,花了五个小时,给我从初一一直复习到高三。 高考一结束,我异常兴奋地在广场上撒着手,蹬着自行车骑了三圈。因为我几乎没有不会的题,这次上大学看来是有门儿了。谁知道,到录取的时候,我却因为年龄问题被拒之门外。当时最热门的学校是外贸学院(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 可是招生的老师却告诉我,学校只招收23 岁以下的,而我已经28 岁了,年龄偏大,不适合学外语了,他们让我去读师范做老师。我非常气愤,因为招生简章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而且他们并不知道我自己在家里学外语,在海关天天用外语,并且我是英语、法语、日语一起学的。而且周围很多人都说我是当年的北京文科状元,但分数没有分布,我也无法核实这一点。 这时候,一位叫张冰姿的老师站出来为我鸣不平。张老师当时已经得了红斑狼疮,他却在大冬天走到当时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当天的值班编辑是保育钧,后来也成为我的至交。 当时,高考的作文已经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资料送到了《人民日报》。保育钧问张老师,海关有两篇文章被选入范文,里面有高中的文章吗?张老师说,有。那一年的高考题目叫《战斗在1977》,我写的是在海关的战斗历程。接着,保育钧写了一个内参,题目叫"状元落地"。 没想到,这篇内参邓小平看到了还作了批示:第一,公布高考分数;第二,适当照顾老三届。与此同时,张老师打电话找到了教育部部长李强,李强了解到我政治上是党员,成绩是当年的第一,不录取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28岁超龄了。"28 岁怎么就大了,还是收了吧。" 事后,商务部的政治部主任悄悄地问张老师,"高中的爸爸是谁啊?"张老师很生气,吐出三个字"周总理"。 虽然我的各门功课都接近满分,在报考外贸学院的学生中比第二名高出36分,但我跨进大学的那一步却是如此的艰难。 不过,仔细地回顾一下我的成长历程,我还是要比许多人幸运得多。假如我没有当兵,就入不了党,改不了家里的政治面貌,那我就进不了海关。因为在海关工作,才比别人多学了外语,也正因为这个才进了外贸学院。如果我没有进外贸学院,我也不会比别人更早地接触外部世界。 (整理| 本刊记者 王颖) 高考前:老师 左小蕾 我的卷子入了"另册" 口述|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我常常讲,我只上过小学和大学。因为我是"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赶上"文革",初中没有认真上过。高中也只算上了一年。直到后来上大学,才算再次接受系统的教育。 1972 年,我高中毕业就在自己的学校,武汉市39 女中里当起了毕业班的数学老师。因为原来的高二数学老师生病了,就让我代一段时间的课,没想到我上的课大受欢迎。就这样,我一直在39女中当老师,先是当了两三年的数学老师,后来又成为"两兵一团(民兵、红卫兵、共青团)司令",可以说我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那段时间,我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先是政工组主任,到中学书记、校长,再到区教育局干部??或者,升得更快一点,能够当个武汉市教育厅干部。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内心惶惶。当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大学。我报考的是数学系,一是我爸爸觉得我一个女孩子,不太适合考要求动手能力强的专业,用他的话说,我只适合"纸上谈兵",所以首选就是纯理论性的数学专业;二是我自己一直当数学老师,数学学得很好,考这个专业会比较有优势。 当时数学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上了大学才知道,当年报考武大理科的学生中一半报的是数学系。当年武大的数学系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老师都是数学界非常有名的专家。 说起当年备考,我要感谢我的几位老师。他们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都是39 女中的教师。数学、语文、政治之类的科目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复习理化时,我碰到了困难。 因为中学没有系统地学过,所以我的理化基础比较差,幸好有这些好老师帮助我。那时候我的物理老师经常出题目给我做,一晚上50 道题。 后来考试还算比较顺利,尤其是数学,我的卷子是入了"另册"的,当时95 分以上的卷子就放入"另册"。 考完试我被学校派到郊区劳动。因为学校领导知道我要走了,就没有给我安排下个学期的课。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干活,突然有人跑来告诉我,我妈妈来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 回到宿舍,我妈对我说:"你跟我回去吧,武大通知书来了。"那时我刚刚20岁,听到这句话,"哇"地一声,什么都不要了,挽着我妈就要走。 我妈说,你的东西呢?对,还要收拾东西。我把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跑到办公室跟人家说:"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走了。"说完,也没等人家表态,转身就走了。就这样,我上了武大的数学系,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武大当老师。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与我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有了机会,能否充分把握、充分利用,就要看自己的努力够不够了。 小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考到100 分才能打球,好,那我就努力考,5 门功课门门都是100;初中时大家都不去学校,只有我去,跟着老师一起写宣传文章,老师们都说我的文笔很好;上了大学之后,我一直是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大三时还因为这个原因被选去经济系学习,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整理| 本刊记者 罗影) *1977 大事记:8 月12 日,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0 人、代表党员3500 万人。会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情况,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 年最流行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977 年热词:"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术语随陈景润的故事在这一年成为一个热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经磨难的科学重获新生的重要信号,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 *1977 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1977 流行座右铭:"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成为当时青年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1977 流行歌曲:《金梭与银梭》成了最流行的歌曲。 *1977 畅销书:《青年自学成才丛书》。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