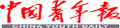|
|
|
山林变法:第三次土改艰难破冰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4日 02:37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刘畅 董伟 这是一场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变革,被称为“继农村土地承包后,我国土地使用制度上的又一重大改革”。这就是正在进行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今年3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我国林业中,属于山区农民集体所有的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37%。其中,人工林面积占全国人工林一半以上,林业总产值将近占全国林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山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9%,是我国的资源宝库和大江大河的源头,全国90%的林地、84%的森林蓄积量、77%的草场、76%的湖泊、98%的水能都集中在山区。在如此重要的资源宝库和地理环境中,任何改革举措的推行都是异常艰难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土地承包的带动之下,南方一些省份对部分林地已进行了承包。或许是出于“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担心,包到林地的部分农户出现了乱砍滥伐等情况。随后,这一改革被紧急“叫停”。近年来,以明晰产权、规范流转等为内容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又在悄悄展开。 中央党校调研报告引用林区群众的话说,这是继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土改”。 2006年5月18日,北京黄沙漫天,遭遇了今年以来的第14次沙尘天气。“今年的沙尘天气是3年来最多的。”有关专家表示。 5天前,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悄悄来到福建省三明市,与他同行的还有中央农业和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他们研究探讨的是“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沙尘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共和国的决策者和各级林业官员。 “我国18亿亩耕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什么43亿亩林地没有解决好现在的生态问题?” 这样的提问,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问到了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一直问到各级林业官员,成了中国发展的“必答题”。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接着必须面对的就是生态问题。即便是目标远大的“和谐社会”,也离不开“生态友好”。 当前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发生?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中存在的困扰和难题会给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20天时间里,本报记者分赴浙江、福建、江西、辽宁等地,对当地林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这场变革的图景和困境。 山林养活了谁 林改,遭到抵制 “先抵制,再敷衍”,江西省崇义县副县长胡晓平形容基层干部最初面对林改的态度说:“第三阶段才是——认真去改。” 崇义县是全国集体林模式的“红旗”,在国家林业局是挂了号的。如今,要分林到户,“红旗”会不会倒——县里领导这样考虑,想不通; 集体模式下,一个乡从山上得来的钱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一百几十万元。过去,把林子卖了,贴个告示就可以。如今,一旦农民有了林木所有权,这一切岂不是化作了泡影——乡村干部这样表示,更是想不通。 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彭宏松和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赶到崇义县调研时,在场的老同志及乡村干部,没有一个赞成改革。 不光县、乡、村干部们“不乐意”,基层林业部门同样也“不乐意”。林业部门人员多,但在编“吃皇粮”(财政开支)的很少,绝大多数经费都是从树上搞来的,改革等于敲碎了自己的饭碗。 对于省林业厅出面力挺改革,作为下属不好公然反对。有人说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听谁的 村委会里,身材魁梧的辽宁省桓仁县华来镇川里村党支部书记王春玉与村民挤在一条很窄的凳子上。他弹了弹手上的香烟说:“作为村干部,我想不通。” 王春玉想得很简单:集体的林子给了农民,村干部没有权了。再说,林子归集体的时候,川里村还有8个脱产护林员,一旦分给农民,这些人干啥去呀? 可村民罗胜春说,林子说是集体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谁真当回事啊?年年造林不成林,种下点树苗,“羊打尖,牛打叉,老母猪一来连根拔”(东北土话,意为牲畜糟蹋林木)。 本溪市林业局一位干部说:“村委会管的集体林也是全体村民的,分到农户,表面上看村委会有点损失,但却给村民带来实惠,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就这样,林子分到农户,8个护林员改成了“监督员”。 “干部林” “名义上集体所有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没份,广大村民既没有经营权,也没有收益权。”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对“集体林”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下乡调研,村民干脆管“集体林”叫做“干部林”。 什么意思?农民理解,就是村干部操纵,采伐收入开支全都由村干部说了算。林子犹如村干部的“小金库”,村上吃喝接待、补助补贴,全都在“集体林”中出。 福建永安一个村发生森林火灾,没有人上前救火,村委会主任拿着钱袋子吆喝:“谁上山扑火就给谁50元钱!”结果,村民蜂拥而上,村委会主任情急之下又大声喊:“别来了,别来了,没钱了!” 有人说,“山上着火、百姓观火、干部打火、领导发火”。 据说,这样的“干部林”,原来在福建集体林中,约占30%左右。 谁养活谁 说江西人“靠山吃山”有充足的道理:森林覆盖率列全国第二位,2/3面积是山区,2/3人口在山区,2/3县是重点林业县。 江西省林业系统15.4万人,其中全额拨款不足10%;自收自支的,倒占了80%多。 这80%的林业职工,都要从山林中收费来养活。因此,各地林地收费项目多得吓人:除了大宗的育林基金、农业特产税外,还有增值税、所得税、维简费、林业建设保护费、森工行业管理费、护林防火费、植物检疫费、森林资源更新费,以及县、乡、村出台的森工企业养老保险金、遗属补助、提取利润、乡村管理费、乡村提留、山价款等等。 该省平均各项林业税费征收比例接近50%,部分产材县甚至高达70%。有个县的杉木售价每立方米仅为205元,而育林基金却要550元。 2003年,江西省各地林业税费共计收取12.4383亿元,包括五个部分:税收,3.6556亿元;经国家和省政府批准的收费,6.4881亿元;市县政府出台的收费,4681万元;乡镇出台的收费1亿多元,村出台的收费7672万元。这些收费中,市县、乡村的收费都属于越权出台的乱收费项目。 由于经费没有落实,林业部门只能通过收费、罚款来增加收入。以武宁县为例,全县林业部门多达2600多人,负债6800余万元,林业行政事业人员352人全部靠收费养活。于是,林业工作站成了“收费站”,木材检查站成了“罚款站”。老百姓说:摆摊怕见城管员,种树怕见林业员。 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说:“几十年都是想着县乡怎么办,现在也该想想老百姓了。”断了县乡和林业部门的钱路,总归还得要给他们活路。在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支持下,省政府拿出2.9亿元让林业部门全部进财政,县、乡、村的损失部分补助,特别是干部的工资,也要各级财政负责。 江西是个穷省,全省财政收入250多亿。此次林改的不完全成本,已经超过5亿元。 艰难时刻,刘礼祖不得不放言:“林改不成,我自己向省委交帽子”。 突破之难 改变之忧 辽宁省林业厅厅长王文权要拿“干部林”开刀,也遇到了难处。因为村里的招待费、工资、补助以及村级债务,无不出自于此。 他下乡动员搞试点。一试,就试出了“麻烦”。村民们追着村干部问:“南山的林子卖出去了,俺们咋不知道?” 过去,林子卖给谁,村干部说了算。如今,要分林到户,村民一下子“明白了”。 辽宁有8933.9万亩集体林,其中,公益林(国家为保证生态严格控制的山林)占了大部分。不把公益林纳入,试点的面积将很少,失去改革的意义;把公益林纳入,风险又很大。 “要是搞乱了,对上对下,我这个林业厅长都无法交待。”王文权说。他让有关同志坐在屋子里想了100多个问题,拿到试点单位时,依旧“战战兢兢”,不停叮嘱:“遇到问题咱们商量”。 后来,看到没有因为林改引起一个逐级上访和乱砍滥伐事件,王文权松了口气:“把问题放在屋里想,太多了;把问题交给农民,解决了。” 分林到户 江西省崇义县,1381人的铅厂村,有林地5.7万亩,人均42亩,光竹子,就有288万株,是典型的林业村。得知林改的消息,村里马上分成两派。 不赞成的,多是村干部。他们认为,集体林场一二十年来搞得不错,贡献不小,没有必要分。而且,分下去林业秩序就要乱——1981年到1983年就曾经出过这样的乱子,滥砍滥伐,弄得山上“光头秃脑”。结论是:“不理他(上级),咱们村按照老一套干。” 可是村小组长和村民们不干:一定要分,而且保证不会乱。 结果,村里反复开会,村支书罗扬龙说,一年开的会比过去20年还要多。开会的大礼堂是原来毛泽东思想宣讲台,长时间没人去了,到处是灰尘。 最后,投票表决,38名村民代表,37名同意分。具体分法是:村归村,组归组,农户的归农户。 干部群众对“林权”认识不同 小小林权证,理解不一样。 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他担任永泰县县长,到一个曾经出了名的滥砍滥伐村搞试点。他把村民们都找过来,说今后种树是“谁种谁有”,而且,政府提供补贴。可村民无一应答。 黄建兴细问,原来,村民担心“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一锄头下去,明天未必还是自己的地。” 最后,黄建兴终于打动了一个杀猪的,他说:“我种!有什么补贴?” “种一棵树补贴10块钱。”结果,没有多久,三百亩荒山郁郁葱葱。从那以后,黄建兴每次乘车从那经过,都要停一会儿,看一看,想一想。 不过,出乎意料,等他当上林业厅厅长,再次下去调研发现,那位农民承包的山林已经被收了,山上的收入也归了村干部。 陈锡文是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有一次到农村调查,县领导陪着一起去,县林业局长跟着去了。到了村子,县林业局长就拿出了一个证书颁发给老太太,高兴地宣布:“你家种的林子已经成为生态林了。” 没想到,老太太接过证书就嚎啕大哭:“我白种了!如果是生态林,所有的林木都不许砍,那我投入为什么?” 可以看出,干部认为“产权”重要,可村民认为“处置权”才真的“重要”。 报告,来自中央党校 2006年3月,中央党校调研组拿出研究报告,题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江西省林业体制改革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提出,林业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林业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特别是占江西全省林地面积85%的集体山林,存在产权归属不清、权利责任不明、经营机制不活、利益分配失调、林农负担过重等问题,广大林农没有经营林业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林业的主动性、积极性。 针对“赶着农民种树,管着农民砍树”的工作方式,报告认为,明晰产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据统计,江西省林业改革开始之后,已有40万外出人员返乡务林。2004年到2005年上半年,共完成人工造林329万亩,为10年之最。其中,私营林不足三分之二。按照每亩投资200元计算,全省投入造林的社会资金4.26亿元。 此外,江西全省原有山林权属纠纷6万多起,争议面积400多万亩,林改期间已调节处理5万多起,面积将近300万亩,调节处理率超过80%。一些多年积怨甚至经地方法院判决都难以执行的纠纷,也借此解决。 给省委书记算的一笔账 林改非同小可。向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汇报时,辽宁省林业厅长王文权算了一笔账:辽宁100个县(区),有32个分布在山区半山区,其中,10多个就是以林为主。这些地方人均耕地不足1.5亩,却有人均林地15亩。做1.5亩的文章,还是做15亩的文章? 李克强表示,就算这个账。 对于农民,王文权也愿意算致富账:如果在林下种人参,“一土篮(人参)换一台桑塔纳”;再说种红松,一个松塔1元钱,一棵树20个塔,一亩地50棵树,仅此一项收入1000元。 不过,尽管有关官员向农民描述着致富的前景,在高寒的北方,相对于人参、红松、杨树长达10年、20年甚至50年以上的成长、成熟期,有些农民的目光是迟疑的。 44岁的辽宁农民张战军,花了一万多元承包了15亩林地,有树木400棵。这两年,他在树下种了豆子,光这个收入,一年就达到6000元。盘算着3年时间,靠种豆子就能收回成本,张战军认为“合适”。“这些树成材要20年,20年后,我64岁,正好可以用来养老。”他说。 林权证还能干啥 一天,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把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叫了去,问他:“你知道,林权证还能干什么?” 黄被问得有点发懵。卢展工给了他答案:“还可以贷款。” 原来,卢展工到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乡镇调研发现,当地的林农急需贷款,就把刚到手的林权证作了抵押,向银行贷款,居然成了。 卢展工是想告诉黄建兴,林权证就是农民拥有山林的财产证明,用它让农民获得致富的启动资金,何乐而不为? 实际上,从前依靠林权证贷款,并不容易。因为银行原本没有这种金融产品,加上农村贷款本来就让银行家们顾虑重重,风险也很大。 在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和国家开发银行永安分行行长协调,还从市财政拿出300万元作担保,要求允许林农拿林权证贷款。双方还成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终于促成此事。事实证明,此举双赢,至今无一呆坏账。 陈锡文的担忧 “作为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山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仅把它确权到户,坦率地说,摆脱不了小生产状态。”陈锡文一番话,矛盾直接指向林改政策,对于林业官员有点“振聋发聩”。 “林木的生长状况,实际只有林木的生产者最清楚。而你给他的配额,到底是否适合当地实际情况,我觉得非常值得探讨。” 陈锡文所说的配额,是指政府规定采伐量、颁发采伐证。对此,陈锡文委婉地表示,砍伐制度的管理是个很迫切的问题,严格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否只有通过政府来规定采伐量、发放采伐证呢? 2006年5月,中央农业和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人、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林业官员共聚福建省三明市,除了表示看好林改的前景,有关人士也认识到,这次改革不仅涉及到山林产权明晰问题,也涉及到政府有关部门既有权力和既得利益的调整问题。 明天会怎样 林改的地域特色 张炳海一家7口人,生活在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以前一直靠种植茶叶和农田为生。1991年,他在20多亩山地里种下了雷竹,4年竹子成林,家里的收入一下子从近一万元变成了十五六万元。 如今,他一次性承包100亩竹林,时间20年。最近两年,竹林产值每年超过18万元,加上竹笋的收入,自家楼房已经400平方米,空调4个、电视3台、还有农用车3部。 南方的竹林,让人羡慕,但北方的农民,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面对着耐寒、生长周期漫长的树种,想获得不错的收入,很难。 44岁的朱广胜站在树下,面露难色,充满心事。去年夏天,这里进行了林改,100亩山林进入了他的名下。可是,这些林子是国家的公益林,根本不让砍。 拿到了林权证,绿色的,还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上面写着41年的使用权,他说自己“像做梦似的”。 可是,林子在自己名下,又不准砍伐,他就发起了愁:“山林都分给自己了,不能瞎了啊,究竟干点啥好呢?” 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支书夏玉云说,村子位于太湖源头,全是森林,没有农田。过去,靠山吃山,村民们整日忙着砍树、烧木炭,结果,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频发,老百姓也没富起来。 偏偏,白沙村的山林有个名字,叫龙须沟,与作家老舍笔下那个环境恶劣的地方同名。 1990年,白沙村禁止烧木炭,控制采伐量;1998年,白沙村采伐量为零。 不砍树了,村民靠什么?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本诺沙来到白沙村,他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龙须沟呢,可以叫生态沟,开发生态旅游。这样,他们拿出7000美元,送临安市林业局高工王安国去广州参加“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培训班”,并对白沙村乃至临安市的生态旅游进行研究。 王安国从广州回来,就给村民们开展“利用森林景观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培训”,村民们抱着好奇的心理听课,却没人相信游客会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来。 有的村民说:“老王平时不吹牛,但这件事就是在吹牛。” 还有的村民说:“上海离我们好几百里地,那里的人要是来旅游,我爬给你看。” 林权证发到手之后,也随之进行了“流转”——全村2000亩山林,包给了外来的老板,一年支付2万元,并且,一包就是50年。 外来的游客逐渐增多,有的农民“想不开”:“包给老板,就给那么点钱,这不公平。” 随后,王安国引导大家:“不要去抢老板的钱,而要想办法赚外来游客的钱”。 就这样,白沙村的村民家家户户办起了家庭旅馆,发展农家乐,一时间,生活变了——44岁的吕建中,20多年前砍树被压成残疾,全家生活困难。这里发展旅游业后,他利用搬迁补偿盖起了一座3层小楼,24个标间,日接待能力50人,旺季时,一天就挣2000元。如今,每年家庭旅馆的收入就有8万元。 从砍树,到看树(利用树发展旅游),经历林权制度改革的白沙村人似乎找到了从相互矛盾到相互依托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砍伐的矛盾 “我们村的树是30年前种的,现在,到了个人手里,想砍伐下来,再栽上新树,可就是没有国家给的砍伐指标。”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北洼子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才说。 对此,铁岭市林业局局长孙彪说:“(我们这里)农民的砍伐期望值与国家计划指标有矛盾,林改之后,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争取砍伐指标,让成熟的林子在农民手里变现(金)。” 当地林业官员说,适度砍伐,也是林木更新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希望“十一五”期间,农民要砍伐变现(金)的,都能实现。 而宝力镇林管站面临的现实是,全镇应该砍伐31万棵,蓄积量25万立方米。每年,农民申请砍伐量是3万至4万立方米,而砍伐指标只有4000立方米。 因为指标有限,有关官员就“按质量分,残次林优先”。 《森林法》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如今,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山林,随着林改,走进了农民家庭,有关人士担心,如果不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将使此次改革的成果和效应受到重大影响。 如同过去的每一个重大举措一样,林改,也将接受历史的检验,是成是败,还是由时间来回答吧。
【发表评论】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