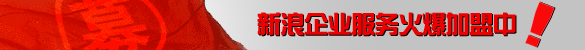迟到的婚纱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8日 18:08 经济观察报 | |||||||||
|
采写:刘小萌 口述:张玲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一 我出身在一个资本家家庭,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三年级,迎接少先队十年大庆,要选代表上人民大会堂,还有毛主席接见,听说这消息,别提多振奋了。同学们都以为会选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清楚,回家时我爸正挨那儿坐着。在这之前,人民大会堂刚建完还没开放的时候,组织工商业人士参观,我爸也兴冲冲地去了。回来以后还给我讲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钉子鞋,怕把地板碰坏了,干脆就提了着鞋,光着脚走了一圈,特新鲜。我当时还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不让我去。”等到我告诉他“去人民大会堂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时,我爸看着我笑着说:“没关系,长大当上劳动模范就能进去。” 1967年我在中学闹串联回来,学校说要“复课闹革命”,接着给毕业生办学习班,动员上山下乡。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最后报名去了内蒙土默特左旗,那是1968年9月。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她分给你点工分那不可能啊。 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的十个鸡蛋,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的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去的,好像内蒙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过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救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刚小,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本来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故我。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过月子有吃一百个鸡蛋的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十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般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种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们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玲了。 71年秋天有了点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几个孩子上。“文革”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人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 二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二个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80年5月我到厂子报的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一直到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8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营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三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高的跟个低的,大家一个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的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白毛风天遭的罪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吉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80、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证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两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的挺容易,到我这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8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呆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我们原来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我是在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踏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的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你没在那盖房,拆迁也没你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三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为了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单位他不给你落户口。我开了证明,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的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个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就决定回内蒙。我是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个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们就没有欠帐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 。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四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又落实回来,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那间公房到底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70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寄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 。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标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 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300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映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 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也曾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功能强大 |
| 戒烟让男人暴富项目! |
| 韩国亲子装2.5折供货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联手上市公司赚大钱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