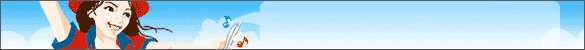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作者:王怡
《物权法》每一回审议稿的修订,都会引起舆情的热烈关注。法律尚未通过,成效已经出来。
什么叫“物权”,多数城市居民对这个不久前还显得陌生的概念,现在都可以议上
几句。《物权法》是落实《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法律,是《民法》的奠基。
《物权法》其实是一部技术性很强、也相对较抽象的法律。也许人们有太多急迫的要求了,总赋予或者希望《物权法》能解决更多更具体的问题。于是在关于《物权法》的一些争论中,理论诉求与现实诉求构成了一种立法的矛盾。一方面法学家和立法者们希望弄出一部能管一百年甚至更久的抽象的物权体系,另一方面民众却有着更多具体的事情希望《物权法》能够涉及。人们似乎正在把以往对行政权力的盼望直接转移到立法上去。
在某种民主化的观念氛围里,这些想法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使立法者和皓首穷经的民法学者们必须迁就妥协。譬如小区的绿地、车库该归谁所有,居民能否在农村购买宅基地,甚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领导人导致资产流失怎么办,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又怎么办等。《物权法》对此可以照单全收,但却可能因此伤害《物权法》的稳定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
再如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要不要分类保护的问题,则是专家意见与政府主流意见相互迁就的过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分类,要不要一起保护,而在于真正的物权制度,只可能是从私人财产权开始的。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在物权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所谓集体和国家财产权,无非是私人财产权的集合形式,通过契约、公司、股份合作、合伙、结社等方式的集合。在《物权法》中分列三类财产权,必然给物权法理论框架造成漏洞。
其次,这也带来另一个新问题。就是立法过程一旦开始走向公开、透明和民主化,各种反对意见就会频繁出现。这时候立法程序如果不能获得更坚实的民意基础,进一步推动选举和投票的民主化,立法者拒绝反对意见的能力就可能下降。而不能拒绝意见,不见得就比不能接受意见好多少。
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年来立法过程的日渐开明,但也看到了在这种开明模式中,政府主流意见、专家意见和大众意见之间的某种尖锐对峙。
最后要说,虽然《物权法》对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确有深远意义,也是我们缺乏的,但它的意义仍然被夸大了。这种夸大含有一种危险的暗示,一个遥远的例子就是罗马法。学者们对《物权法》乃至民法典的制定,背后都怀着一种仰慕罗马法的情结。但罗马法后来的悲剧恰恰来自这种对私法的过分夸大。
对国家权力而言,私法仅仅是一个被容许的事实,不是一个针对权力的戒条。如果市民社会是一块草坪,《物权法》回答的是能否种草,怎样种草,草坪可以发展到多大。但惟有公法才能成为草坪周围的栏杆。没有私法,不能发展出成熟的草坪。但只有私法没有宪法如罗马帝国,草坪仍然可能被任意践踏。
只有《宪法》和《行政法》才构成针对权力的戒条,才能为私法内的自由举行成年仪式,真正防止我们的财产权被侵犯。但这恰恰是当初罗马帝国所缺乏的。当不受限制的皇权日益膨胀,一度辉煌的罗马私法很快便被吞没,罗马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那种过分强调靠《民法》的发展,靠《物权法》等私法的成熟就可以保障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其实是幼稚的。
财产权和契约自由一样,不可能独自存活于私法内部。人类法治进步的历史,就是以公法保卫私法的历史。这也是英美法系不对公法私法作刻意区分的缘故。只有当权力被有效制衡,被法律捆绑;只有当财产和契约的概念从私法进入公法,从物权走向人权,成为凌驾于国家权力之先的一个初始来源,一个自由的、生生不息的私人财产的空间才可能如鱼入大海、鸢飞戾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