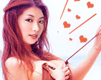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Cees Veerman 荷兰农业部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依然在问这个问题:谁将养活中国?现在答案已无庸置疑。人均每日可得食品数量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00卡路里提高到了2000年的3000卡路里以上。直到最近为止,中国实际上一直是食品的净出口国,现在依然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国。农村人口的40%以上现在不从事农业,而且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超过1亿人口转移
到城市寻找工作。同时,远比这1亿人更多的人已经脱离贫困线。
这些变化的起始点是1978年开始实行的农业结构改革。农业因此成为中国在近数十年发展的发动机。中国的巨大发展不应只归功于组织的大规模改革和政策变化,新科技的应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土地的利用。中国正在上演伟大的事情。
中国和荷兰差异巨大,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时。中国产量最大的农业区位于大河沿岸的肥沃谷底和三角洲,而荷兰也位于一个肥沃的河流三角洲上,城市化水平很高,有着因人口-土地比率产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因此就何种形式的农业发展能最成功地对国民经济、国家繁荣和城乡人口福利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交流知识和经验。
“多哈回合议程”应对
我并不认可在荷兰经常听到的那种说法,即随着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将转移到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我认为西方拥有的高科技农业针对“第三世界”的传统农业享有经济优势。我认为其实是工业以及可能紧随其后的服务业,更可能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从西方世界退出。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迹象。
这里我引用《经济政策》杂志2005年4月的一篇文章,在其中鹿特丹的Erasmus大学和Wageninggen大学的研究者说明,可以通过平衡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自由化来从“多哈发展议程”中获取最大可能优势。关键是,这一自由化不应只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或它们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化才能使它们获益最多。
我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并相信它们能从南北贸易自由化中得到好处,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的农业竞争力最弱,这一情绪可能最终变为巨大的失望,尤其是在它们的经济路径错误的情况下。为发展合作而工作的人们尤其应当体会这一点。
但这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此不应努力发展农业。它们应当继续投资于更好的基础设施并更好地定价,既不是人为地定价过高来使农民受益(西方在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做),也不是人为地过低(这一情况经常发生在发展中世界)。在荷兰,在城镇地区近郊发展的农业有最好的机会。我相信这同样适用于贵国,高科技、密集型、市场化的农业能快速为城市提供食品和高质量的乡村环境。
上海附近的武进县开拓地项目是一个例子。这是武进县和Wageninggen大学及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正在建设的这块开拓地能实现可持续的密集型农业和严格的市场结构,结合自然管理,并可供城市人口消遣。
城乡发展平衡
中国在近几十年成功地为宏观经济发展创造了推动力,这一力量部分来自农业领域的重大改革。中国放弃了集体化方式,给农民更多空间发展它们的创业才能。发展的最初推动来自农业是很自然的。
但这一最初推动已经丧失了后劲,到了从其它领域寻找另一推动的时间。我切身感到,中国的城市有很大的潜力。但这些新力量可能是如此强大,以至出现单向发展的可能,而这将使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危险是过多的人们将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因此很多研究在关注收入和财富的地区分配。
为了找到这一平衡,西方国家经常利用价格政策或者直接转移支付来实现城乡收入的重新分配。尽管不可避免有些挫折,这一政策效果还是非常成功的。财政资源帮助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并变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经济部门,而且很明显,其中的劳动力已经远少于50或100年前。但这一转变进程是顺利的,冲突相对较少。农村地区没有出现人口锐减和情况的突然恶化。首先是雇工,然后是家庭工人,最后主要是小农,都从农业中消失了。
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其基础是:农村人口的良好教育和培训;为现代化提供帮助并为农民提供所需知识的研究与公共信息的基础设施;结构合理的所有权关系和良好的信用体系;电力、水和道路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使现代科技的使用和人口与商品的流动成为可能。
城市地区的扩展实际上使城镇相互接近:农村地区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城里工作的同时继续与其家庭一起在乡村生活。它们从城市获得的收入支付于家乡,从而强化了农业经济。
在中国的乡村,人们有足够的头脑和商业技能来成功实现这一点。但当然,要有一个基本的基础设施。
对于欧洲一些人口不够密集和城市化不够高的地区这一模式不大适用。在一些国家农村人口的减少是无法组织的,即便投入大笔的钱,如“欧洲结构基金”。这也证明了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关键性。来自爱尔兰、德国的法兰德斯与威斯特伐里亚的打工者带回给家乡足够的资金来加速那里的现代化进程。
结构政策与社会责任
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价格和收入支持可以控制城乡发展的平衡。我理解贵国正在经历这些可能性。但我也强调了教育、研究、公共教育和结构政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在19世纪下半期荷兰将教育、研究、服务业扩展和结构政策作为发展重点。我们做出这一决策时所想的是中国的名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我们继续重新采取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二战后这一政策在欧洲范围内继续。
但欧洲的政策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欧洲的人们越来越迷惑,为什么我们仍然实行单纯为了农民的收入转移,为什么不是为整个农村地区,或者将其作为对提供特殊农业服务的奖励。来自WTO的压力在加速重新审视农业政策目标和工具的进程。这几乎自动地将结构改革政策和更好的市场导向问题提到了前列。欧洲农村地区资金投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实际上被用于这种结构改革进程。
另外经常很必要的是,使传统组织结构适应新形势并取消一切障碍。从一些研究中我知道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交流意见和经验。
使结构改革成为必需的一个变化是,供应产业、加工业和农产品零售业规模和集中性的加强。西欧农产品的很大一部分通过一些特定的超市链或其他销售渠道提供给消费者,它们通常国际化运作。园艺业和农业尽量适应这一形势,但这也经常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重大和痛苦的改变。
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加工业和零售链对产品和生产方式需求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是食品安全要求。
“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表明私人领域的需求往往比政府高得多。Ahold、家乐福、Tesco和麦当劳不希望看到它们的声誉因为销售不安全食品而受损。所以它们要求供应商实现高标准,而且由它们控制实现这一标准。不能达到这些标准的供应商失去供应权,即使在它们的本国。
我认为这是帮助农业改革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并不是要不厌其烦地安排农业的全部,而是创造条件使农业能更容易地回应新的趋势。私有企业在为食品安全制定自己的条件,这与其他因素一起造成公共与私人责任平衡的改变。我们作为政府代表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行动。去年荷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我在农业部长的非正式会议上提到了这一点。
这不只是关乎食品安全,也影响食品质量的其他方面。加工业、销售链和消费者不喜欢以一种伤害动物或伤害环境的方式制造的产品,或者一种缺乏社会责任的方式或者违法方式制造的产品。
我认为始终在WTO中让人们关注这些问题是我的义务,同时考虑我们如何帮助较弱小的行业适应新的市场要求。可以通过能力和结构建设来帮助弱小行业,我们不止在荷兰这么做,而且更多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和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这些行业本身合作来这么做。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因为这些新要求而使得大批农民被排除出全球市场是一种同样威胁到中国的危险。这将对贵国农业地区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是另一个中荷可以交流知识与经验的机会。
(本文为荷兰农业部长Cees Veerman 6月3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演讲,荷兰驻华大使馆授权本报为发表本文的唯一中国媒体,本报记者刘波根据演讲稿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