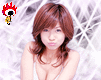商务周刊:重建能源部 关键在采取何种管理体制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0日 16:42 《商务周刊》杂志 | ||||||||
|
重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各方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究竟采取怎样的能源管理体制,成立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却一直还处于争议之中。分歧不仅来自于市场化或威权化的政府治理观念的不同,也来自于各部门分割权力过程中的争夺 □记者 王强
每年3月,对于中国第一煤炭大省山西来说,应该是喜庆的月份,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全国煤炭需求紧张,大量的需求极大拉动山西煤炭生产。一吨吨“黑金”运出去,换回的是数以亿计的人民币。但2005年的3月,笼罩在这个产煤大省上空的却是死亡和悲哀的阴影。 3月9日,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岭底乡香源沟煤矿二坑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9人、受伤5人。10天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白塘乡细水煤矿再次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并波及相邻的康家窑煤矿,共造成72人死亡。短短10天之内,101名矿工丧身矿井之下。 在过去的几年中,矿难和死亡在山西乃至整个中国都不再是什么新闻。伴随着一个个生命的逝去,关于重构中国能源管理机构的议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几年过去了,这个备受争议的机构仍然还是“空中楼阁”。 一个对能源没有战略认识和长远规划的国家,在各种能源灾难、无序管理和能源短缺中疲于奔命和被动应付,似乎也成了必然的宿命。 带血的“黑金” 从晋北重镇朔州到平鲁区,大致还有30公里的路程。沿大运公路前行,天与地都被灰黑色的东西所笼罩。公路两旁的丘陵山地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煤矿和选煤厂。一辆接一辆的运煤“巨无霸”卡车呼啸而过,刮起一股股呛鼻子的煤灰。 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朔州市主要煤炭生产都集中在平鲁区,“这些年,煤炭给平鲁带来了财富,但也把整个环境给毁了”。 发生瓦斯爆炸的细水煤矿距平鲁区委、区政府仅5公里之遥。记者赶到细水煤矿时,矿井旁的办公区依然完好,一尊“拓荒牛”雕塑仍然昂首屹立,墙上的“安全生产规则”清清楚楚。虽然矿难发生过去已经20多天,但矿井上的瓦砾和惨状依然触目惊心。遍地是砖块、石块和水泥碎块;巨大的绞车房被炸得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铁骨架;巨大的矿架倾倒在一旁,一座二层小楼被掀掉了大半,整个矿井已经面目全非。倾斜而下的矿井被崩塌的瓦砾封死,站在矿井口边的瓦砾上,可以听到井下哗哗的流水声。 细水矿难暴露出来的问题涉及“以包代管”的地方煤炭管理模式、被各方利益消解的安全监察制度。此外,利益驱动下的无限度超产是矿难背后更直接的原因。 平鲁区一位对煤炭生产很熟悉的资深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平鲁区号称全国第一产煤大县,煤炭行业是全区的支柱产业,以2002年为例,煤炭收入就占到了全区财政收入的75%以上。尤其随着近两年能源紧缺,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利益驱动导致大量的小煤矿出现。 细水煤矿就是一个年产只有15万吨的小煤矿。根据平鲁区煤炭工业局官方的统计,全区最多的时候,煤矿达到了115座,近年关井压产后,减少到了67座,但其中国有矿只有8座,其他都是乡镇承包煤矿。 近两年煤炭市场好转,使得不论国有矿还是乡镇矿都在超限开采。“在利益面前,很少有人再关心安全问题。”那位人士说。 细水煤矿设计能力是年产15万吨。矿主王应被拘后交代,今年细水矿追求的目标是年产40多万吨。据悉,为追产量,细水矿在井下同时布置了6个工作面,大巷开皮带运输机2部,开刮板采煤机2部。按业内人士估计,这样的生产规模年产量可达60多万吨,相当于产能设计的4倍。技术专家分析,像细水煤矿这样的条件,通风简单,如此超产开采,极易造成瓦斯积聚。 超限生产不单单只在平鲁区存在。公开的资料显示,2004年,山西全省产煤超过4.9亿吨,同比增加4224万吨。其中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完成2.25亿吨,同比增加3189万吨;地方县以上煤矿完成8536万吨,同比增加926万吨;乡镇煤矿完成1.8亿吨,同比增加109万吨。2004年,山西省完成煤炭出省销量3.5亿吨,同比增加5817万吨,增幅为19.57%。 “通过平鲁,你可以看到中国能源生产和能源管理的分散、混乱与无序。”山西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坦言,“管理缺位、带血的‘黑金’、污染的环境,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后能源部时代的山西 3月13日,细水矿难发生前几天,国务院安委会煤矿安全第二检查组一行7人先后完成了对同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和晋煤集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从3月1日就开始的这一大检查发现,超产的不仅是细水煤矿,上述大型煤炭企业2004年超产情况同样严重。其中同煤集团超产700万吨,山西焦煤集团超产470万吨,阳泉煤业集团超产780万吨,晋煤集团超产473万吨。 这些企业在2005年的生产计划中,也都表现出了相当严重的超产倾向。2005年,大同煤炭集团计划生产煤炭4425万吨,相当于计划超产871万吨;山西焦煤集团计划生产5105万吨,相当于超产27万吨;阳煤集团计划生产2747万吨,超产737万吨;晋煤集团计划生产2830万吨,超产860万吨。 如果没有发生3月19日的矿难,或许这些煤炭企业的超产计划将得以顺利实施。但美梦由于细水矿难的发生被嘎然而止。3月22日,全国再次掀起安全整顿风暴,山西4000多家煤矿只有672家正常生产,大部分煤矿停产整顿。 在供求紧张的刺激之下,煤价面临上涨压力。“今年煤炭肯定还要紧张。”4月15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助理巡视员侯文锦刚刚从北京参加完世界能源大会回到太原,他的另外一个职务是山西省煤炭销售办公室副主任。他注意到,山西省今年一、二月份煤炭调出量是每天1.35万个车皮,到4月份这一数字只有1.1万。“山西省面临双重压力,”他说,“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为全国提供煤炭,保证生产,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两难。” 这种两难的造成,有其历史原因。作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长期研究山西省煤炭经济和中国能源问题。他介绍说,1978年,中央在山西开始建设国家能源基地,当时因为国家能源非常紧张,为鼓励山西多挖煤,提出了“国家修路,山西挖煤”、 “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鼓励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虽然缓解了能源压力,但也造成煤矿构成十分复杂,并一直影响至今。 1993年,国家能源部撤销,煤炭生产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山西省5大重点煤矿也下放给省里。“这对山西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王宏英也注意到,“有水快流”的思路更加泛滥,大矿小矿一起上,造成矿点多,规模小,管理难度非常大,在199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山西有1万多个大小煤矿。 由于煤矿下放到地方,政府从管理到资金都缺位,有些乡镇煤矿干脆转包给了不具备条件的个人,在安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变动和多年对山西省煤炭生产开发的忽视,也影响了行业的整体提升和安全生产能力。 1990年代,国家煤炭开发战略逐渐向西移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正好遭遇我国能源供给相对缓和的阶段,而且随着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对煤炭的需求量减少,特别是到1999年的时候,煤炭的供给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山西整个煤炭行业举步维艰。 “这其中当然有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但是与国家在煤炭开发过程中不考虑供给需求也有很大关系。如果当时国家能够通盘考虑能源开发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煤炭供应不紧张的情况下,减缓西部煤炭的开发力度,当时山西煤炭行业窘迫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王宏英还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对山西煤炭开发的重视力度也不够,包括一些煤炭开发的高新技术项目,比如说煤变油项目、煤的地下气化项目,这些能提升整个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项目几乎没有在山西布局,“这对山西整个煤炭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山西煤炭始终处于一个比较低层次发展水平”。 由于国家统一的能源管理机构的缺位,国家对山西省的投资在近年来也大幅度降低。从1978-1998年,国家大概给山西能源工业的投资是900多亿,这900多亿又带动了地方对能源工业的巨大投入,使山西省能源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1998年以后,除在西电东送的北通道建设外,国家对山西的投入大幅度降低。 从2003年开始,能源短缺问题凸显,煤电油运紧张,在长期能源管理滞后和国家统一规划缺位的情况下,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在山西疯狂超产过程中以矿难等激烈形式得到释放。 “今后20年到30年,中国的煤炭行业离不开山西,中国的能源也离不开山西。”王宏英说,从山西来看,迫切需要国家成立综合的能源管理部门对能源开发利用进行综合协调、综合布局,解决山西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 行同虚设的安全监察制度 针对矿难频发,不能说政府无所作为。在中国,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近几年来,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和三令五申早令老百姓司空见惯。 在安全生产方面,政府管理似乎并不缺位。安全监察制度和机构也不是不健全。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更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 国务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对煤矿安全生产的监察制度规定得比较完备,其中已经包含了安全生产的预警机制,对煤炭业安全管理的“关口”实际上也是前置的,“事先建设,事先监督,事先介入”都有相应规定。而且各地煤矿安全监察部门也并非“由煤炭系统设立”,大中型矿区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也是由国家和地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设立的,与煤矿和地方政府分离,并不存在“左手”监督“右手”的问题。《条例》也赋予煤矿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很大的执法权力,包括行政处罚权和紧急处置权。 其实,细水煤矿的问题早就引起过有关部门的注意。去年10月19日,山西省煤矿安监局朔州市安监站就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细水煤矿下达过执法文书,要求其停产整改;11月5日,平鲁区人民政府又责令该矿整顿。但细水煤矿对两次执法令却置若罔闻,仍夜以继日不间断生产。 近两年,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各市建立健全了监管模式,形成“人盯人,不漏网”的严管格局。记者在朔州市平鲁区煤炭工业局了解到,煤炭工业局和安监局两个部门全部在编人员117人,他们为全区67个煤矿共75个矿井派出了70个驻矿安监员。平鲁区安监局还做出了严格规定,驻矿安监员每月驻矿时间不低于22天,入坑次数不低于15次,不准弄虚作假、私通人情、包庇纵容。 平鲁区还制定了《驻矿安监员工作职责》、《驻矿安监员十二条权利》、《驻矿安监员十项工作纪律》等三项制度。驻矿安监员被赋予监察煤矿安全生产方方面面的权力,并可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违规违章操作的行为依法采取检查、制止、责令停产和罚款等手段。 但驻细水煤矿的安全监察员在事发被拘后称,今年2月份仅仅下过2次井,3月份1次也没下。从平鲁区安监局提供的今年2月份安监员考评情况看,70多名驻矿安监员平均驻矿时间只有15天,最少的只有6天;而下井平均次数只有7次,最少的当月没有下过1次井。在这张表上记录的细水矿驻矿安监员朱义下井时间却是5次。 可以说,遏止矿难发生的有效措施早已规定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至少从制度上已经不存在太大的缺陷。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甚至以撤职处分为警惩,各级政府官员也不能说不重视。但在一次次残酷的灾难面前,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无论是行政化权威,还是安全监察制度,都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机构重建日渐紧迫 1993年,在中国能源管理历史上,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能源部被撤销。直到今天,中国再没有设立部级以上的综合能源管理机构。 “能源部撤销后,煤炭部和电力部重新组建。国家能源管理走向了分散化,尤其是能源的宏观管理大大弱化。”今年已经66岁的王家诚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直致力于国家能源战略研究。他认为,能源行业的相关职责分散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电监会、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突出的问题是管理分散,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过于分散的能源管理模式,特别是缺少战略管理,难以适应能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能源自身发展的规律。 “从能源管理的内容和范围界定来看,目前各部委的能源管理职能是以管理对象界定。”他对《商务周刊》说,“决策者把能源工业等同于其他加工工业或制造业,能源的基础地位被削弱,综合全面性和长远性的能源战略管理很薄弱。” 王家诚一直强调,能源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门,特别是它涉及石油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建设和运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必须由国家监控和统一管理。因此,为了达到能源和经济的低耗、高效以及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能源监控和综合管理,他建议,必须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以能源战略管理为核心的能源监管体系。 2002年6月11日,路透社播发的一篇题为《中国需要集中的能源政策》的报道,也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在中国解散能源部将近10年之后,它如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监督能源部门发展的中央化管理机构,“中国需要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和全面的能源政策,应该照顾到煤、油、气、电和再生性能源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以项目为基础”。 近年来,类似重新构建中国综合能源管理机构的呼声此起彼伏。 “1993年国家撤销能源部,是国家对当时能源供求形势的一个错误判断。”王宏英认为,在1990年代初,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国内经济形势经过20年发展后,也出现了自然的周期性波动。在宏观形势判断上,决策者认为经济会继续走低,基于这种判断,当时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已经基本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国家没有必要再保留综合性的能源管理部门。“现在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进入工业初级阶段的国家,能源的供应远远达不到经济的增长需求。”他说。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发展速度加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种判断得到了验证。能源短缺问题实际从2003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出现,到2004年则发展得更为明显和尖锐。总的表现是缺电、缺煤、缺油,媒体称之为“煤荒、电荒和油荒”。而由于能源短缺,煤和油的价格自然高企,这也对小媒窑屡禁不止、非安全生产顶风做案提供了利益刺激。 2004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49%。但因为缺乏总体战略,没有石油储备体系,在国际油价浮动变化中,中国陷入了“买涨不买落”的怪圈。在缺乏立法和能源总体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历经10年才启动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但未来石油储备基地由谁管理、巨额资金由谁承担、储备油由谁支配却仍然存在疑问。 2004年,中国能源短缺问题越发严重,这也引起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到能源管理这一个重要问题。自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能源工作汇报已经不下三次——这是前所未有的。 “成立能源管理部门,核心就是要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保障能源的安全生产和有效供给。能源短缺是客观的,但是可以通过综合协调发展来有效解决,比如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煤、气、水、电等的协调发展,必须有一个综合协调部门规划协调。”王宏英说。 他还注意到,目前国家宏观形势与10年前已经大不一样,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能源安全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能源问题,已经和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王宏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层面上没有一个国家统一的、具有权威的能源管理机关恐怕很难再适应发展形势。 “国家对能源管理机构的重建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的话,恐怕不单单影响到能源工业自身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会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他斩钉截铁地说,“成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综合能源管理部门已经是形势所迫了。” 而基层的态度更直接一些。在山西采访中,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也向记者建议恢复煤炭部或能源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他问道:“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现实的选择和利益调整 在重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问题上,各方面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究竟采取怎样的能源管理体制,成立一个什么样的部门,一直还处于争议之中。 从现有的观点来看,有四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成立能源部,二是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三是成立国务院能源管理办公室,四是把发改委能源局提升为副部级单位。 但不论哪种模式都意味着职权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在既有的利益格局面前,每种选择都需要有些部门和利益集团做出让步和权力让渡。尤其是,历史上中国能源管理部门在经历了机构设置上的历次分分合合以及变革后,决策者在选择上变得更加慎重。中国能源行业频繁的行政机构改革也使得今天的各种关系越发复杂。 1988年,中国第一届能源部成立,当时除了电力行业直接并入能源部以外,石油、煤炭两个部门都对能源部的成立不支持。能源部成立没多久,原煤炭部二十几位副部长甚至联名上书要求恢复煤炭部。1993年,能源部撤销,煤炭部恢复。1998年,煤炭部降格为煤炭工业局,2001年煤炭工业局再度被撤销。在各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也比较混乱。有的省保留了煤炭厅,有的保留了煤炭工业局,有的只在各地经委或发改委下设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 煤炭部撤销后,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关经验的考察和研究,1999年国家决定成立煤矿安全监察局,采取垂直管理。但是,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成立后,却出现了诸多“乱象”。 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又粉墨登场。两者之间在很多时候并不合拍,在利益面前争夺权力、在责任面前互相推诿的局面时时出现。 主张重建能源部的呼声在1999年就有人提出,当时的建议是成立一个制定政策的“能源部”和一个能源部管理的执行政策的“能源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下再设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在政府序列之外。这显然是借鉴了美国的能源管理模式。 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一份名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组建统一的“政监分开”的政府能源管理部门。 但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有关人士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国家现在在电力方面有电监会,在煤炭安全方面有煤炭安全检查局,再组建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管有必要吗?”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能源专家认为,显然,重新成立能源部最大的困难在于部门之间的职权分配和调整,在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下,平衡各部门利益是很难的。 2003年的机构改革之前,除了能源部,呼声比较响亮的还有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持这种建议的是王家诚。早在2002年,他就提出,要从统一和加强国家一级能源管理机构着手,强化对能源的综合管理和调控能力。建议中央重建国家能源委员会。他进一步的构想是,在国家能源委员会内,按中国传统的归口管理模式可分设煤炭、电力、石油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几个行业(或领域)组,分别进行该行业(或领域)发展范围内的战略管理。同时,要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能源分级监管体制,特别要加强省市区一级能源监管机构的建设。 但到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出人意料的是,出台的是更为等而下之的委管局级机构,在国家发改委下设立了一个只要30人编制的能源局。 能源局的诞生是当时国内利益格局妥协的结果。有专家认为,其实在2003年成立能源部或能源委的条件并不成熟。公开资料表明,三大石油公司中部分上市公司2002年的净利润达到了702亿元,缴纳的各种税收也超过了600亿元,加上电力企业,在国有企业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也在1/3以上。如果成立一个掌握如此庞大资产的超强机构,不仅三大石油、五大电力集团接受不了,也与迫在眉睫的发改委和国资委的部分职能相重叠,而要从现有的能源管理职能部门中分权,则更是困难重重。 结果,2003年的中国能源管理格局依然是多个“婆婆”、分散管理,国家缺位。 2004年以来,把发改委能源局提升为副部级单位说法又逐渐热了起来。据最新的公开报道,设立副部级能源单位的编制已由发改委能源局上报中编办,初步编制为60人。把现能源局升格为副部级单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较小,而且也不像新设部委那样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 这对于发改委来说,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一些专家强调,不能因为官僚机构的权限划分,而置国家能源战略的大局于不顾,从中国的现实看,应该成立一个更高层次和级别的能源管理机构。他们担心,在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下,能源部和更低级别的机构不可能顺利平衡部门间的利益和矛盾,也难以有权威性,所以最好是成立由国务委员或一个副总理挂帅的能源机构。至于是叫能源办,还是能源委,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赋予其明确的职能定位。 “重新构建国家能源管理部门,肯定存在着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再分配,但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部门利益和职权的分配问题应该是可以协调的。”王宏英说。 应该抬起哪只手? 对于重新构建中国能源管理部门,尤其是成立能源部,有专家担心中国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再依靠行政权威来行使行业管理。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在中国,对领导的服从是中国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当管理者和管理机构从行政权威中获得更低管理成本下的最大利益时,极易形成对行政权威的路径依赖,尤其这样一个至今还有诸如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之类计划色彩浓烈的行业。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几乎可以预测到它可能采用的办法:开会、下发文件、突击检查。 但更现实的问题是,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从1988年能源部成立,到1993年被撤销,其中的5年间,作为国家综合性能源管理机构,它并没有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职能与企业职能不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干预太多、太具体,很难从现实的利益中超脱出来,站在战略高度考虑问题。 因此,一直以来就有专家主张,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重新成立能源部或者其他机构,属于饮鸩止渴。 “在中国,对于某个问题过于热衷,尤其当政府给予过度的关注时,有时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即导致对于该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陷于表面化。”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博士一直是市场化的鼓吹者,他认为,眼下在所谓能源战略的研讨问题上就有这样的危险。 “解决中国的能源供应,化解能源危机的关键不是靠目前讨论的这个战略那个战略,靠政府出手,而是要靠市场的力量。”因此,去年他就提出,中国能源战略的根本是市场化战略。在市场作用下,中国的能源供应不足恰恰有可能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最大动力,并通过技术进步、节能降耗来解决中国的能源供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佐军博士也认为,市场化是阻击能源短缺的杀手锏,“一般说来,在政府不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的情况下,相信市场常常更可靠。” 在采访中,支持重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专家们也普遍认为,重构管理部门并不是回归到原来的能源管理体制下,它的主要职责应是制订国家总体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政策,及时对我国的能源状况做出评估,并结合当前与长远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监控能源工业、能源市场的运行,建立能源安全预警机制,开展积极的能源外交,争取国际能源竞争的主动地位。 “能源部应该更多的从宏观上考虑问题,职能定位也不应该和原来一样。”作为基层的管理者,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的助理巡视员侯文锦思路也很清楚,“政府不要再去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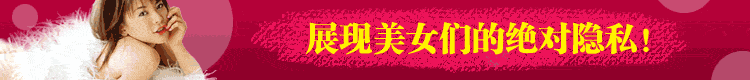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商务周刊》2005 > 正文 |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怎样迅速挖掘网络财富 |
| 短线最大黑马股票预报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开风情布艺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时装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创业赚大钱? |
| 05年具有潜力好项目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开冰淇淋店赚得疯狂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新行业 新技术 狂赚! |
| 投资3万年利高的惊人 |
| 1000个赚钱好项目联展 |
| 05年投资赚钱好项目!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