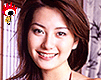黄益平:银行改制最终目的是建立有效银行体系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08日 11:26 《资本市场》 | ||||||||
|
文/本刊记者 杨光润 4月14日上午,美国花旗集团Smith Barney 经济和市场分析部副总裁、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资本市场》记者面前,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重组进行路辨之探。
改革就是建立有效银行体系 银行改制重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改? 黄益平博士认为:“从总体上看,改革的长期目标只有一个,即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银行体系。” 他说,“改革以前资金和资本的配置主要是通过财政体系来实现的,现在通过市场机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 “改革以前,中国只有一个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而其他的几个所谓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所以当时关于银行改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建立更多的银行。最开始的时候建立了四大银行,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再之后包括现在我们外资、花旗银行的进来。” “现在应该说我们的银行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从贷款占GDP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应该是150%以上。这已经非常庞大,而且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产权来看已经比较多样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 黄益平博士强调道。 对此,他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建立实体性的银行体系,目前这个工作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但仍然有发展的空间,比如民营银行比例过低等;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即如何使现有的银行体系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 对于第二个方面,他认为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要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完善外部的制度环境。 他觉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不应是光资金进来了出去了,然后同时制造很多坏帐,这样不论是使金融体系还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都很难持续下去。 如何变成有效的银行?黄益平博士开出的药方是,“首要的问题就是银行的业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业务,一方面把存款者的钱收进来,一方面把钱给贷出去,这中间一定要增加回报;第二要降低风险,风险主要包括信息不确定,比如宏观经济以后会怎样?利率走势会怎样?这些问题并不是银行可以控制和影响的;还有就是信息不完全,包括你把钱贷给企业,但不管你怎么去了解,你对企业的了解总是间接信息,你不可能对企业有一个彻底的完全的了解,这其中就是风险。 如何化解?他觉得最主要有两个,一个从制度的角度来完善内部的治理结构,比如说你本身的产权结构或者监督管理等;另一个应该是和外部的制衡,比方说我们的管制体系和市场环境怎样。他举例到,“利率是由国家决定还是市场决定,它本身对银行运作的方式和结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看银行改革,应从这样两方面来看。” 道德风险是改革最大问题 谈到银行业改革面临的问题,黄益平博士认为道德风险是银行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并且道德风险本身也是随着改革进程而不断变化。 他认为,道德风险是银行改革中永远都会有的问题。 作为一个银行管理人员,是不是能够真正按照银行的长期利益来做决策? 黄益平博士谈道:“我们刚刚开始银行改革,把一部分的资金配置、资本配置的功能转移到银行以后,很多的业务实际上还是由中央计划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拿到多少钱,什么样的部门应该多少,什么样的利率等等。实际上对于管理银行的人没有很多的自主权,所以当初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激励,管理者没有很大兴趣真正做事。”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银行管理,管理者也不是非常在乎,因为他也没有权限去改变;第二方面,做的好坏,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他55元钱一个月的工资,做好也是55元,做不好也是55元,所以这时候的道德风险就是不尽职。尽管是有银行了,但它的运作基本上还是一个计划体系,和原来的财政调拨前实质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因此,下一步改革应该给银行的管理人员更多的的自主权,要让制度的功能慢慢淡化,因为建立银行的目就是为了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给银行管理者决策权力扩大,也就是对他的经营支持放宽,行长可以决定把钱贷到哪里,给谁贷多少,甚至将来有权力在利率上放宽,这个时候所出现的道德风险就和过去又不太一样了,比如腐败,比如决策不当等等,他有了很多的权限,也有很多的激励,但不一定能保证他的行为符合银行的长期利益。” 从看坏帐到看资本充足率 怎样改善一家银行呢? 从2003年以来新政府在银行业改革方面的新动作,黄益平博士谈到,“监管体系的改革成为非常重要的部分。” “银监会开始运作,有法律依据地对银行进行管制,虽然出现‘法律依据清楚,实施起来困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体系的建立本身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银行的评价由单纯的看坏账比例转向考察银行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银行为降低坏账比例引起的许多不合理行为;” “其次,对银行制度本身如何控制风险问题也采取了措施,比如统一坏账分类原则、会计制度、建立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等等;” “再次,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方面,把国有独资体系转变为股份制,谋求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寻找战略投资者。” 上市不是改革的结束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黄博士表示中国银行业改革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市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结束。 他认为,“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仍然很大,虽然在短期内,由于所有者是国家而且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能力,危机不会显露,但是从长期来看,风险非常实在。银行‘黑洞’有多深?让人难以预料。” “坏账比例从官方数字来看,在几年内从30%下降到13%,虽然变化大,但由于每个银行对坏账的定义不同,使得这个数据的意义要大打折扣;坏账比率尽管下降,但每年的贷款额却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其中隐含着潜在的风险因素,几年之后可能显露;银行负债比例依然很高,一旦宏观形势不好,对银行资产的质量将会有很大挑战。” 改革路径借鉴国际经验 黄益平博士认为改革成功与否,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有进展:外部环境是否得到改善;立法、监管方面是否有很好的体系;产权改革是否成功,国家所占有的股份是否大大降低;除监管当局之外,市场对银行监管发挥多大作用。 98年、99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时候在很多银行实施坏帐责任制,如果你贷了一笔贷款,如果这个贷款哪一天变成坏帐了,你要终身负责。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本身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凡是做银行肯定要有坏帐,不管你是多好的银行,肯定会有一部分是坏帐,况且你做了好帐对你自己的激励并不是很充分,最终就导致他们就在自己银行的存款上不贷钱,这种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从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国家开始给银行注资,结果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到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就是监管体系。像韩国、泰国,他们有了自己独立的银行监管体系,或者是由其他机构兼顾这个工作,使得他们所谓的权力范围,或他们工作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监管体系得到改善,包括坏帐的定义 或者是坏帐划定的规则也变得比较的严格。在监管体系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变化比较大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所谓的新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坏帐,在多数国家,像泰国和韩国主要是一个所谓的中央化的体系,一个国家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所有银行体系的坏帐。 最后一个方面是在金融体系的结构方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的并购的现象。当然也有一些银行比如在韩国运作不下去了,国家收回来;也有一些小银行的倒闭、关门或者被其他的银行兼并的情况。 从以上的国际经验再反观我们的银行改革,黄博士认为,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和当初东南亚国家的改革,本身区别不是非常大,基本上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工作也都差不太多。 分拆大银行有助改革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黄博士还认为分拆一部分大银行有助于改革,因为规模大,改革难度大,并且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受到影响,政府不会任由大银行破产,但是对中小银行的做法却不一样。 他说,“虽然中国是大经济,有几家大银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经济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大银行,是有竞争力的大银行,是由市场主导而不是政府支撑的大银行。 “国企改革不彻底,给银行改革、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这些改革不完成的话,那彻底改善银行会比较困难。虽然大银行本身可以有潜在的规模效益,但是规模效益的回报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一个相应内部的机制,搞大银行反而不好,因为这样的大银行是政府把他们捏在一起的。现在如果把他们分拆了,以后再通过市场的力量把他们融合起来,到那时“大”才真正有规模效益,如果没有规模效益它就不会去做‘大’了。” 最后,关于花旗银行集团在中国银行业的抱负有多大? “花旗集团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雄心,一定要在今后几年或者十年成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前十大银行。” 黄益平博士透露到。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资本市场》2005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怎样迅速挖掘网络财富 |
| 短线最大黑马股票预报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开风情布艺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时装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创业赚大钱? |
| 05年具有潜力好项目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开冰淇淋店赚得疯狂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新行业 新技术 狂赚! |
| 投资3万年利高的惊人 |
| 1000个赚钱好项目联展 |
| 05年投资赚钱好项目!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