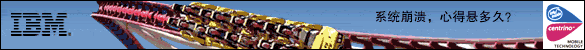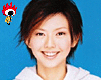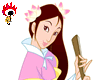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最近有不少来自西方主流财经媒体的记者都在关注曾经繁荣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这也许会让我们有些吃惊。实际上,在我们将这两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宏观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改革实验却在静悄悄地进行。来自地方的分散实验的结果和改革探索的经验也在迅速积累之中。一趟长沙之行,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上海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还放在改变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时,长沙的改革已经
很彻底了,而且很成功。
自从1984年我们开始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来,直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那就是,通过改革企业的激励制度(比如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制等),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是生产率或生产的能力)是可以改善和提高的。但事实上,国有企业这样的体制总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生存环境。国有企业的体制很复杂,它是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难与整个经济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割裂开来。在这个体制下过来的国有企业累积了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曾有的政策性和体制性的负担。越老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越多,这样的包袱也就越重。在这个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基本上都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作为官员的管理层目标和行为均与企业家有显著的区别。而要改革掉这两个问题,国有企业也就脱胎换骨了。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今天,长沙的做法就典型地反映了很多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这种理解方式。借用地方的话说,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企业的再造,再造就是重组。而我再加上一句,那就是,重组首先是一个会计的、核算或者财务的问题。长沙则把这个问题朴素地归纳为两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样的改革理论在10多年前就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被提出来了,当时的问题是在实践上不太能够大规模地去做。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上不能接受脱胎换骨的思想,现在我才明白,意识形态上接受还是不接受其实是一个成本的大小问题。当领导人认为民营化在那个时候的操作成本太大时,没有人敢冒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最要问的问题往往是,谁来为国企改革埋单?
重组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这使我想起俄罗斯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早期教训。去年年底,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在与我座谈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免费的私有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根本没有免费的私有化。要重组国有企业,首先必然涉及到这个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即职工的身份。我1994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一篇经常被引用的理论文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我把国有企业看成国家与公民的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国家用就业保障来换取公民放弃选择权。现在,国有企业的重组就是国家用市场合约去同职工替换社会合约。在这个替换中,国家要首先解除原来的义务,因而需要支付代价来赎回自己的义务。
那么,为什么今天国有企业的重组在财务上是可行的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重组的成本今天比20年前大大下降了。这是国有企业以外的改革到今天的一个重要成果。随着我们在社会保障、保险、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非国有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一些老的国有企业尽管不盈利了,但它的部分资产和土地、厂房还有着市场的价值,尤其是这些国有企业的脚下所占据的土地,更是值钱的资产。这些显然大大降低了国有企业重组或再造的社会成本。
回想一下,过去我们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增量改革,不先去动存量,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开始成本过高的改革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而变得可以接受和操作。当国有企业的身份像户口那样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改革的成本就下降了。这样,国有企业的重组或再造就可以转变成一个会计的或者财务意义上的项目来操作了。
我注意到,在建立这样一个损益表的过程中,长沙的经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全部国有企业的可变现的经营性和土地资产统筹到政府下设的资产经营公司中来统筹所谓理顺劳动关系的成本支出。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土地和部分可经营的资产在变现和重组中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国有企业原有的区位与行业差异对重组后企业职工安置的不同影响,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另一个来自长沙的看起来成功的做法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功地利用了政府作为第三者的角色和承诺。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土地置换、债务打包以及社保并轨等方面,政府作为当事人同时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比如,为了解决职工的社保问题,政府出面向社保局承诺把2亿元的社保欠费动用工业发展资金分10年付清。不过,我觉得有些顾虑的是,政府这样的承诺可能实际上是转嫁了部分国有企业重组的成本,对社保基金覆盖下的全部企业和人员来说有失公允。另外一些做法常常可能是,在引进控股投资者或者在土地置换与开发中由政府出面担保向银行取得信贷等。我主张,在筹措企业重组成本的问题上,不仅要做到阳光(公开化),而且要严格体现公正、合法和程序化。对于成本缺口的弥补,也是否应该考虑以合法和程序化的财政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干预政府部门和银行)解决更好?
最后,我还想提到的是,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再造,理顺了原来职工的劳动关系,尽管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但从长远来说还只是解决了存量问题,发展增量则是更长远和更重要的问题。在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之后,就业创造就成了政府的最根本的挑战。在浙江和江苏等地,由于非国有企业发展得比较早、比较快,因此可以很好地消化国有企业重组中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员。而对于一个非国有企业发展不够理想的地方来说,解除了国有企业的职工的全民身份,并没有真正缓释政府在就业创造上的压力。因此,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和鼓励更多的人创业,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上海证券报 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