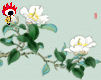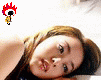| 国未富民先老--熊德明们的城市化觅食战争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08日 11:0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本报记者 何忠平 成都报道 从1996年5月1日起至今年4月1日止,四川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周立太总共受理了4698件案子——其中涉及农民工维权的占90%以上。
今年2月,为了追讨1.5万元的律师费,这位闻名全国的“民工律师”将一位身有残疾、生活困难的重庆籍民工告上了法庭,因为“当事人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律师代理费”。 7年多来,周立太共被拖欠500多万元律师费。在他所打赢的上千件工伤赔偿案件中,胜诉民工“拿了钱就跑掉的几乎占了一半”。 为此,周立太感慨万千,“中国农民工的培训不仅仅是技能培训,还有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训,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熊德明们需要培训 2003年在总理面前说了句大实话引起全国性为农民工讨薪运动的重庆云阳县农妇熊德明,现已是某集团公司的管理人员。进城打工1个月后,她坦承,“转换角色很难,目前的工作有点不习惯。” 周立太一针见血地指出,“获得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又咋样?从农村进入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 “农民进城务工,并不仅仅是工作和吃饭的问题,要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从事多年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郭虹所长指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郭丹也认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许多农民工挣了钱后,又重新回到农村,因为他们没有融入城市,在城市没有归属感。” 换句话说,农民工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和转型也需要培训。周立太就处理过农民工上午被招进企业,车间还没熟悉,下午就发生工伤的案子,也有为了获得企业内部的工伤赔偿费而自残的极端例子。 现实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往往是企业对文化高的员工培训,文化越高培训越多;而一些文化低正需要培训的,反而得不到培训——“这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就像银行贷款贷给有钱人一样,谁又会为农民工的未来作担保呢?” “每个农民的培训费用只有2元” 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仁寿县是四川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打工大县”——全县160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人数高达33.2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5,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一半多。方加镇又是该县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乡镇之一,据记者了解,全镇1.2万名农业劳动力人口中就有8000人常年在外务工。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县,去年政府培训农民工的投入,“平均下来,每个农民的培训费用只有2元钱。”县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股股长陈仲清肯定地告诉记者,“2003年,县里拨给7万元‘农村劳动力转移费’后,就将免费培训3.5万农民的任务由劳动就业局转交给了县教育部门。” 显然,这7万元杯水车薪“还远远不够”。陈仲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教师补助费、培训材料费、证书工本费、教材编写费等,按最低支出算,几乎就要花光这7万元。“加上安排工作会议、抽查工作等,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比如培训设施上的费用。” 如开办一个烹饪班,起码要有锅碗瓢盆;开一个家电维修班,家用电器和各种维修工具应该要有,更别说电子、机械等培训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如果仅靠7万元经费,根本没法完成培训任务,而且农民工来乡镇培训,要自己掏路费、生活费,“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参加”。 陈仲清也承认很难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培训,但他把原因归咎于劳动准入制度没有全面实施,“到底需要什么文凭或通过什么培训获得的证书才可务工,至今还没有定论。” 双流县的投入似乎要大方一些。该县副县长杨东升宣称:5年内每年将投入150万使全县32万农村青壮年全部接受一次轮训,掌握一至多门就业生存技巧。但据记者了解,该县去年培训了6.4万名青壮年,但平均算下来,去年每个农民工的培训费用也25元不到。 很多农民工难免担心花了时间和金钱,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就不参加。另外,金堂县竹篙镇农民周涛琼告诉记者,有些培训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1994年我刚出去务工时,县里有关部门对我们进行培训,内容竟是‘向左转、向右转’。” 2003年,仁寿外出务工人员创造劳务收入18个亿,占全县GDP的20%;整个四川省农村劳务输出137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达474亿元。然而即便如此,现实依然残酷。 据省农调队对仁寿、渠县等县(市)部分乡镇的调查,渠县51%的农村劳动力是小学以下文化,70%的未受过专业培训;仁寿县外出务工农民中85%是初中以下文化。 农民还是移民? 资金投入尴尬的背后,还有培训什么的问题。 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并提出培训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引导性培训”。 何谓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郭虹认为这里暗含了一个信号,“职业技能培训现在已完全市场化了,但对农民工的引导性培训——非职业教育,长久以来被忽略,现在终于引起注意了。” 不可否认,目前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很多都是政府行为,但这种培训其实还没有关注到真正需要培训的广泛的农民工群体,很多还只是局限在城市扩张之后被圈进城市里的城中村的失地农民。” “政府拿钱免费送他们培训而他们不见得需要。”而那些真正想得到培训的农民工,因为户口不在城市,郭虹告诉记者,“就没法享受到这种待遇。”这样导致的结果,城市政府只管它所辖范围内的“农民”,农民工也就是流动人口没人去为他们考虑,包括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在城市里也处于“非国家空间”,出现了“不流动的流动人口,不是农民的农民工”现象。 然而政府也有自己的理由,比如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有多少外来人员子女,“假如花很多钱办一所学校,但不知道学校的生源能否长期有保障,这显然政府对投资外来人口子女学校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收费低,假如教学质量好势必引来外来人员中的亲友子女入学,“这样,城市就承担了应该由其他地区承担的九年义务教育责任。” 一座没有移民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对很多举家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如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我认为他们就是移民。”但目前政府普遍表示“管不过来,没法管”,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农民工问题,而不是城市问题。郭虹告诉记者,目前她们正努力推动把问题聚焦在移民上。 根据流动人口居住分散、不易集中的特点,郭虹们尝试对一所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非正规学校的学生家长们进行培训,告诉这些在成都做生意或打工的流动人口“如何做家长”。同时,也帮助这个私立学校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讨论进入城市后的感受、你有什么要给即将进城的兄弟姐妹的忠告、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后来怎么解决等。 为了这个项目,郭虹本来想在社区先推动——让社区来接纳流动人口,让流动人口融合到当地居民之中。但社区负责人后来说了句很现实的话,“这个工作虽麻烦琐碎,但有经费保障,完成应没问题。关键是这个工作没有纳入年终目标考核,我们做了是算白做的啊。” 四川省社科联的高圭滋表示,流出地对农民工不好培训,流入地也不好办,农民工分布太分散,找不到他们,“如果项目能与劳动部门合作,见缝插针,借用政府资源,效果可能会好些。”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正文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