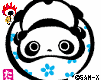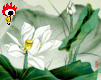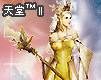| 南张楼没有答案--一个城乡等值化试验的现实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4月15日 08:58 南方周末 | |||||||||
|
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从1990年开始,山东青州一个叫南张楼的自然村所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与当前大部分农村不同的解决方案。 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理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经历了15年实践,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碰撞。 比如,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南张楼确实实现了把村民留在农村,但更多是通过大力兴办非农产业,这一切恰恰是在违背“巴伐利亚试验”初衷的背景下完成的。 现在的南张楼肯定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某种意义上,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一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本报见习记者 徐楠 3月22日,约根.维尔克到达山东省青州市(潍坊下属的县级市)南张楼村。 这个63岁的德国人是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在山东省外办他有个雅号叫做“德国白求恩”。下了车,和以往一样,头一个迎上来的还是留着寸头、脚蹬布鞋的袁祥生。他们相识15年了。 维尔克的中国之行也有差不多30次了。这15年,他们一直在为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试验而奔忙。这是何等感慨系之的一段合作,就如同共同参与了一个孩子的培养,眼看着他一点点成长起来——尽管并不完全是当初期待的模样。 从巴伐利亚州到山东省 1987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巴州和赛德尔基金会共同确立了一系列援建项目。带着为项目选点的使命,维尔克第一次来到青州市南张楼村,这个4000人口的大村,除了大片农田和一个冒着黑烟的砖窑,几乎什么都没有。矮胖的村支书袁祥生在前面带路,高大的维尔克跟着他趟过村里的烂泥土路,走过成片的垃圾堆,穿过村民惊奇的目光。 横七竖八的农舍、坑坑洼洼的地块,这些景象在北方村庄里,再常见不过了。 那一年,袁祥生41岁,已经在南张楼做了14年村支书。 项目的名称是“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维尔克的背后,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享誉世界的土地整理经验。50年前的德国面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农业凋敝,交通落后,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恶化,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维尔克说,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 赛德尔基金会想在中国山东做成这件事。 1990年,一个农业职业教育中心首先在山东平度建起,村庄实验作为其子项目来立项,基金会聘请的联络负责人常驻平度。袁燕那年刚8岁,现在她已经在村委会办公室工作:“选咱村是因为典型啊——六条:不靠城,不靠海,不靠大厂子,不靠大路,没矿,人多地少。”她说的这些都是袁祥生后来的总结。 就在那一年,4名德国人进村住了一个月。他们分别是土地整理、水利和建筑方面的专家,还有当时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司的司长马格尔。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南张楼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村里按照基金会的要求组织分组讨论。“妇女组要拖拉机;学生组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工业组要新设备、要接受培训;老年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袁祥生每组讨论都参加了,代表们提的全是“要钱的事”。 “无偿的资金援助”,这是村里人当时对项目的本能理解。 “德国人听了咱讨论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态,只是笑,估摸听出全是在要钱。”事后大家猜度着。 最后形成的《南张楼村发展规划》实际上是张蓝图,把村子划成了四个区片:大田、教育、工业区和公共设施,总的原则是:同类的功能要连片。规划不涉及定量目标,也不提资金的事,项目通过论证后,基金会承诺需要花多少钱就拨多少。 从那以后,村中大会小会必谈项目的进展情况。 首先是土地削高、填洼、整平、划方,每个基本“方”东西向300米、南北向350米,当季的粮食一打下来,就重新分了地。田间主要道路硬化了,宽的地方能开小汽车,大田比以前整齐了,播种机、收割机可以沿直线开过去。 接着就是修路。“以前下雨天根本出不去人!全是烂泥。”不满20岁的袁乐依然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景象。 房屋之间的“胡同”也全部重新整修,路面正中间挖一凹槽,用来排水。 幼儿园和初中的旧房子彻底扒掉了,在规划中的教育区重建起来。小学校来了德国客人,人家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德文,翻译朗声念出来:“南张楼的小朋友,你们好!”1994到1995年,基金会分批选送小学教师到上海、阜阳等地去培训。中学新建了图画室、微机室、劳技室等等。幼儿园和小学的桌子设计成半个椭圆的形状,拼起来孩子们就能围成一圈;中学的桌子做成梯形桌面,几张桌子能拼出个封闭的形状,是大家围坐讨论的空间。 幼儿园以南盖了长廊、亭子和小型雕塑,整片区域被划定为“村民休闲用地”。 1989年6月,袁祥生第一次赴德考察。后来他向基金会主动提出选派年轻人到德国留学。1992年,袁普亮和袁东升开始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学习德语。1996年,又去了袁普华和张敏。此外,德方每年资助几个青年到平度、上海、阜阳等地去接受职业教育。 2000年,“南张楼文化中心”落成,这是一座礼堂,全村共有1013户,这里有1013个座位。但欧式立柱和欧式色调使它呈现出很不“中国”的风貌,被德国专家说成是“建筑垃圾”。 2002年,民俗博物馆在文化中心北侧落成,这是袁祥生去巴伐利亚农村考察时的学习成果。挑角飞檐的两重院落,完全是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展品从村民手中收集,每件上面都用橡皮膏粘个小条,写上捐赠人的名字。本以为德国人会对此满意,没想到马格尔又急了:“这是规划好的休闲用地,怎么能随便占用?” 1990年制定的区片规划,如今已经基本完成。赛德尔基金会前后投入约450万元人民币。2000年,南张楼项目在46国国际农村发展研讨会上被专门介绍。2002年,中德建交35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安排南张楼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讲解和翻译全由该村村民来担任。这件事在人们的眼里,被看作是赛德尔基金会极为满意的象征。 “副业”出名的南张楼 “外村的姑娘说给南张楼的人家,男方哪怕是腿脚不太利索,哪怕长得孬点,都能将就——关键他们村里副业多。”相邻的郭集村村民张秀说。 三月的乡间满眼是油绿的麦田,南张楼成了小岛,被包围在中间。 油绿色中间,往往只有几个稀疏的人影,很多时候一个人也看不到。 张云珍白天的时间就守在自家的美容美发店里,她说:“坡上(农田里)的事现在不咋费工夫,有时半个月也不到坡上去一趟。麦子一春三水(浇三次水)就够了,一亩地花个半天功夫,俺家三亩地,一半天也就完了。收的时候专门有人开收割机,一亩三四十元钱租上,就都打下来了。” 所以,她的丈夫袁可贵从机械厂下班回来,就能坐在屋里安闲地翻翻《齐鲁周刊》,晚上踏踏实实看电视。南张楼的厂子每年放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这里工厂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30分到11时30分,下午12时30分到4时,余下点时间,留给人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上班累了,生意忙了,经济上有底气了,农活就被包出去做了。赶上农忙季节,有三四百名外村人在南张楼替人收麦子。 中午11时30分,村里的三家饭馆开门营业了。都是家庭经营,父亲算账,儿子下厨,闺女端盘子。客人有不少是来村里谈生意的,也有很多跟袁长海家一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中午从饭馆炒菜带回去。 下午2时一过饭馆就关门,店主一家人该跑买卖的跑买卖,该下地的下地。 南张楼目前的经济总量里,农业约占40%。一般村民家庭平均至少从事两项“副业”:上班、种地、开店或者经办企业,选择多了,生活的底色就变了。 眼下还有约100名村民在国外务工,村子的人口保持在4000左右,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维尔克认为:“项目是成功的。” 但很多南张楼人认为,改善生活并使他们留在农村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国人的试验,而是“副业”的兴旺。不难发现:赛德尔基金会所做的文章,始终紧紧围绕“土地”。曾担任村干部的袁崇武说:“看起来他们是更重视教育和群众福利,对工业上的事好像不咋感兴趣。”然而,工业是这里最出名的“副业”。离开了它,南张楼的变迁恐怕要失去一层最坚实的地基。 借助外力的同时,南张楼没有停止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身努力。袁祥生说:“咱两国工业水平差距太大,他们的工业咱还达不到,咱的工业他们也搞不来!” 1970年代的一孔砖窑和一个油坊,是南张楼最早的“工业”。砖窑被德国专家坚决叫停了,因为严重污染环境。1984年村里建立了石油机械厂,选派16个年轻人出去学技术,面向东营油田加工石油机械。后来有了织布厂、化肥厂、饲料厂,因为临近寿光蔬菜集散中心、周边蔬菜大棚的种植面积很广,村集体又做起塑料农膜回收造粒。前前后后加起来,现在共有七八十家企业。 目前南张楼村固定资产由1990年代初的几百万元,增加到现在的五六千万元,年人均纯收入接近5000元。村子西边辟出了一片150亩左右的“开发区”,基本相当于土地整理带来的耕地面积增量。往后村里新办的民营厂子会从那里冒出来。 袁祥生去温州考察的次数最多,他认准了搞民营企业的路子,因此2001年村集体企业全面改为民营时他丝毫没犹豫。“村里不背那个担子了!”县级公路经过南张楼的路段,左右两边平房小院整齐划一,塑料造粒机械24小时不停转。 就是这七八十家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村民的生活,它们使80%左右的非农业人口成为可能,使青年在农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长。 村子依然是4000来人的规模。在赛德尔基金会的帮助下,村里不再为交通、文教犯愁,南张楼也以文教中心和集贸中心的功能幅射周边的自然村。缺少了土地整理后的高效率耕作,“副业”的兴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留在这里,几成是因为有了平整的道路和整齐的农田,几成是因为闯世界办厂子带来了经济收益和生存空间?没人想过这问题。这个村庄的15年有太多记忆,它还来不及细细梳理。 “厉害”的“袁村长” 为了陪同维尔克,袁祥生这些天就住在青州。 他熟悉这里,不亚于熟悉南张楼。这个庄户人曾是青州市市委委员和潍坊市人大代表。村里到青州不到30公里,到潍坊84公里,他的圆口布鞋无数次在清晨踏进市政府大楼,在那里他竖起耳朵听着各种各样的项目信息、投资信息、企业信息。 1987年,德方要搞农村项目的消息就是这样被他听到的,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第二年他的拉达车跑了51趟济南。后来省政府的门卫都知道:“青州那个胖子又来了,不用登记。” 进入进一步的考察论证时,德方要求中方提供一幅村庄、土地全貌的空中照片,和两幅带比例尺和高程的村庄田地地图。袁祥生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弄法,但他当即表态:“一年时间没问题!”德方专家说,巴州的一个村子搞这三幅图要3年时间。袁祥生憋了个大红脸:“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年时间保证完成。”马格尔当场竖起大拇指。 经过与德方专家的多次接触,袁祥生慢慢明白了:德国人理想中的农村,是安守乡土的,是自足的、宁静的。然而对中国农村的事情,他早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就是户口本的皮皮颜色不一样吗?咱庄户人哪点比城里人差?我就不信这个邪!” 袁祥生倒是希望村民走出去。村里对考出大学生的家庭给予一次性的物质奖励;袁祥生亲自去给初中生演讲,鼓励他们“出去闯闯”。在南张楼初中念过书的刘建强大学毕业后到青州市当了记者,回想起初中生活,他第一个想起袁祥生的演讲。 1992年一个华人从阿根廷回村探亲,这让袁祥生冒出了新想法。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安排村民到阿根廷务工,合作创办华生农场。谁也没料到这个开端有多重要。那个时候农村最响亮的口号还是“离土不离乡”,可袁祥生已经在大会小会上说:“出去一个富裕一户!”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少青年人先以商务考察签证出国,再转为劳工签证。 南张楼的很多人家都并排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出国打工的多了,咱得看看他在啥地方”。 后来有人说:论境外劳务输出,南张楼在青州搞得最早,等别的村都开始张罗,他们出去的头一批人已经往回返了。袁长海1996年出国,5年后从美国回来,盖了新房结了婚,又资助家里搞了个自营的奶牛养殖场,他说:“这几年我爱玩,花得凶,拿回来近20万人民币吧,在村里不算多的。” 机械厂、织布厂、塑料厂,直到现在的奶牛养殖,南张楼搞什么,周边村子就跟着学什么,但它总能快一步,出国打工回来的人“脑子活,见世面广,做起买卖反应也快”。 袁祥生说:德国人对这些是一知半解的,“有些事没告诉他们”。 村党委会召开的时候总是天刚擦黑。村委会小楼里灯光雪亮,袁祥生站在大幅的巴州风景图片前面,讲他在国外的乡村见闻:“一户就老两口,看不见边的大田全用机器耕,得空了俩人就骑马进山去。人家那山呀、路呀,干净得像洗过似的。”妇女主任郑庆彬很久以后还记得这些话。 当初搞项目时,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袁祥生一句话:路照修!谁家不乐意就隔过去,最后谁也受不了下雨天堆在自家门前的烂泥。德国专家再来时,只看到平平展展的大路和胡同。他们感慨:这是“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情感和友谊”。袁祥生还是不吭气,翘着二郎腿抽他的烟。 维尔克把项目获得的成功评价首先归功于“袁村长”:“他很厉害——大家谈规划的时候他说起一些想法,我们只是听一听,等到再来的时候,已经变成现实。” 德国的风和中国的空气 清晨,袁祥生散步归来,坐在宾馆大堂等着维尔克。 与德国人打了15年交道,架也吵过,脸也翻过,这个敦实而狡黠的山东人,最终还是摆了张合影照片在自己的案头,上边印着“珍贵的友谊”。 1993年巴伐利亚州州长来访时,村里正在为中学配备桌凳。用于教师办公桌椅的5万元已经到位,要求按照德方提供的图纸制作。为了赶在州长来时装备好,袁祥生拍板买了40张三屉桌代替,后来项目负责人把钱要了回去,那一次袁祥生火了:“我不用你的钱也能把中学建起来!我不陪你了!”事后他又后悔——人家按要求办事,于理不亏。 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心服口服。1993年给幼儿园做桌椅,德方项目负责人“为一颗钉子钉在哪,都能和木工一起研究几个小时”。费解归费解,用了六七年后,买来的桌子都快散架了;可他们指导制作的桌子,至今都没有变形。 小学音体美教师是基金会组织培训的重点对象。一人一个图画本,每天的功课是“发挥想象力”画各种东西。四方形的苹果,或者长着翅膀的鱼——都是黑板上的示范。 回村后,“学以致用”的具体做法是给学生布置命题作文——《二十年后的我》、《四十年后的学校》、《五十年后的我们村》。学生们的作文本中,写得最多的是:“四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一定变得更现代化、更美,有很多高级的设施。” 袁珊珊今年读高三,袁华在平度念职业教育,他们对自己初中时劳技培训的回忆,都只是几节木工课,“毕竟还要中考嘛”。 对于村庄发展规划讨论会,普通村民没有兴趣。“一般村民?你拽他来都不来,来了也坐不下去——开这会又没啥经济效益。”当年的大队干部袁崇武说。 几乎没人记得德国人印的问卷调查表上都列了些啥问题,“问咱满意不满意,让画勾那咱就画勾呗。” “德国人为啥来?咱没详细问,但总觉得吃不透那个精神。” “是不是要挖什么矿?在咱这里提炼啥东西?” 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村民中流传,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平淡了。 论证规划的一个月,是德国专家在村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再往后,每次最多三两天。田间匆匆的走访、办公室里长长的会谈,对村民来说,项目渐渐隐退到生活的背景之中,德国客人的形象模糊了。 今年20岁的袁伟说:“要是没人提起来,差不多都忘了有这项目了。”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副书记徐雪林说:“土地整理这方面,群众参与得还很不够。” 开发区沿路的一排小楼使德国专家相当不满,然而对于村民来说,住在那里就是富裕的象征。他们说:“那些在开发区盖新房的,都在青州城里买了楼呢!”建筑式样的否定是容易的,有关“先进”和“落后”的价值标尺却极难改变。 民俗博物馆建成了,袁崇武负责拿钥匙,他经常在里面独坐一天。有村民说:“俺的名字还在那磁盘子上贴着呢,有啥看头?再说,俺家门头(杂货店)上忙着哩。”小推车、老油灯、村史陈列,还有走廊侧墙上“二十四孝”故事的刻画玻璃砖,只好蒙尘。在村里,博物馆是最地道的中国仿古建筑,也是最孤独的建筑。 张云珍夫妇已经把儿子送到青州的亲戚家去读初中,他们还是觉得那样孩子才能有大出息。“现在看咱日子也不孬,城里有的咱这也有,可你想想:啥好东西不都是先到城里,然后才到咱庄里的吗?” 德国人带来的冲击是风,而南张楼落脚的这块土地,是它的空气。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关注“三农”问题 > 正文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